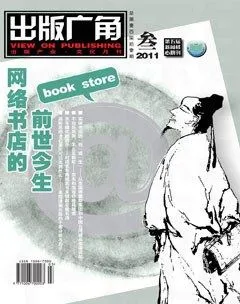\t窮出
[摘要]在轉企改制的大背景下,出版社的財商要得到進一步的提高,筆者認為還存在幾個主要問題:有了點文化意識,卻缺了點財商意識;安全談得多,財務自由卻談得少;產品談得多,企業系統卻談得少。
[關鍵詞]出版社 財商意識 財務自由 企業系統
財商是一個人對財富(泛指資產,包括品牌、人脈、時間、技術、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等)的認知、獲取和運用的能力,當年隨著《富爸爸,窮爸爸》一書而風靡全國,但是對于出版業的意義卻很少有人關心。也許有人會說:“我們出版業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的洗禮,早已經丟掉了計劃經濟的做法,怎么可能還不懂賺錢呢?”實際上并非如此,會贏利的出版社都很相似,不會贏利的出版社卻千奇百怪。如果我們從出版社的組織結構上很難覷見端倪的話,那么財商或許是一個不錯的破解之道。
出版社的財商發展軌跡可以分為4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大講或者說不用講(錢),因為在這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文明古國,不屑于靠賣書賺錢;第二個階段是不能講,因為那時“以階級斗爭為綱”,“出版工作為政治服務”,不能談錢,談錢很容易被說成“利潤掛帥”,否定“政治第一”,甚至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出版方向;第三個階段則是一個普遍的看法——編輯就是編書,編好書賺錢的事情由搞經營的人去想;[1]第四個階段,也就是當前,不少出版社認識到,要好好學學關于資本和管理的科學,學會兼并、重組、上市等運作手段。在轉企改制的大背景下,出版社的財商要得到進一步的提高,筆者認為還存在幾個主要問題。
有了點文化意識,卻缺了點財商意識
有的出版社對于錢的態度很有代表性。他們常常叫苦:這些年經營很困難,只有等有了錢才能解決這些問題。把問題索性都推給了錢。實際上,對于這樣的企業,沒有配套的人員和機制,尤其是沒有財商,可能給再多的錢也會被套進去,變成了庫存呆賬。在轉制前,出版社指望著上級單位或政府照顧自己,這可以稱作“權利意識”占主導。在轉制后,規則變了,只有具備“財商意識”的出版社才能活下來,才能讓員工活得更好。
出版社是要贏利的,但具體到哪種形式和何種程度,理解卻各不相同。比如個別出版社會說,我們不想賺那么多的錢,貪財是不好的,我們只求按部就班地出書。這樣的出版社對贏利表現出了清教徒式的克制,認為過分贏利是脫離文化的表現,似乎只要把贏利與文化并列起來,就會令人想到唯利是圖、粗制濫造、黃色低俗;而作為對立面,只要主管主辦單位不在意,那么不贏利甚至虧損反而可以心安理得地生存,出版社的文化可以脫離贏利好好地活著。可以說,這樣的出版社是有了點文化意識的,但卻缺了點財商意識。
實際上,出版社可以創造有品位的文化產品,可以聚集充滿人文氣息的騷人墨客,但這些充其量只是滿足了讀者的欣賞視角和作者的創作視角,還不足以談得上是個合格的出版社,出版社不應該使經營管理浪漫化或理想化。我們不妨看看被公認為出版家的王云五,他不僅文化造詣高,財商同樣也很高。有人總結:“王云五的出版家素質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雜家;擅長計算;善于借鑒和移植,喜歡創新;勤奮;辦事大刀闊斧,追求效率。”[2]除第一點,其他四點都體現了他的高財商。
有的出版社有這樣的錯覺,認為只要按照三審三校、印制發行等程序嚴格執行了,出版社就算正常運行,自然也就有財商意識了。實際上,目前不少出版社的三審制只是做到了內容上的“把關”,卻沒有做到財商上的“分權把關”。三審制首先是選題的立項審核,應該融入財商的考核標準和生成機制,訓練編輯的財商。比如,英國的出版人就建立了一套以分權為基礎的嚴格的出版流程,提高大家的財務意識,緩解出版風險。[3]
安全談得多,財務自由卻談得少
富爸爸曾經說過:“當賠錢和失敗的恐懼使內心充滿痛苦時,他會選擇尋找安全,而我選擇尋找自由。”其中安全指的是在財務和業務上采取保守和不敢創新的態度;財務自由則是指除正常的業務收入外,還有一些主動開展的投資和拓展。安全和財務自由并不是絕對對立的,比如安全是財務自由的前提,兩者存在轉化關系。這里主要談的是保守和創新兩種態度。
出版社面臨這樣的抉擇時,很多會選擇前者——安全第一。不少出版社的領導只求在自己的任期上不出什么大問題,其余則蕭規曹隨。在他們眼里,安全等于職位安全,等于仕途安全;贏利的圖書領域一旦發生風吹草動,需要開拓新的圖書領域,他們就一下子慌了神,或者病急亂投醫,什么書賺錢就做什么書,全無章法;一看到新項目就頭疼,因為自己看不懂這個項目究竟是否贏利,比較常見的處理方式就是把項目砍掉了;還有的出版社選擇了不用費腦筋的方式,即別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沒有自己的主張和規劃,完全跟著別的出版社甚至民營書商的腳步走,雖然短期安全了,但卻喪失了抗風險的能力等。
從財商的角度看,處理好安全和財務自由的關鍵在于把握好貪婪和恐懼這樣一對矛盾。比如有的出版社熱衷“安全”,即便談到所謂的“增長”,也是“按部就班”地或者“應景”地為了增長而“增長”。這實際是恐懼與貪婪的念頭錯位了。一方面,他們對現狀表現得很貪婪,認為目前的成績已經不錯了,碼洋差不多,庫存差不多,十分滿足;另一方面,他們對未來很害怕,擔心外部環境發生絲毫的變化,擔心上級領導發出影響他們命運的指令,擔心轉制、資本、數字、改革、人事等充滿穿透力的話題。其實,出版社的領導可以采取相反的思維方式,即一方面對未來表現得貪婪,敢于從長遠發展為出版社考慮,另一方面對現狀表現得很害怕,要有危機意識。
出版社的財務自由有自己的行業特色。筆者認為,只有立足于內容資源和出版權的經營,出版社才可能實現財務自由。我們可以把出版權看作是一種“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的濫觴造成了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但從企業經營的角度,衍生工具的思維方式卻是現代企業不可缺乏的。不少出版社低估了內容資源和出版權的價值,相信隨著我國版權保護制度的完善和數字出版技術的發展,內容資源和出版權必然能為出版社帶來新的贏利渠道。
產品談得多,企業系統卻談得少
不少出版社只注重選題和產品,卻從不講企業系統。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可能出版過一些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俱佳的圖書,但是他們卻不是都擁有具備贏利能力的企業系統。很多出版社滿足于自己每年出多少新書,但“從創新的經營內涵說,做新書并不等于創新——一本書單從品種意義上說可能是新的,但也可能不具有營銷價值和市場前景。”[4]即缺乏系統的、流程化的財商上的審視。此外,不少出版產品的生產是落后于計劃的,產品生產線上各個流程環節的人員都忙得加班加點,其原因也在于大家不是在一個合理的企業系統內工作,而是僅僅為產品打工。相比較而言,在英國出版行業中,“商業模式”及“現金為王”(Cash is the king)這兩個觀念卻被反反復復地強調。[5]
有業內人士談到:“很多東西,看別人做很簡單,大把大把地掙錢,但你一做準死。原因正在背后有一套東支撐著別人的產品,而只看產品是看不到背后支撐產品的那些內容的。不少圖書,你可以做得比別人好,但市場卻未必買你的賬,結果可能完全兩樣。”[6]這里所說的“背后的一套東西”就是企業系統。世紀天鴻書業的任志鴻對此也深有感觸:“過去單靠一本圖書打遍天下的時代已經過去,單打獨斗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整個圖書行業面臨著重新洗牌。現在書業的競爭將不是產品競爭、市場競爭,更多的是一個企業的綜合實力的競爭,包括團隊的競爭,人才的競爭、物流效率的競爭,其中任何一個元素都可能成為制約企業整體效益的關鍵。”[7]
當前,出版業一個新趨勢是資本整合,這要求出版企業首先要有智能化的、成熟的企業系統。單單在產品上下功夫是無法達到資本運作的高度。比如,目前有的出版集團為了戴上“雙百億”的帽子,有意收攬中小部委出版社或地方出版社,但實際上這究竟是買資產還是買負債呢?有的看似增加了總資產,但是新買來的業務如果不能帶來任何贏利或贏利不大,那么歸根到底,還是買了負債。
出版社的財商不高,這可能與他們沒有足夠的人格化的出版理想和愿景有關。財商的核心在于贏利,但是贏利歸根到底是基業常青,是獲得實現自己理想的滿足感,是將自己的智慧投入到信念中的成就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應該學會冷酷地用“窮”與“富”來評價出版企業:企業因為創造利益才得以存在和發展;脫離了效益的企業或者等于公益機構,或者只有耗著等待破產。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09CXW17]“數字時代我國國民閱讀行為嬗變及對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 楊牧之.關于編輯的經營意識[J].出版發行研究.2009(4).
[2] 鄧詠秋.王云五的出版家素質[J]. 出版科學,2003(3).
[3] 耿相新.英美出版文化行記[M].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9.
[4] 葉寧.何謂出版創新[J].出版廣角,2007(7).
[5] 張東.英倫啟示——淺談英國出版業的核心觀念[J].出版廣角,2007(11).
[6] 安民.編輯掙錢與否的原因(一)[J].出版廣角,2007(1).
[7] 李彬,袁國女.任志鴻:民營書業進入企業化時代[J].中國出版,2009(8).
[8][ 美]羅伯特·T·清崎,莎倫·L·萊希特.富爸爸,窮爸爸[M].電子工業出版社,2003.1.56 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