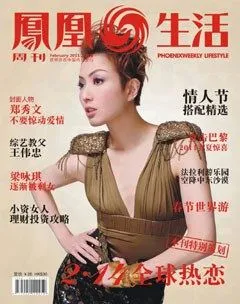綜藝教父王偉忠
2011-12-29 00:00:00
鳳凰生活 2011年2期

他自認為是個天生的電視人,
小時候喜歡畫畫打下了入行基礎,
大學讀了新聞系卻沒正經在學校學習,
而是跑去電視臺實習,然后再沒離開這個行當。
畢業后跟著曾制作《正大綜藝》的老板江吉雄干,
從打燈到寫劇本、畫背景、當助理編導、主持,
慢慢到當上制作人。他就是王偉忠。
眷村成長提供創作養分
其實王偉忠能夠在臺灣創造出“全民系列”這種頗具“顛覆意義”的電視節目,跟他個人的經歷和性格有絕大關系。而臺灣政經環境在近20年來的翻天覆地大變動,也給他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創作養分。
出生和成長于臺灣嘉義眷村“建國二村”的王偉忠,但在臺灣的軍隊中卻只是個管發動機和卡車的士官長。從小,王偉忠就敏感地意識到,自己是生活在一個階級分明的世界。在空軍眷村,飛行官住在獨門獨院大房子,地勤軍官較次一點,軍階最低的士官只能住違章建筑的小房子。
竇文濤:我說你們是臺灣來的客人,也有點不準確,要就此地來講,我倒算外人,我是山東人,你才是貨真價實的北京人。
王偉忠:本來我爺爺那輩是河北保定,然后我奶奶是旗人,我爺爺那輩的時候那進了北京城,我媽是河南洛陽人。我媽小時候就跟我姥姥進了北京城,那時候我老爺去打八年抗戰了。當時他們是住在西城,西四大院胡同那邊,后來就在抗戰勝利之后,我父親已經進了空軍,就在西四大院胡同碰到我媽。
小眷村,大中國
因為從小飽受階級制度迫害,所以王偉忠一直抵抗階級,長大了做節目,就會去做一些顛覆性的節目嘲諷階級、打倒階級。《全民最大黨》等一系列政治模仿節目以“全民”為名,是最自然的選擇。
成長在眷村也不全然是壞事,王偉忠覺得,“一個小眷村,可是一個大中國”。眷村里居住了來自南北各省的軍眷,空氣中飄揚著各種腔調的國語和方言,村里大榕樹下述說著爸爸們口中的家國大事和媽媽們口中的雞毛蒜皮生活小事,這一長串悲歡交集的故事,日后都成了提供王偉忠搞創作的“子彈”。
如今王偉忠練就一口很溜的普通話,忽兒可變成四川話,忽兒是天津腔,忽兒又成了東北腔,各種腔調來去自如,在大陸參訪時與各省各路人馬侃起大山而無往不勝,也就是來自當年的建國二村的滋養。很多成長自眷村的“外省第二代”日后成了臺灣藝文界的大腕和傳媒界的要角,在他們身上總能看到這種“多元文化”氣質的自然流露,令香港和大陸方面的同行艷羨不已。
王偉忠:臺灣很有趣,臺灣的文化是移民文化,所以臺灣文化有大量的中國文化精神,所以我們現在在做臺灣的文化創意。臺灣最棒的一個文化創意,就是最有臺灣特色的中華文化,就是多元文化。有日據時代的文化、有本來的河洛文化、有很多客家文化、有很多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文化,還有我們這拔1949年父母帶來的,大南北的這種文化,我們身上是帶著很多大江南北的東西。
竇文濤:就是說你到北京住兩天就能很快混同于一般群眾。
王偉忠:我們還蠻像以前的老中國那個味道,講人情世故,講兄弟姐妹,講情趣,講哥們,講道義,是真的不會老鄉見老鄉背后開一槍,是真的講感情。這個感情的濃郁是非常中國文化的,我們叫人,我們小時候再皮,再太保,你看我們那個打架打得,一看長輩還是問好。
“混世魔王”的電視情結
王偉忠雖出身軍人家庭,家中卻是“嚴母慈父”,父親是罕見的不動武老兵,而由母親專掌“刑部”。每當王偉忠在眷村里外搗蛋闖禍回來,動手教訓他的總是母親王孫紹琴。但他還是打混如故,氣得這位嚴母自嘆:“我怎么會生出你這混世魔王來!”
然而,這一種“混”的精神并沒有驅使王偉忠走入黑道,而是讓他轉化成一種擅于觀察社會、了解人性、隨機應變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他日后成為一個在圈中走紅了20年,卻仍然可以做一個以創意豐富、擅于掌握社會脈動著稱的好制作人。
竇文濤:我覺得眷村其實某種程度上講,它是一個不幸。尤其是昨天看了《寶島一村》,我就更加感覺到。最后你看父親給兒子寫的這么一封信,我甚至都想起近些年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提倡的一句話,但是這句話呢其實很通俗,就是別折騰,別折騰,但是這句話聽起來讓我覺得有歷史感。
王偉忠:臺灣也有句話,叫當家的不鬧事。
竇文濤:我就覺得這么多年來,中華民族真叫一個折騰。
王偉忠:我們這個民族特別內斗內行外斗外行,就是內斗特別厲害,外斗每個人都蔫了。世亂遭飄蕩,生還幾人遂。這個感受我沒有,但是我能夠體會的到,他們這種一輩子抗日戰爭,國共戰爭,生死幾百萬人。所以說我就覺得兩岸的人民老百姓甚至是全世界的老百姓都是一樣的人。
老靈魂
王偉忠自稱是個“老靈魂”,從小就“憂國憂民”。他確實憂慮臺灣,所做節目喜歡反映社會現象。他小時候就對“電視”這個東西充滿幻想,因為它可以影響很多人。在高中時代逃學時,他看到當年的臺視名導播黃海星帶著外景隊在嘉義公園出外景,心里就想:“他媽的!有為者亦若是!”當時就決心要做導播。
為了追求這個理想,18歲時他考上了文化大學的新聞系。一個眷村的窮小孩,身上帶著全家湊出來的兩萬塊到臺北。在新生訓練的前一天晚上,王偉忠在陽明山上的文化大學校園驀然看到山下臺北繁華的燈火,他發誓,要在臺北好好打天下,“有朝一日,要讓山下的萬家燈火統統認識我”。
帶著這種“光宗耀祖”的巨大壓力,王偉忠從大二開始就不放過任何在電視臺實習的機會。他曾經在攝影棚里關了四天四夜沒睡覺,當最后終于可以走出電視臺的攝影棚時,他抬頭看到臺北的夕陽,不禁跌坐在臺階上哭了起來。
為了多一點了解電影實務,他到臺北影業公司打工,學習沖洗底片,整天泡在充滿化學藥劑的工作車間。當同一批實習的學生都打退堂鼓時,王偉忠硬是撐到了最后,有了如今的成績。
竇文濤:你看咱們年齡可能挺相近,但是像你偉忠哥為什么對那段記憶刻印那么深,現在稍年輕一點的人,有個形容叫做活在空中。連我自己都覺得對過去的記憶很模糊了。
王偉忠:因為故事不多。
竇文濤:就是所謂活在當下,活在現在,根本就沒心沒肺的。但是我覺得這個眷村對你的一生顯得出來是刻印非常非常深。
王偉忠:我就說在當年有些事情你覺得是苦的,覺得是破的,覺得是不搭茬的,對你人生來講都是好事,所以人一定要珍惜你的一生,不管是苦的樂的什么東西,其實都是你人生的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