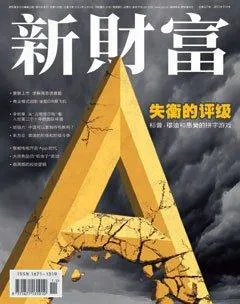以制度創新規避“棘輪困境”
當面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時候,要避免步入“棘輪困境”,最為有效的辦法是通過制度創新或者技術創新來提升潛在增長率的水平,否則只能接受經濟增速下臺階的現實。當然,對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而言,最為有效的辦法就是進行制度創新。
經濟學里的棘輪效應是指人的消費習慣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調整,而難于向下調整。尤其是在短期內消費是不可逆的,其習慣效應較大。用中國的一句古話來概括,就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當全社會都由于“習慣效應”把經濟活動具有不可逆性根植于自己的思維中,形成固化思維,那么由于經濟活動的“剛性”,造成經濟體未來出現經濟危機的風險將不斷積累,從而使經濟體陷在艱難痛苦或難以擺脫的經濟運行環境中,我們稱之為“棘輪困境”。
經過一輪經濟的高速發展之后,現實生活中,一些經濟活動的“棘輪困境”似乎隨處可見。例如,前一段時間媒體報道,北京通州一開發樓盤開始降價銷售,樓盤以前的買主要求開發商退還他們之前高價買房的差價或者直接退房。房價的漲跌本來是屬于市場行為,作為購房者本來就需要承擔價格漲跌的風險,但由于很多購房者的潛意識之中認為房價只會漲不會跌,在未來都會呈現出剛性,一旦房價開始下跌,這種現實便很難接受,從而出現前述的一幕。
經濟運行就像潮起潮落一樣,存在著發展周期。在缺乏制度創新或技術創新(當然中國過去30年高速發展更多享受的是制度創新和技術外溢帶來增長)的條件下,經濟增速就會在潛在增長率附近不斷波動,任何政策的調控或刺激,只能改變經濟體經濟增長波動的幅度,但并不能持續提升經濟增長的速度。
2008年,由于美國次債危機的影響,全球經濟增速出現了斷崖式的快速下降,為應對這一“黑天鵝”事件,決策當局動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避免經濟增速的快速下滑。盡管刺激政策有效地扭轉了經濟增速斷崖式的下降,但改變不了由于全球經濟下滑所帶來的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的事實。與此同時,在保住經濟增長的同時,刺激政策所帶來的“后遺癥”已經在不斷發酵.
其一,當前的物價壓力就是“寬貨幣”的結果。為了避免物價進一步上漲的壓力,決策當局采用偏緊的貨幣政策,但偏緊的貨幣政策又直接導致當前中小企業面臨融資的困境。當前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刺激后的政府投資規模越來越大,由于政府項目獲取貸款具有天然的優勢,當決策當局進行總量調控時,首先受到緊縮沖擊的就必然是中小企業;其次,由于緊縮政策和成本推動的影響,一些出口企業和一些中小企業的盈利能力開始下降,盈利能力的下降直接導致當期現金流的減少,而銀行天生就是“嫌貧愛富”的,一旦中小企業經營開始出現困難,那么銀行就會放大這一效應,在經濟學里這叫“馬太效應”。因此,由于通脹的壓力而進行的總量貨幣控制,其結果必然是最具活力和彈性、最有利于經濟轉型的中小企業受到沖擊,從而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發展。
其二,財政杠桿的透支會使經濟體未來抗風險的能力減弱。首先,積極的財政政策首先表現在地方融資平臺的快速釋放,但在地方融資平臺快速釋放的時候,地區的財政收入更多的是依靠于土地的出讓獲取,其他方面的財政收入并沒有呈現出相應的增長。這種單一的過多依賴土地出讓的財政收入,一旦遇上房地產調控就會減少,這種土地財政的風險也會凸顯。
經濟體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面臨發展方式的轉型和潛在經濟增速的下降。中國經濟在經歷了上世紀90年代一輪有效調整之后,步入了近10年的高速增長,目前人均收入已經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依照經濟發展史的規律,一個經濟體步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后,都面臨經濟轉型和潛在經濟增速下臺階的挑戰。二戰之后,成功跨出中等收入這一道坎的經濟體主要有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但它們在跨越這一階段的時候經濟增速都下了臺階,所謂下臺階就是相對于以前降低了2-3%的經濟增速。但是,還有很多拉美國家沒有跨越這道坎,其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經濟增速就出現了持續低迷。
面對經濟體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假若決策當局不愿意接受這一現實,一旦經濟增速低于其所習慣的增長速度,決策當局和地方政府就最大限度地運用可支配資源“保增長”,那么經濟體很容易步入“棘輪困境”。處于“棘輪困境”的經濟體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變得越來越脆弱,經濟結構變得畸形,缺乏經濟發展的健康性和可持續性,經濟體一旦受到外部沖擊或受其他黑天鵝事件的影響,經濟活動很容易形成斷崖式的下降。
因此,當面臨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時候,要避免步入“棘輪困境”,最為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制度創新或者技術創新來提升潛在增長率的水平,否則只能接受經濟增速下臺階的現實。當然,對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而言,最為有效的辦法就是進行制度創新,畢竟技術的創新需要多年的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