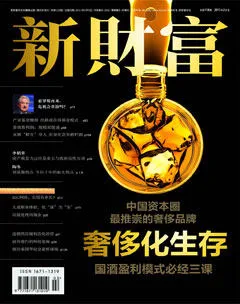房產稅發力點應是業主與政府良性互動
不要指望以房產稅抑制高房價,它不能改變當前投資買房的期望。但這個稅應該收,這是整體稅收體制改革的重要一步,關鍵是,這筆費用應該交給基層政府用于提高地方公共服務的質量,并且要求政府定期向業主通報稅收使用情況,接受后者的監督,由此形成納稅人與征稅人之間良性的互動,并以此讓地方政府盡快遠離出賣土地的收入模式。因此,房產稅必須發力于業主與政府的良性互動。
過去一兩年,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后出現了比較快的恢復,但是,地產價格過快的上漲,又成為最大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其影響遠遠超出了經濟、金融的范疇。這一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摩拳擦掌,紛紛在設計本土版本的地方房產稅。筆者認為,房產稅應該收,但同時要看到,在中國當前的環境下,這一稅種不可能緩解房地產價格的上漲;不過,從改革地方財政稅收體制的角度看,這個稅應該收,更應該利用好。
別指望以房產稅控制高房價
當前房價上漲的根本原因,是房地產市場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投資市場之一,眾多百姓,尤其是收入較高的階層,把投資房地產作為財富管理最主要的方式,而過去十年來的房價走勢也確實為這一理念提供了再好不過的佐證。這種百姓已經形成的房地產價格“只會大漲不會小跌”的預期不斷自我實現,支撐了當前房地產價格一輪又一輪的上漲。究其原因,這是百姓投資渠道不足加上流動性高漲所造成的。問題在于,由于中國的財富積累與其他任何一個市場經濟社會一樣,是不均衡的,因此,巨大的財富差距不僅體現為百姓房地產持有量的不同,而且,在中國當前土地存量不可能大幅增加的情況下,拉動了地產價格的持續上漲。
根據這個分析,只要百姓對于房地產價格上漲的預期不變,僅憑征收房產稅是不可能緩解價格上漲趨勢的。因為從政治層面考慮,房產稅的稅率與百姓預期的資產價格上漲幅度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目前房產稅稅率的上限也就是1%左右,而百姓對于房價上漲的預期是以10%為計價單位的。因此,房產稅不可能起到緩解房地產價格上漲的作用。
關于這一點,最基本的證據就是當前許多家庭或個人購買房地產之后,既不自住,也不裝修,更不出租,而是完全閑置。毫無疑問,這種閑置在短期內犧牲了租金回報,而中國目前的租金回報率最低也能在2%左右, 明顯高于即將開征的房產稅稅率。這種不租、不住、不裝修的行為,突顯出在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的預期下,許多百姓不認為所犧牲的2%租金是一個巨大成本。因此可以推斷,1%左右的房產稅對買房投資的行為不可能有重大影響。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要看到房產稅的社會成本。它會帶來民眾對政府的不理解和不信任,房產稅在很大程度上會被百姓理解為政府掠財的手段,這對于政府的公信力毫無疑問是有負面影響的。尤其是在當前的公共財政體制下,納稅人與政府支出行為和方向之間的關系極為薄弱,納稅人與稅收支配者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這種情況下,依賴房產稅來調節房價是不現實的。
房產稅的關鍵
是業主與政府的良性互動
盡管房產稅對于調節房價本身作用不大,但是筆者認為,這個稅還是應該征,但應該以非常低的稅率來征,比如千分之一,同時逐步擴大房產稅的稅基,也就是說,對存量房也逐步收稅。
而要充分發揮這一稅種的作用,關鍵是用好房產稅。原因很簡單,房產稅應該成為地方政府直接為業主服務的一種超級物業費。房產稅應該交給基層政府專款專用,用于包括掃街、治安、交通、環境治理等方面,以提高地方公共服務的質量。
如果地方政府能夠比較好地使用房產稅,同時定期向納稅人匯報,那么,就很容易形成著名經濟學家蒂布特(Tiebout)等公共財政學者長期研究的情況,即,地方治理搞得好的地方,房價會漲;房價漲了之后,地方服務繼續提升,這就形成了一個地方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一旦這種良性關系形成,就能夠打開中國公共財政的一個死結,那就是納稅人與稅收使用者之間的對立情緒。房產稅可能幫助我們恢復公共財政之本色,即,政府為納稅人服務。
總之,房產稅應該收,但發力點不在控制房價,而在于建立納稅人與政府的良性互動。關鍵是這筆費用應該交給基層政府來使用,通過這個辦法為地方政府尋找新的、可持續的、良性的、互動的財政基礎,讓地方政府盡快遠離出賣土地這種不可持續的收入模式。如果這一目的實現的話,那么,不僅中國房地產業的體制改革可以邁出重大一步,中國公共財政的改革也能推進一大步。
對于本文內容您有任何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