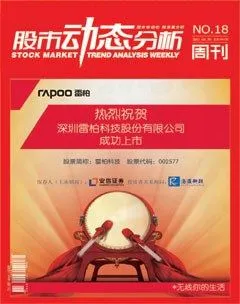預測與預期
我們似乎可以先扔出一個觀點,就是從預測到預期到調整預期,其實就是一個投資過程,它們在時間上有先后,在邏輯上有因果,在辯證法上又互相有反身性,這似乎又是個常識,但知易行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卻總是陷入一個個誤區,造成整個投資過程的強行割裂。
所謂預測,既是基于現有條件,綜合歷史經驗與基本邏輯而建立起來的對于未來的判斷。而這樣的預測,是投資工作的第一步驟,任何投資策略都是基于這種預測。而這里首先就存在一個陷阱,很多人過于關注預測的結論,依據結論決定投資行為。我不認為這完全錯,但一定不是完全對,預測的結論確實很重要,但我更關注預測的邏輯,即是預測形成的過程。其實,專家與非專家之間的最大不同在于邏輯,一個有邏輯一個無邏輯,一個邏輯嚴謹一個邏輯松散。專家使用的如果是數量化的邏輯,而一旦能形成模型,則意味著符合邏輯。而非專家一般沒有邏輯,即使有,也一般是把搜集到的其他機構的預測拿來,主觀給個權重,做個平均,如果硬說是數量化,也好歹是個算術平均……關于CPI,如果我們知道通脹是目前市場的主要矛盾,并由此形成了政策緊縮的廣泛預期,那么這個數字依然維持在高位就并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壞,這就是邏輯,如果沒有這個邏輯,我們看到接近5%的數字,豈不又會像很多人一樣,驚呼大事不好嗎。所以,如果僅僅依據預測結論,而忽略預測邏輯,我們會很容易受bK1TVGMzWsN8fpZ6eI6yf5Y452LlCAUitNT/o362ocU=到不同來源信息的干擾與蒙蔽,使我們放棄了選擇更好預測的機會,畢竟像剛才所說的,拍腦門所得的結論也是一個數字啊。
如果拋開預測的準確性不談,我覺得預測的價值有二。
一是預測的邏輯,不論經濟、政策是理性或非理性,總有規律存在。而這個行業中確實有很多值得我們尊敬的人在試圖尋找這種規律,而我所關注的,往往看誰的邏輯更符合常識,準確度更高一些,因此,我更加注重的是預測的過程。這一過程中,易存在兩個違背常識的陷阱,一是糾結于預測的結論是否正確,而落在預測的圈子里爬不出來,以預測為最終目標,自得于偶爾的準確,刻意忽略經常性的錯誤。二是過于關注預測的結論,而忽視了預測的邏輯,使得難以分辨合理的預測,魚龍混雜。
預測的價值之二,即是預測提供了預期的基本基礎。在預測完成后,將會依據此預測設計投資方案,而目前工作只完成了一半,因為方案一定不是完美的,而是否對其進行調整,則取決于預期。預期是具有一致性的預測,如果說預測只是投資者個體行為,那么預期擇時投資者群體性行為。多數的預期都來源于預測,預測錯了,預期也就錯了。預測是投資行為的基礎,而預期則是衡量投資行為的標尺,一旦不符合預期,那么必須迅速調整預期,以此為依據的投資行為也必須進行相應調整。而新的預期則需要與新的預測相互印證,等待事實的檢驗,然后依據預期的符合情況繼續調整投資行為。這就是上面所說的,從預測到預期到調整預期,其實就是一個投資過程。
但如果把一個投資過程描述的這樣簡單,似乎就抹殺了從預測到預期之間激動人心的魅力。這其中的關鍵點在于,預測的價值在于形成了預期,而預期的價值則在于超預期。
預期為市場提供了一個錨定目標,看的是是否會超預期的好或不好,而超預期就是這個市場上最有價值的東西,當然,也是最危險的東西。預期就是用來超越的,超越之后,之前的預期,一文不值。
對于預期的處理而言,最重要的不僅僅在于使用預期本身去指導投資行為,而更在于調整預期,形成應對超預期的方案,這往往是獲得超額收益與規避超額虧損的關鍵點。這里的困難在于,一是如何調整預期,如何依據新預期制定應對超預期的方案,制定后如何執行,執行時如何進行調整。二是如何應對超預期的超預期,像是盜夢空間一樣,我們經常并不知道超預期的預期會超預期到第幾層。
再賣弄一下辯證法,在預測-預期-超預期的投資過程中,其核心就在于預期的價值就是被超越,而超預期的價值在于為我們提供超額收益的機會與超額虧損的風險。這個過程中,時間有先后,邏輯有因果,還有辯證的反身性,任何單純強調某一環節的行為都是武斷的割裂,都落入了違背常識的陷阱。
最后要強調的是,應對超預期的方案比超預期本身更加重要,否則超預期也成“浮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