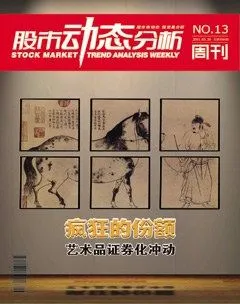非理性哄搶食鹽風波的股市感悟
席卷大江南北的一出哄搶食鹽的鬧劇上演總共不過兩天,便匆匆謝幕曲終人散。對于參與哄搶者來說,這自然是出悲劇。但對于圍觀者來說,則是出喜劇。魯迅先生曾經定義悲喜劇的本質是將人生有價值與無價值的東西以一種扭曲的形式展示給世人看。這一次亦是如此。但筆者認為更有意義的是:它為研究人們的非理性行為如何在合適的溫度下迅速由個體發酵到群體乃至形成極富傳染性的趨勢提供了一個生動的范本,通過剖析我們可以更深切地感知股市中常見的同樣是出自非理性狀態的“羊群效應”的來龍去脈。
本來就鹽的儲量在國內極其豐富及其在我國屬專營商品性質來說,最不具備哄搶條件的是它,最不應該被哄搶的也是它。這是一個理性的判斷,卻因為所謂的“核污染”與碘鹽可以“防輻射“被推翻,被蕓蕓眾生置于腦后。在正常人的眼中,那些輕信謠言的哄搶者都瘋了。但在哄搶者自己看來,他們并沒瘋,相反還“聰明”得很、“理性”得很——因為他們有“科學道理”作為行動依據。更重要的是:他們所信奉的人生哲學訓示他們“隨大流不會吃虧”,“你不去買,人家買完了你就買不到了”。由此可見,所謂的“非理性行為”實際上也包含理性行為從中開路的成分在內,也染有理性的背景。
在通常的情況下,理性旁觀者的注意力(或第一反應)很容易被導致“哄搶者”的素質有問題的層面。然而正如上文我們已列明的——當問題演化為“若不從眾便將吃虧”的選擇時,行為的動機已與素質無關,也與理性無關了。同樣的,那種將哄搶“上升”為“社會信用危機”以至“政府職能部門應對失當”的觀點,亦屬過度解讀——不是任何負面的突發事件都可以把行政機構拉出來陪刑打上兩槍的。
類似這次哄搶食鹽的社會現象,心理學有一個術語叫“群體歇斯底里癥”。此癥波及的范圍可大可小——小如三五組合、一二村落,大如一個行業、一個區域、甚至整個國家——那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便是史無前例的“群體歇斯底里”的典型,但它由頭到尾卻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在非理性的同時又是理性得很。足見非理性與理性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相互依存、互相轉化的辯證關系。很多時候,非理性的內核上往往披著理性的外衣,只是通常不那么明顯相反還較為隱晦而已。
“群體歇斯底里癥”事件如果起因比較簡單且屬短期因素,一般來得快去得也快,即所謂“見光死”,如這次的哄搶食鹽風潮就是;A股中的相關鹽類品種也同樣經歷了“一日游”行情。然而倘使“群體歇斯底里癥”成因比較復雜,延續的時間就會很長,直至最終形成趨勢,產生強大的慣性使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這就是我們在股市中常見的“瘋牛行情”及“羊群效應”了。事情發展到這個階段,如何把握非理性力量與理性力量的此消彼長,準確捕捉足以催生轉折的臨界點便成為決定成敗的關鍵。
寫到這里不由回憶起一件往事:在著名的“5.19”行情將見頂前幾天,我在某券商組織的一個大型報告會上發出了預警的判斷,說已到了“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時候了。豈料隨后發言的一個股壇新秀不同意“到頂說”,針鋒相對地提出:“在大家的頭腦都發熱的時候如果你還清醒,你就會錯失賺大錢的機會,你就是最大的傻瓜!”話畢臺下掌聲如雷,可見我的確已成為為數不多的傻瓜了。雖然三天后股指以大跳水為行情畫上句號,我得以將“傻瓜”的帽子奉還,但我還必須承認這位新秀說的這句話十分精彩,只是說得不是時候,太晚了些。如果在行情初啟或中段牛氣哄哄時說,是辯證法;在沖刺末段時說,則是詭辯論。因為到了這個關頭,瘋狂已到了極點,也就是非理性預期的膨脹已達到極限,再沒有發展的空間了——聰明人與傻瓜之間的擊鼓傳花再也難以傳到傻瓜的手上,博傻定律又怎能不壽終正寢呢?(更正:上期本欄文中的“今年的中國財富榜”及“今年越演越烈的高速擴容”中的“今”字皆為“近”字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