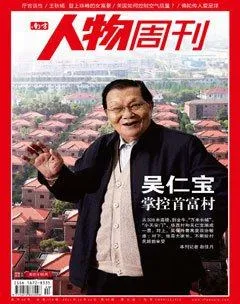吳仁寶治下的華西:小村
2011-12-29 00:00:00趙佳月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40期


分層的村民
“華西中心村內,外出就讀的大學生回村率是200%,他們不僅自己回來了,而且還會帶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甚至帶同學回來。”華西村宣傳科趙開軍自豪地說。
“回來有房子、車子,也不用找工作,我為什么要在外面?”今年6月剛剛從華僑大學畢業回村的趙龍賢說。和他同一年回村的李梅紅之前就讀徐州空軍學院,“和身邊同學唯一不同的,就是優越感。”
“如果去北上廣,還要自己買房子車子,生活哪有華西好?”1988年出生的趙龍賢和同一年畢業的同學比,他回華西的優越感在于此。
不僅是出了華西村的年輕人愿意回來,出了國的“海龜”也毫不猶豫地回了華西。“我去英國讀書兩年,覺得英國人住的房子也沒有華西大,車子也不見得比華西人開的好。”于是在國外學網絡技術的趙成寧愿回到華西,到華西銅業的生產第一線做個工人。
這些從小在村子里長大的孩子,出村讀書的時候就非常清楚“我是要回來的”。他們和父輩一樣,言必稱“老書記”。
盡管他們偶爾也會到20分鐘車程之外的張家港聚餐唱K,到江陰或無錫買名牌,他們對吳仁寶的印象是:“小時候覺得老書記只是個爺爺,長大了看著華西這么好,就覺得他非常了不起。”
年輕人如此,年長者更是認同華西的集體經濟和吳仁寶的管理:“村里的旅行社每年組織我們出國旅游,我們到國外看看,美國還沒我們華西好呢!”華西村316號住戶朱榮根感嘆。
中心村民手中都有一塊“硬牌牌”,也就是他們的股金。盡管他們在華西每個月的收入只有兩三千,“但重要的是年底的獎金。”年底的獎金二八分成,20%發到村民手中,80%強制入股。
事實上,趙龍賢希望“入股的部分多一點,等于存在村里,村里幫我們去理財,存得多,收獲得也多”。有他這樣想法的還有79歲的朱榮根。“存在華西集體的戶頭上,又安全又穩定,比外面去存銀行好多了。”
中心村民到華西本地的企業商鋪消費,可以用“硬牌牌”直接刷卡,這種來自于集體的刷卡快意,伴隨了華西多年。“買房買車都如此。”華西村最早是配額制的,車子房子都是統一發放到村民手中,“最初的一批車子只有十多輛,是捷達的。本世紀初,統一發了100輛白色賽歐。”至今依然能見到這樣的小車穿梭在華西村,盡管村里購買的十多輛奔馳多半由吳家人占用。
隨著集體資產的膨脹,漸漸地,華西村人脫離了消費配額的限制。他們有在外現金消費的自由,只是他們更愿意使用“硬牌牌”在華西村下的商鋪消費:“有得刷卡,我為什么要到外地去買呢?”
隨著華西村在江陰市區等附近地段的房地產開發,華西中心村的村民甚至可以用“硬牌牌”去江陰買房子。“只要你的股金夠,你就可以買房買車,買多少也沒人管你。”
上世紀60年代,鄰村的農民都還住著土坯草房,需要自己賺錢,自己蓋房子。而華西自1964年開始,“村里搞規劃,拿出一塊地統一為我們家家戶戶建蓋了新瓦房,以舊房折價方式給村民。”第一次分房,家家戶戶都分到的平房,面積基本相同,在50平方米左右。
1976年,全國在自然災害和政治風波中一片哀鴻,而華西村民則喜氣洋洋地搬進了兩層的排樓房。“按人口分配,每戶樓上樓下2-4間房。”1988年開始,華西村民分年分批住進了價值不同的別墅住宅,價格在12-50萬元不等。
現任村黨委書記的吳協恩,他的住房是價值三四百萬的華西村最豪華的別墅。這是2001年吳協恩領導的寶昌公司盈利為村企業最高之后,村里獎勵給他的,“他家一個浴缸就要幾萬塊錢”。
2000年后,“村里首次為村民提供13幢外型各異、價值在150萬左右的豪華歐式別墅;2003年又添40幢類似別墅,價值170-200多萬。這兩次先入住的,大多數是村企業干部,尤其新分的40戶都偏向現在正年輕的有經濟實力的村莊干部。”
如今在龍東湖一帶,1萬套別墅正在火熱建造中,這些別墅面向的人群是“大華西”村民以及村外人員,兩者價格有所不同:大華西村民因“大華西”發展需要價格為52萬一套,“大華西以外的人過來買,價格為300萬-400萬不等,是沒有個人產權的。”
華西一村的田琴家,別墅剛剛整飭完畢,陳舊的桌椅搬到全新的別墅中顯得寒磣。田琴家本屬于華明村,她在向陽村的工廠上班,老公則在華西村聯防隊,并入華西村后,他們借錢買了這個房,裝修了下,算是安定下來了。華西村每年每人發300斤大米,350塊錢,“從并村后到現在已經發了幾年了,但是去年突然沒有了。”
田琴買下這套房子的時候是16萬,“拆老房子抵了點,借了點,自己家里的積蓄都搭進去了,還是嫌貴的。現在已經是五十多萬一套了。”他們家的老房子原本在龍西湖一帶,那里如今成了華西最新的別墅區,因為面湖背山,算是華西村位置最好的房子了。“大部分中心村的干部住在那里。”
一幢位于田琴家別墅前的老房子,房門號上還寫著舊地址“唐家基”。這是沒錢買別墅的郭家。郭家兩個兒子,大兒子搬進了新別墅,小兒子沒錢買別墅。“按照拆遷政策,他們收回了大兒子的房子,等待二兒子搬走。”同時華西村將收回的同處一幢的大兒子舊房出租給了外來工,生活起居上的沖突于是就開始了。“這樣就是逼著我們搬了,可是又沒有錢買別墅啊!”
外來務工群體
從安徽到華西打工的陶業的一家十多口人,蝸居在華西村70年代建起的兩層排樓里。25歲的陶業和父親陶向軍都在華西鋼廠工作,每月2000元至3000不等的收入對這一家而言已經比老家的生活改善了許多。
這些打工者一般租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每月的租金從兩三百到四五百不等,工作時間也是不分晝夜,很多是三班倒。相較而言,華西村的工人則只上白班。“一般本村的村民都是領導,廠長主任什么的。”
陶業一家都是被他的小叔帶到華西來的。自稱在華西已經打工十多年的小叔,其實也僅是華西村金塔賓館內的前臺服務員。他們一家的居住區與中心村民的別墅隔著一條長廊,但是在華西這么多年,他們從來沒有與華西村民打過交道,“不認識華西村的人,也沒有華西村的朋友。認識的都是打工的外地工人。”
在華西實驗學校讀初一的陶飛翔已經意識到與中心村學生的差異,“初一一個年級有8個班,其中四班和五班都是中心村的學生,其他班級有些是我們外地來的學生,有些是外村的學生。但教課的老師是不一樣的。”
對于這種村民和外來打工者的差異,吳仁寶曾這樣回答媒體:“可以這樣說,待遇是一樣的,也有不一樣的。所謂一樣的,我們工資是一樣的,甚至有些比本村工資高。為什么會高?因為他的水平高,他的技術能力比較強。我們這里要的工資,要靠勤勞、靠科學、靠水平才能得高工資。”
作為一名外來打工者,已經步入干部行列的華西村藝術團副團長王維楨告訴媒體:“反正老書記待我們是很好的,我們在這里住的是賓館,那個幸福園里就跟別墅一樣,敲鐘的那個地方,就跟別墅是一樣的。環境也很好,里面其實就是賓館。我們其他人住在金塔。”
在老書記的眼中,2萬多的大華西村村民,加上外來的3萬多打工者,只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大華西建設成為“新市村”,將華西變為一座城市,每個人都要為“華西大集體”添磚加瓦。
一位華西村研究者認為,完全按照市場價格,外來工還是愿意到華西打工,原因在于華西村有實力保證他們的收入。盡管他們和華西中心村人的比較差距很大,但是跟那些給私營企業打工的人比較,他們更加穩定。
所以,這位研究者的觀點是,“你說華西被吳家族控制的時候,吳仁寶就說我們這么一個家族養活了四五萬人,如果中國全部像我們這個樣子,那中國也行了。那他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一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