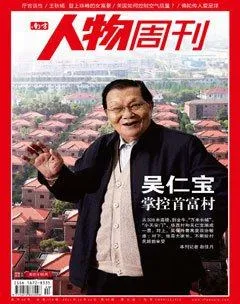《午夜巴黎》 如何成為漏網之魚
午夜的巴黎,時空交錯,亡靈悉至。
在虛無主義者和懷疑論者伍迪?艾倫的手里,時間是可以反復折疊打開的。只要你站在巴黎街頭等待一場細雨,或者跳上一輛極度不安分的汽車,你就會逃離這個成規陋俗壓迫的世界,成為一條漏網之魚。
1920年代的巴黎,想象力橫流、人性的亮處和暗處頻繁閃爍。那是一個以探索自我為樂的“流動的盛宴”。吉爾在《午夜巴黎》、在伍迪?艾倫的時間軸上貌似一個發達資本主義的抒情詩人,可他踏入發黃的、老舊的巴黎酒館,又喪失了本雅明式的孤僻和隔離,在由知識和想象筑成的世界里如魚得水。吉爾是生活在紐約的伍迪?艾倫的分身,對現實頗多微詞,獨立、堅持不懈地思考自我、死亡,每周會在曼哈頓某個爵士酒吧里演奏單簧管。這支單簧管就是伍迪與吉爾共享的時光機,就是電影里巴黎街頭突兀駛來的汽車。
伍迪?艾倫不避世,他并非幫助我們尋找一條充滿魅力的避世之道,《午夜巴黎》像他一貫的態度,美丑沆瀣一氣,我們對此只能喜憂參半、略帶嘲諷。
男主演吉爾的巴黎之行,需仰仗他準岳父的跨國并購生意,他能夠身處巴黎是國際資本游戲的附帶結果,就像吉爾和好萊塢的關系。吉爾是一個自我沒有充分實現的符號,他身份的模糊(一個寫作者,可是沒有作品)導致了他在現實世界中話語權的喪失。他的未婚妻一再試圖剝奪他在語言上的自主權,吉爾每次試圖用自己的方法論和世界觀描述主流社會,都會遭到未婚妻的一再阻撓,因為在不可一世的上流社會的大堂和庭院,ZUTdocH9jCZmqfVJ1VvEeSd0oa8rSOrYo/nR6dRWXM0=對美國政治、對羅丹大放厥詞,都是不合時宜的。
就算吉爾和女友已經形成一種未婚的社會契約關系,這并不能保證他們的關系牢不可破。保羅的闖入加劇了這種不穩定性,因為保羅可以對藝術如數家珍,并且不是以蹭吃蹭住的方式來到這個18000歐元一把椅子的巴黎。保羅有大學的邀約,可以堂而皇之進入知識的譜系,而吉爾只是一個影子般的無名小卒。
作為一個不愿過分迎合當代主流世界的寫作者、文藝愛好者、不成氣候的抒情詩人,吉爾解決自己身份焦慮的辦法非常伍迪?艾倫——他變成了一個現代社會的輕度精神分裂癥患者。他轉身進入上世紀20年代的巴黎,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斯坦因、布努埃爾魚貫而來。在燦若繁星的巴黎,在那些圣日耳曼的小酒館里,吉爾如魚得水,他的小說海明威讀過,斯坦因讀過。吉爾再也不是那個不可示人的寫作者,那個身份不能確立的、沒有語言果實的模糊之人。并且,作為“流動的盛宴”的列席者,吉爾獲得了充分的軼事和想象,這可以讓他在畢加索《沐浴者》面前來一番如數家珍的精彩表演,然后志得意滿地離場。吉爾的未婚妻以一種非比尋常的眼光望著他,這是惟一一次,吉爾在一個向后張望、充滿虛構的世界里找到了自己。
“如果你年輕時有幸停留巴黎,那么你的余生無論去往哪里,巴黎永遠會與你在一起,因為它是一席流動的盛宴。”海明威給了巴黎一個標準,印象主義式的標準,那是才華橫溢的巴黎,如影隨形,但我們每次調動巴黎的方法都不同。電影開頭長達3分鐘的明信片式鋪陳,不厭其煩地表達了一種對巴黎的摯愛,相比這些甜美的景致,伍迪對星級酒店的高級餐廳、紅酒品鑒會,歐式家具店可就沒有這么寬厚包容了。在伍迪?艾倫的價值體系里,一個物質、刻板、有秩序和階級的巴黎當然比不上一個超現實的巴黎,煙酒、愛以及所有的舞蹈都在敘述的愁腸里閃閃發光。
伍迪?艾倫貌似在和現實玩一個避實就虛的游戲:你沒有未婚妻,依然找得到巴黎雨中的浪漫,你不會生不逢時,也不會別無選擇。你可以在白日夢的碎片中借著巴黎剛好可以用來行走的雨,找到一個可以和你一起,在大街上被淋濕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