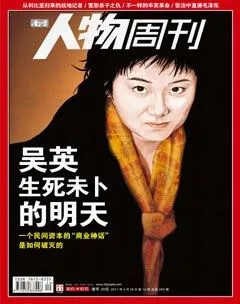邱永崢 我從戰場歸來
2011-12-29 00:00:00徐梅羅姝
南方人物周刊 2011年12期



北非震蕩的升級、萬能微博的強大傳播效力,以及他和央視主播水均益的一次戰地連線,令他聲名遠播
“別人怕不怕死我不敢說,反正我很怕死。”《環球時報》(環球網)戰地記者邱永崢捂著眼睛,又拿手在臉上狠搓了兩把,自打4月3日從利比亞回國,他就陷入了各路記者的訪問車輪戰中,必須強打精神勉力應付。
他從事戰爭與沖突報道已有幾年,報道過緬甸果敢沖突、4次跟隨巴基斯坦軍隊深入部族區記錄他們如何打擊塔利班,3次前往阿富汗,還曾嵌入美軍王牌101師,零距離呈現他們在阿富汗如何與塔利班武裝作戰。
今年3月,他和老搭檔郝洲進入利比亞東部反政府武裝控制區進行采訪。北非震蕩的升級、萬能微博的強大傳播效力,以及他和央視主播水均益的一次戰地連線,令他聲名遠播。
“做了這么多年戰事報道,這回突然火了。”他笑著搖頭,“咱們國家30年來無戰事,大家把戰地記者神化了,其實我們也只是記者行業里的一個特殊工種而已,在國外,很常見,各大通訊社都有戰地記者,跟我們一起在戰地采訪的外國記者有老有少,還有不少美女記者干這行。”
他個子不高、相貌平常、脾氣溫和、說話帶著福建口音,據說平常也不好交際,就愛宅在家里種花養草。這個形象與傳說中威武機敏、英俊瀟灑的戰地記者確實有差距。
他開始講述自己的見聞——根本還來不及反應就被炸死的利比亞軍人、家用轎車里被燒成灰燼的平民、10分鐘前還在提醒記者小心狙擊手的軍官,自己一扭頭卻被子彈打穿……
這些帶著濃烈硝煙與尸臭味道的故事與窗外明媚的春光、開得豪放盡興的花朵,以及旁邊球場上傳來的加油聲形成了反差。
10米外火箭彈從天而降
“戰地記者需要什么樣的特殊素養?你有什么裝備?”
“你怕死嗎?在前線靠什么保證自己的安全?”
“你見過的最殘忍的戰爭畫面是什么樣的?你會因為看得太多心理崩潰嗎?”
……
記者們問題總是大同小異,每次接受采訪前,他總要特別強調,“不要把這當采訪,就當是我們同行之間的交流吧。”隨著新聞競爭的加劇,越來越多的媒體將自己的記者派往沖突地區,“以后,中國記者出現在戰場上可能會變成常態。”
老一輩的戰地記者,如抗日戰爭的隨軍記者穆青、抗美援朝的隨軍記者林戊蓀、對印自衛反擊戰的隨軍記者郭超人、對越自衛反擊戰的隨軍記者閻吾等等,他們報道的是與中國有直接關系的戰爭,中國是參戰國,隨軍記者一般會受到我軍的保護。
海灣戰爭期間,中國記者出現于交戰雙方的陣地后方,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只能守在美軍或者伊拉克軍隊的新聞發布廳里聽新聞官“說新聞”。有中國記者向美軍提問,對方反問,“這場戰爭關你們中國記者什么事?”
2010年9月,邱永崢和郝洲與美軍簽下“生死狀”,得到駐阿聯軍南方司令部的批準,跟隨美軍101空中突擊師(《兄弟連》原型部隊)采訪他們在坎大哈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國防大學教授、海軍少將張召忠稱此次采訪行動是“新中國歷史上中國記者首次近距離觀察美軍地面部隊的作戰。”
“安全是第一位的”,他們剛到阿富汗的時候,美聯社的老記者提醒他倆,“悠著點”、“別干傻事”。嵌入美軍采訪時,他們按照要求配備了美軍戰地標配的防彈衣和頭盔,“一個頭盔800美金,防彈衣1500美金,可以防衛AK-47的連續射擊。”
那身防彈裝備在阿富汗立了汗馬功勞,卻不適用于利比亞,“反政府武裝沒有這個行頭,政府軍隊也僅僅穿個軍裝,沒見誰穿防彈衣。一旦(你)穿成這個樣子出現,雙方都會覺得‘哇,這個人很重要,一定要先把他干掉’。那里的情況是你穿得越低調越安全。有的西方媒體會找幾個武裝保安,但記者自己絕對不能攜帶武器,這也是戰地記者全球通用的規則,當記者拿起武器的時候,他就不再是記者了。我和搭檔一個人采訪,另外一個人觀察情況,發現不對馬上提醒,互相保護,沒有什么特別的保衛措施。”
“抵達戰地,安全就是眼疾手快。”在阿富汗隨軍采訪,他們所在的美軍作戰部隊曾經一天遭遇3次伏擊,也曾親眼看到一名美軍中尉被路邊的炸彈炸得粉身碎骨。
這次在利比亞采訪也幾度涉險。
“我們和當地向導兼司機約好了,車門始終打開,一旦有情況,立馬跳上車就跑。”忙完一天的采訪后,他和郝洲一般會用衛星電話跟國內編輯部再聯系一次,以口述的方式對當日報道再做些補充。
“打衛星電話的地點我們都會精心挑選,確保安全”,除了他們個人人身安全的考慮,還有對通訊設備的珍視。一部衛星電話價值四五萬人民幣,也是他們在戰地與外界通聯的唯一保障。
3月29日他倆在雙方交戰的最前線——本杰瓦德采訪,特地挑選了一個看起來很安全的地方支起通訊裝備,10米外是一個汽車修理鋪,鋪前空地上停著兩輛反政府武裝使用的皮卡,十幾名武裝人員散坐在地上休息。邱永崢與編輯部通話后回到汽車里,郝洲接著使用電話,一枚火箭彈從天而降,郝洲拔掉電話跳進汽車,司機踩死油門一路狂奔,驚魂未定時回頭,但見那兩輛皮卡車,連同那十幾個人,都被炸飛了。
“慌亂中我們的電源線和衛星電話背包全丟了,幸好那時整個采訪已接近尾聲了,不然太讓人絕望了。”
獨家摸清反政府武裝軍力
“戰地記者必須與職業軍人一樣,及時感受到可能面臨的危險,有效規避。”當諸多國內媒體躍躍欲試,打算將記者派往沖突和爭端現場時,邱永崢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事先培訓。
他本人畢業于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是一名有過11年軍齡的“老兵”,國外許多戰地記者也都有過從軍經歷。在踏上戰場之前,他和搭檔郝洲以及其他同事先后在國內接受了特警學院和防化學院的戰地安全培訓。
在《跟著美軍上戰場》一書中,他公開了自己的戰地求生秘笈。
當前方發生爆炸時,應該立刻180度轉身臥倒,以最快的方式趴在地上。
筆記本、錄音筆、相機、衛星電話等采訪設備,再加上防彈衣,緊急臥倒時肘部和膝蓋會承受不小壓力,一定要帶上護肘和護膝。
爆炸發生時,地面會劇烈震動,一定要用雙臂將自己的軀干和地面隔離開來,否則可能震碎內臟。
在阿富汗的“終極求生裝備”是《古蘭經》。2010年8月7日,一個由西方人組成的醫療隊在阿富汗東北部被塔利班綁架,該醫療隊的翻譯在生死時刻大聲朗誦《古蘭經》,成為整個醫療隊里的唯一幸存者。
……
找到可靠得力的“線人”也是決定戰地采訪成敗的關鍵,邱永崢自己總結了一個簡單有效的辦法。“如果你在一個非英語國家,發現一個人英語講得不錯,談吐不俗,這樣的人一定不要放過,他能給你帶來極大幫助。”他解釋,這樣的人一般受過不錯的教育,社交面也很寬,信息靈通。
辨識線人有時事關生死,他們在阿富汗采訪時,記者被綁架、被殺害的事情時有發生。有位日本記者聽信線人的話,“說跟著他們能采訪到昆都士塔利班頭目,輕率前往,結果被對方綁架,至今下落不明。”
憑著經驗和謹慎,邱永崢他們一直比較幸運。在阿富汗,他們結識了為美聯社工作了整整15年的阿富汗籍通訊員阿米爾?沙阿,“他五十多歲,經驗太豐富了,從蘇聯入侵阿富汗,到北方軍閥混戰,到塔利班奪取政權,再到美軍率北約部隊攻入阿富汗,他可以說是阿富汗現代史的一個見證者,他們家在當地也算一個名門望族,我們就靠他找到了塔利班的頭目,找他走遍阿富汗,沒遇到太大的困難。”
在利比亞采訪時,先期撤離的馬來西亞女記者艾米把一個非常得力的當地向導介紹給了邱永崢,他名叫哈里發,身兼司機、翻譯和向導三職。
哈里發本是利比亞阿拉伯海灣石油公司中級職員,三十多歲,受過良好教育,去過英國等發達國家,起初他也是一名狂熱的反政府“革命者”,甚至是組織者。然“革命”的結果是公司關張,他失業丟掉了飯碗,不得不冒死送外國記者去前線掙錢養家,按照約定邱永崢他們付給他城內采訪每日200美元,城外采訪視危險程度不等每日600至800美元的酬勞。
事實證明,這次他們又找對了人,“在后來整個26天的采訪中,哈里發起了很大作用。”
3月10日,卡扎菲政府軍已推進到距班加西200公里的港口城市卜雷加,邱永崢一行在反政府武裝把守的戰略重鎮艾季達比亞采訪。機警的哈里發看到反政府武裝前線指揮部門前湊著一幫記者,他去打聽,得知一會兒會有個要人來視察。其后,哈里發把邱、郝二人拉到一座民居,他說:“你們在這兒等著,過會兒反政府武裝最高司令尤尼斯將在這里接受加拿大記者采訪。”
邱永崢說自己當時心中一陣狂喜,他來班加西,首要的采訪目標就是尤尼斯。尤尼斯原是利比亞內政部長兼特種部隊司令,他與卡扎菲鬧翻后,卡扎菲懸賞40萬美元要他的腦袋,曾經3次組織暗殺他。“我們真是太幸運了,全球只有4家媒體采訪過他。”
在這次意外收獲的獨家專訪中,尤尼斯告訴邱永崢、郝洲,反政府武裝的核心武裝力量就是隨他一起造反的一千多名特種兵,這也是反政府武裝第一次向媒體透露了其真實的軍事實力。
繼續行走在剃刀邊緣
非常時期,如何在新聞現場與美軍、埃及軍方、利比亞反政府軍的關鍵人物搭上線?
我的性格其實算不上外向,但是當我進入工作狀態后,我可以去認識任何人。
有一次我的目標是一個阿富汗國防部高級官員,我沒有辦法直接聯絡到他。只能先找到他的發言人,我充分研究過這位發言人的履歷,他很有名,是阿富汗國防部的創始人之一。我之所以決定通過他接近真正的采訪目標,是因為我確信這個人非常有能力,通過他我肯定能找到任何人。
雖然他本人并沒有什么新聞價值,但我還是向他預約了一次專訪,采訪提綱是我根據他的履歷設計的,問得他很高興。
采訪結束后,我把事先準備好了的一份采訪名單交給他,請他提供幫助,他絲毫沒有拒絕,很快為我安排了一系列采訪。
還有的時候,因為戰亂完全沒有秩序和規律可言,需要你通過自己的判斷和變通尋找突破口,如果你找到了,那你就成功了。
例如這次去利比亞采訪,很多事情按流程來走是做不到的。我們原本是打算從埃及去的黎波里的,但是在埃及時發現來自的黎波里的新聞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內容,政府軍方面嚴格管控記者們的行動。
于是臨時決定改去反tenmg9FvtPGpga1bl8sa0Q==政府軍控制的東部,事實證明我們做對了選擇,班加西是其后的主戰場。到了之后,反政府給我倆一人寫了一張紙片,用英文分別寫上我們的名字和服務報社的名稱,說這就是準許在利比亞東部活動的“記者證”,我們想去哪里去哪里……
邱永崢家的陽臺一派春意,功夫茶桌被花花草草環繞,半個月的休整時間里,他最大的享受就是坐在這里,和朋友喝茶聊天,“聊啥都行,就是別聊工作呵呵。”
幾乎每個訪問他的記者都關心他的心理問題,害不害怕,想不想家……
這個實在人的笑容總有幾分憨厚,“說真的在前線真顧不上想東想西,工作一天下來,稿子發回去,腦袋一挨枕頭就睡得像頭死豬了。”
每次都是回國以后,細想那些與死亡擦身而過的驚險片刻,心里才會涌起一陣陣的后怕。
他不吃動物內臟,春節的鞭炮聲也讓他不安,“這些都讓我想起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西方有很多戰地記者一干就是一輩子,離開了那個特殊環境反而不適應了。”他不知道自己還會干多久,可以確定的是10天之后,他將再度出發,目的地還是北非某個動蕩之地,繼續行走在剃刀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