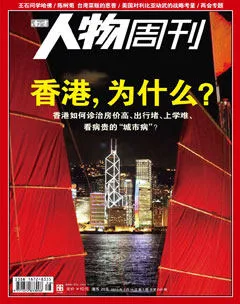觀察
好的管理和壞的管理
“黑車”是一個很令人傷感的詞,為什么連車都有“黑”的?
何三畏
兩會期間,國家發改委發出通知,決定從3月28日起降低涉及162個品種、近1300個劑型規格的藥品的“最高零售價格”,降價后比現行規定價格平均低21%,“預計每年可減輕群眾負擔近100億元”。
這是適合獻給兩會的消息,配合了兩會“解決民生問題”的主旋律。這個獻禮的規格比較高,屬于國家級的。另外,我在網上還扒出兩條消息,地方性的規格,但也同樣的有民生性,適合獻給兩會:“成渝大巴大降價”,降價的幅度比上述藥品還高,接近30%。
這樣的消息實在正面得讓人不知說什么好。因為它惠及百姓,可是,我們可以弱弱地問一聲:在這通脹加速的時候,這樣降下來,行業里還有利潤么?如果有,那么,它們原有的利潤,能不叫暴利么?如果屬于暴利,它又是何以穩定地維持著,而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行不悖的?
但這樣的問題,是不會有人回答你的。給你“實惠”,你就接住吧,不接白不接,接一個算一個。所以,政府在發布“增加群眾負擔的壞消息”時,會有一個“理由”,而發布“好消息”,就“不需要理由”了。例如,從前鐵路春運“漲價20%”,就“講理”(聽證)了,到“不漲20%”的時候,就“不講理”了。
但我覺得,“好消息”跟“壞消息”一樣,都需要說明理由。“說明理由”應該成為政府的習慣。只是當發布“壞消息”的時候才“講理”,會造成公眾的心理負擔:當你開始“講理”,他就擔心,就緊張。這樣,公眾會不喜歡你“講理”,害怕你“講理”。這該有多悲催。
同樣是行政定價,漲價聽證,降價不聽證,邏輯上還可以隱含這樣的不公平。假如某個官員“不喜歡”某個行業,甚至不喜歡某一位在這個行業里占有一定份額的人,他就可以以“惠民”的名義,來一個降價令。當然,這只是理論的推演,現實中恐怕不會大面積發生。因為事實上,在中國,行業總比公眾有話話權,行業總是不乏代言人,而官員也總是熱衷于讓某人在行業內“做大做強”。
世界上是不是真有無緣無故被“減輕”的負擔?這是很可疑的。如果某些藥品的“暴利”還可以頂住市場內外的壓力多堅持一會兒,它會不會“提前”降價,這可能屬于行業秘密,不為筆者所知。但一望而知的是,如果某一條公路客運線是旅客到達相關目的地的惟一選擇,你的“負擔”只會越來越重,而不會“減輕”的。
前述這一條公路客運線降價,無非因為一條平行的鐵路線,火車跑得越來越快,價格卻比它低30%(也就是而今公路宣稱降下來的那個水平),以至它客流不足,開始空著車跑了。而市場真的是一個靈驗的東西。新聞報道說,降低第一天,客源就增加了50%。這就是群眾得到“實惠”的過程。這就是群眾在有關部門管理下的命運。
在中國,許多重要的行業,特別是壟斷行業,都有一個或多個權力部門為其利益代言。用行政手段維持其高價,是人所共知的基本管理方式。由此支撐著的巨大腐敗空間,也給社會造成巨大的傷害。藥品行業的黑幕,令人發指,不知危害了多少百姓生命,更“害死”了級別不低的官員。交通運輸呢,前鐵道部長劉志軍先生的胞弟在武漢鐵路局除了瘋狂的經濟腐敗,還有買兇殺人的極端刑事犯罪。
“黑車”是一個很令人傷感的詞。為什么連車都有“黑”的?但是,想想在一個有30%降價空間的車站附近,怎能沒有“黑車”滋生!“黑車”也是合法生產的車輛,就因為沒有向有關部門繳納“門檻費”,這就連同車主一起“黑”了。而由高額的利潤空間必定撐高的“門檻費”,也使被排斥在門外的車主有動力去冒險當“黑車”。所以,說“黑車”基本上是“管理出來的”,并不為過。公眾要顛倒黑白,稱“管理費”為“保護費”,也可以理解。
車既已變黑,警方便不得不努力去“打擊”。車是無辜的,被打擊的,其實是人。而這些人如果不去開“黑車”,或許可以做“好人”。上海“釣魚執法”的悲情事件,無非就是這個邏輯。這就是有關管理部門給社會增加的額外成本。但還要說明的是,汽車客運行業相對其他壟斷行業,并不算暴利,應該相信它不算太黑。只是這個道理,足以貫通經濟黑道產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