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登之死與世界反恐之路
2011-12-29 00:00:00張學林韓存江
輕兵器 2011年1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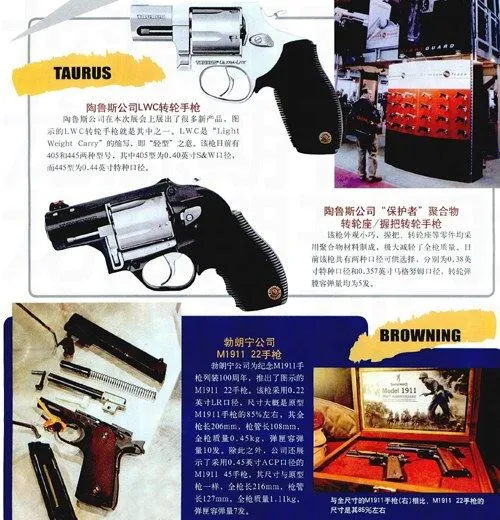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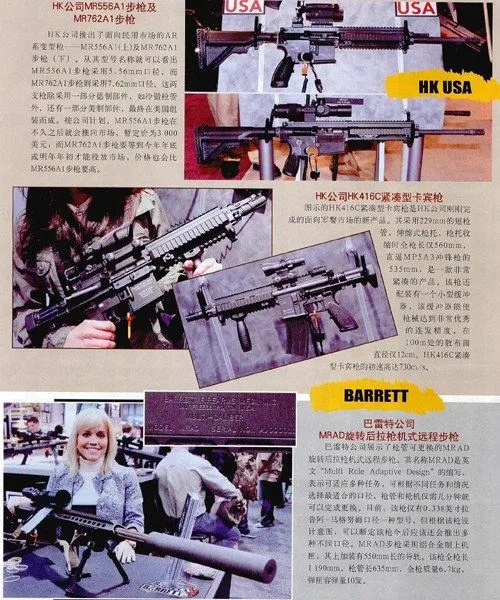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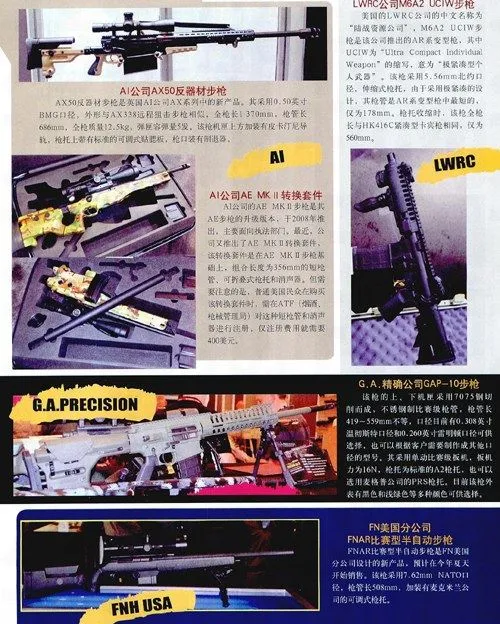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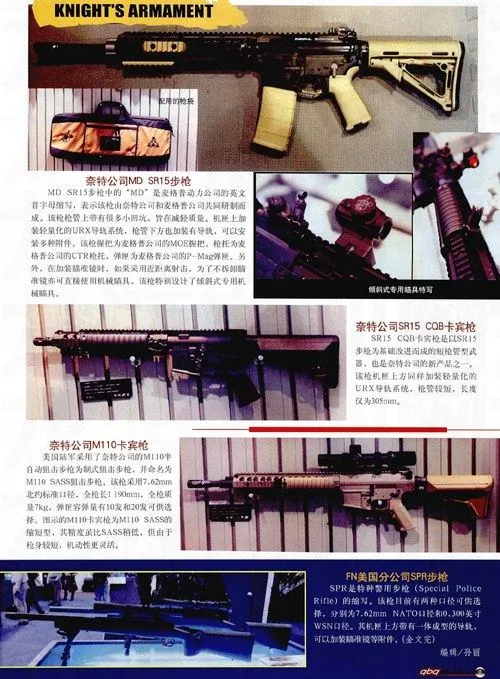
北京時間5月2日上午(美國當地時間5月1日深夜)奧巴馬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布本·拉登被美軍擊斃。此言一出,各國媒體爭相報道,全球匯市、股市、商品期貨市場聞風而動。恐怕世界上還很少有一個人的死亡會對全球產生這么大的影響,足見拉登之死的轟動性。拉登之死將對世界反恐格局產生重大影響,會對世界各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新的變數。拉登之死并不意味著世界反恐戰爭已經取得了徹底勝利,相反,反恐之路仍將任重而道遠……
拉登的人生軌跡
這一次,拉登真的死了,結束了他54歲的人生。
回看拉登的人生脈絡,其中充滿了跌宕起伏。他舍棄富裕的舒坦生活不過,卻為了“信仰”,寧愿呆在山溝里風餐露宿,冒著生命危險,出錢又出力地和前蘇聯、美國等他眼中的強權勢力作斗爭,直至生命的終結。他策劃了多起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事件,特別是他策劃主謀的“9·11事件”導致近3000名平民喪生,這一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國對國內及國際安全形勢的判斷,也改變了以往世界范圍內的反恐戰略格局。由此,美國稱拉登為世界頭號恐怖分子。
從富商之子到“圣戰者”的轉變
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局收集的一些卷宗描繪,本·拉登出身的家族規模龐大且極具影響力,與本國(沙特阿拉伯)王室關系密切。本·拉登的父親曾經借1950年代初阿拉伯半島的第一次石油大開發,成為當地聲名顯赫的建筑商人。而1957年出生的本·拉登在童年時就與沙特的王子們一起玩耍,并在15歲時就擁有了自己的馬廄。不過,在52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17的本·拉登,與其他大部分都去西方國家學習或者長期居住的手足同胞不同,其從來沒有前往西方接受教育,而是在阿卜杜拉國王大學完成了學業。這一經歷被認為與本·拉登后來的極端反西方思想頗有淵源。還在大學期間,本·拉登即與穆斯林兄弟會這樣的伊斯蘭激進組織來往甚密。1979年,前蘇聯入侵阿富汗,本·拉登來到阿富汗參加“圣戰者”組織,資助阿拉伯國家的志愿者來到這個中亞國家抵抗前蘇聯入侵,并為他們提供訓練經費。很快,本·拉登成為在阿富汗的阿拉伯“圣戰者”的領袖。1988年,本·拉登及其“圣戰者”們建立了一個名為“阿爾—伊達”的大本營,即基地組織,專門訓練“圣戰者”。不過,本·拉登的目標并不僅僅是將前蘇聯入侵者趕出阿富汗,而是要通過暴力手段改造整個伊斯蘭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拉登在阿富汗的所作所為當時都得到了美國中情局的幫助。美國為在阿富汗抵抗前蘇聯侵略軍的“圣戰者”們提供武器彈藥和資金援助。可令美國人沒想到的是,十多年后,這些美制的武器反過來會被用于擊落美軍的直升機。
從捐資人到精神領袖的蛻變
通常,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被認為是本·拉登個人生涯中頗具轉折意味的一年。為防備薩達姆的軍隊入侵沙特阿拉伯,本·拉登志愿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武器和士兵,但沙特阿拉伯拒絕了他的援助,取而代之的是美國援軍。這下激怒了本·拉登,他以此開始向基地組織提供財政援助用于暴力攻擊美國。1992年,一樁針對駐索馬里美軍的也門旅館爆炸案,被美國情報人員認為是本·拉登操縱之下的第一樁恐怖襲擊。不過,根據埃及記者達爾維希的分析,此時本·拉登尚未進行任何意識形態滲透,而只是通過一個非常復雜的、從也門一直延伸到阿爾巴尼亞的金融系統來為基地組織提供后勤支持。到了1994年,本·拉登開始在蘇丹建立新的訓練營,但此時,蘇丹政府正式凍結了拉登的財產并剝奪其公民資格,甚至其家族也在他從也門走私軍火事發后對其公開指責。但這些反對意見反而讓本·拉登變得更為狂熱。1995年的利雅得美軍軍營爆炸案,以及1996年的達蘭美國軍營爆炸案、1998年的東非美國使館爆炸案都被認為與本·拉登有關。1996年本·拉登與塔利班創始人奧馬爾的結盟也許是其從“后勤者”角色走向意識形態領袖的重要一步。就在當年,本·拉登發表其反對美國的“圣戰宣言”,稱“穆斯林對美國的怒火正在燃燒”,并號召要以游擊戰的形式來對抗美國。1998年,本·拉登更是發布公告,鼓動“對世界每一個角落的美國人展開攻擊是所有穆斯林的個人義務”。同年,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遭到炸彈襲擊,造成200多人死亡,美國認為本·拉登參與了策劃。
定格為世界頭號恐怖分子
實際上,本·拉登最早進入美國中情局視野時只是沙特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最多也只是一名幫助伊斯蘭激進分子的捐資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根本得不到關注。本·拉登1996年的“圣戰宣言”在美國當局看來就像一場滑稽的小丑表演。這個日后成為聯邦調查局頭號通緝犯的人,最開始只是一個居住在山洞里的、沒有國籍的、思想還停留在十字軍戰爭中的沙特人。“幾乎沒有人重視他。他太怪異、太原始,也太遙遠。美國人堅信,現代科技以及自己的理念,一定能防止歷史上的那種野蠻場面降臨到他們頭上。面對這種信心,本·拉登及其追隨者的挑釁姿態就顯得很荒謬,甚至有些可悲。”《巨塔殺機》的作者勞倫斯·賴特曾在書中如此評論。然而,基地組織絕非阿拉伯的古董,本·拉登已經學會了如何利用現代工具和現代思維。他通過電視或者錄像來傳遞信息,甚至用網絡來號召跟隨者,顯然本·拉登很善于運用現代科技的力量來擴大自己在伊斯蘭極端分子中的影響力。直到1999年,美國政府才公開稱,基地組織是一個陰謀殺害美國公民的國際恐怖組織。“9·11事件”之后,本·拉登更是成為美國政府用以判斷敵友的一個標準。小布什在當年公開表示:“每個地區的每個國家現在要作出這樣一個決定:是與美國為友還是與恐怖分子為伍。”“9·11”之后的數個星期,本·拉登在錄像中首次公開承認對此起襲擊事件負責。自那一刻起,本·拉登的個人聲望在伊斯蘭極端恐怖分子中攀上頂峰,而美國則在驚魂未定之后,展開了冷戰后最重要的安全戰略大調整。
拉登之死對
世界反恐格局的影響
當美國總統奧巴馬5月1日深夜就本·拉登被擊斃一事作電視演講時,在白宮外,大批美國民眾在歡呼慶祝這一勝利,全球各大新聞媒體幾乎都在頭版頭條報道了此條重磅消息。此消息一出,美元結束連續多日下跌的走勢而應聲上漲,美元指數一度漲至73以上。以美元計價的原油、黃金和白銀等大宗商品和貴金屬價格隨之下跌。這一系列連環反應,足以說明拉登之死的影響力。更為重要的是,其消失將對世界反恐形勢及反恐格局帶來新的變化和影響。
國際恐怖主義組織遭重大挫折
本世紀頭10年,拉登一直作為全球恐怖主義的象征性人物而存在。這個符號,既因他策劃對美國本土襲擊而強化,也因他刻意指向文明沖突而凸現。在這樣的恐怖戰略中,拉登建立了一個全球性的恐怖網絡,導致全球的非傳統安全風險急劇增加,甚至超過了傳統安全風險。拉登之死有助于削弱“基地”組織和其他恐怖勢力之間的有機聯系,令全球性的恐怖網絡失去協調能力。同時,拉登被美軍擊斃這一事實對其他恐怖主義分子也起到了很明顯的政治威懾作用,意在宣示以后任何恐怖組織膽敢對美國公然發動恐怖襲擊,其頭目會像拉登一樣被窮追不舍。
雖然不能說拉登之死會使恐怖分子徹底消亡,但是,拉登作為“基地”組織乃至世界恐怖分子的精神領袖,其被擊斃對恐怖勢力絕對是重磅一擊,將會大大削弱恐怖分子之囂張氣焰,恐怖勢力將會在相當長一個時期處于一種低迷狀態。即使再出現拉登式人物,也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這對于全球的長久安全是有益有利的。在全球反恐與恐怖勢力的較量中,天平無疑傾向了正義的一方。雖然“基地”組織聲言報復,但多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恐怖襲擊不斷加強防范。因此,在各國加強提高對恐怖襲擊防范等級的前提下,基地組織報復行動計劃的實施和最后效果令人懷疑。
美國國際影響力獲得提升
拉登之死,首先標志著美國“反恐戰爭”取得階段性重大成果。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美國迅速調整了戰略,派兵進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時,在國內將大量國家資源投入到安全領域。盡管美國推翻了塔利班的統治,扶植了新政府,但在美國民眾眼里,只有拉登在肉體上被消滅,才能算是反恐戰爭的告慰。可以說,拉登被擊斃不但顯示了美國堅定的反恐決心和強大的反恐能力,而且使得美國國際影響力大大提振。奧巴馬第一時間宣布拉登被擊斃的“正義終于得到伸張”演講中最牛的一句話是:“今天我們再次印證只要美國下定決心,這個國家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夠實現。”拉登之死是全球反恐戰爭的勝利,根除了世界各國的一個心腹大患,告慰了“9·11”罹難者。但是,奧巴馬本人也是一個大贏家。奧巴馬把擊斃拉登事件發揮到了極致,從第一時間宣布拉登被擊斃的“正義終于得到伸張”演講中多次提到“我自己”,就把自己放在了一個非常顯著的位置。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拉登被擊斃使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民眾支持率大幅上升。《華盛頓郵報》和皮尤研究中心當地時間5月2日晚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奧巴馬民眾支持率從4月份的47%上升至56%。具體到國家安全問題,69%的美國人認可奧巴馬在反恐問題上的做法,60%的人認可其在處理阿富汗問題上的表現。在美國大選到來之際,這對于奧巴馬試圖獲得連任無疑是重大利好。盡管國際社會對擊斃拉登的時機選擇有懷疑,認為美國選擇在這個時候擊斃拉登顯然是經過匠心獨具、精心設計的。但無論如何,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民眾更看好的是拉登最終被擊斃的結果。
世界范圍內新一輪“反恐”角力或將展開
美國為了消滅基地組織和拉登,2001年發動了阿富汗戰爭,推翻了塔利班政府,扶植了新政權,同時和巴基斯坦結成戰略反恐聯盟。2001年以來,美國一直深陷阿富汗戰爭泥潭。據不完全統計,9年來,上千名美軍死于阿富汗,美國在阿富汗戰場的花費已超過1.4萬億美元,巨大的代價拖累了美國的全球軍事戰略。可以說,從白宮到國務院到軍界,美國從阿富汗逐漸撤軍已成為某種共識。奧巴馬上任以來,就制定了從阿富汗撤軍的時間表;然而,只要拉登不死,阿富汗的形勢就難以明朗,因此,撤軍時間表一再拖延。拉登的死訊一宣布,加快從阿富汗的撤軍步伐就順理成章了。既然拉登之死為美國的反恐戰爭劃上了一個階段性句號,那么這個句號之后美國的戰略調整就將展開。其調整后的戰略指向何方,值得人們關注。
對世界反恐之路的冷思考
拉登死了,但恐怖主義不會死,世界范圍內反對恐怖主義的斗爭也不會停止。對由于拉登之死而引發的關于世界反恐之路的思考在各大媒體中引發了一個小小的高潮,各類評論文章爭相刊發。在對拉登之死這個信息的激情過后,我們確實需要對反恐這個話題作一些冷思考。
不必過分夸大拉登之死的實際影響
本·拉登被看作是恐怖主義的頭目,象征意義很大,但他個人的死對美國的反恐斗爭乃至世界范圍內的反恐斗爭實際意義卻很有限,因為恐怖組織并不是只有本·拉登一家,其他很多勢力仍然存在。另外,“9·11事件”后,在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聯合打擊之下,基地組織作為一種網絡化組織已經被嚴重摧毀,其組織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已實現了“去拉登化”、“去中心化”。多年來,本·拉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精神層面,對恐怖活動的實質性領導地位早已式微,其在組織中具有象征意義的領袖角色遠高于實際領導角色。近年來,發生在歐洲的多起重大恐怖襲擊都是本土醞釀的恐怖主義,與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并無直接聯系。對這些零散和新生的恐怖勢力來講,拉登充其量是個“精神導師”,他的生死對這些極端勢力和恐怖組織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即便是對基地組織來講,拉登之死也不會對其運作產生太大影響。海灣研究中心研究員穆哈辛在接受卡塔爾半島電視臺采訪時說,打死拉登已毫無意義,因為拉登早已將其組織化整為零,培訓了大批骨干而且各自為政,在中東和北非等地區的基地組織分支機構相對獨立運轉,不再需要他統一的領導和指揮。同時,拉登被擊斃并不意味著恐怖主義沒有了滋生的土壤,造成恐怖主義的諸多因素也不是一個拉登之死便能被消滅掉的。
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不會很快消除
滋生恐怖主義的原因有很多,只要這些根源還在,恐怖主義就不會從這個世界消亡,它不會因為一個人的死亡而消亡。這些根源首先體現在政治上的不合理,這是滋生恐怖主義的主要原因。當某一個國家的政權體制出現意識形態危機時,各種反對團體便應運而生。另外,在跨國間權力斗爭出現不均衡時,一些力量弱小的集團或個人,為了向國際對手“討取公道”,很可能通過極端暴力手段制造血案。這也是現在巴勒斯坦為什么會以人肉炸彈去對付以色列的原因,因為他們除了此舉外,實在找不到可以和以色列先進坦克、戰機相抗衡的資本和條件,否則誰又愿意“以卵擊石”呢?
經濟上的不公平是滋生恐怖主義的根本原因。南北關系惡化和最不發達國家貧窮加劇是產生恐怖狂熱勢力的溫床。強者更強,弱者更弱。全球化既給了富人和想成為富人者以機會和想像,也給了窮人和絕望者以新的反抗手段。索馬里人因為經濟上實在一貧如洗,于是一些人為了生計,拿起武器,靠當海盜為生,靠打劫為業,這是他們無奈的選擇,也是絕望者對經濟不公平的另類反抗。
錯綜復雜的民族、宗教、文化矛盾,這是恐怖主義泛濫的重要原因。現代世界在造就物質輝煌的同時,也使信仰、宗教的認同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終于導致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之間的沖突,這是恐怖主義泛濫的文化根源。世界的很多沖突歸根結底是文化的沖突。因此,反恐必須標本兼治,鏟除恐怖主義的土壤,才能維護全人類的和平與福祉。如果為了反恐而反恐,結果則可能是“越反越恐”。
以“反恐”之名行“排異”之實仍將長期存在
“9·11事件”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傷害,也使美國從冷戰結束后尋找“假想敵”進行戰略攻擊,轉而對現實敵人進行戰略攻擊。在這個進程中,美國與傳統的國際政治盟友分分合合,其戰略安全邊界也不斷外移。反恐的正義性與現實戰略利益考量互相交織,不僅造成了新的民族矛盾和宗教沖突,也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反恐雙重標準的疑慮。從這個角度說,拉登之死意味著對于美國“9·11事件”完成了一個交待;但是,對于國際社會而言,拉登之死還沒有完成交待。拉登之死,實際上為美國的全球安全戰略開啟了一個新的窗口。對拉登成功實施的斬首行動,對世界其他地區或國家不聽美國話的領導人或許都是一個危險的警告和壓力,如果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美國會不會以“反恐”之名對其進行精確鏟除?如現在的利比亞,美國在1986年就曾以反恐的名義對其進行過長途空襲,那時也曾試圖對卡扎菲進行斬首,但“心有余力不足”,現在美軍具備了這樣的能力,只要戰略形勢需要,取卡扎菲的首級對美軍來講并非難事。以“反恐”之名行“排異”之實必將成為美國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重要戰略選擇之一。改造大中東,掌控世界資源核心之地的主導權,重新界定和處理與印巴的關系,積極構建東亞新秩序……所有這些都是美國在后拉登時代必將實施的戰略選擇,這些戰略調整也都將對我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安全環境和戰略利益產生重大影響,我們必須早有謀劃,有針對性地做好應對之策。既要維護國際反恐大局,積極參與國際反恐合作,又要著眼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強身健體”是我們提高對恐怖主義威脅免疫力的不二選擇,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
編輯/魏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