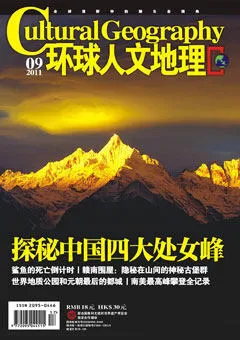與九月有關的旅途和思念
構思這篇卷首語的時候,我剛完成了玉龍雪山的自駕穿越,許巍低沉的聲音彌漫在我的汽車曲庫里。給遠方的家人電話報完平安,我突然想起,原來現在的時間就要進入中秋了,是啊,9月已經到來,那個月亮最圓的月份也即將隨之而來。
或者說,那個讓人浮躁而思念涌動的秋季就要到來。
那其實是一個充滿思念的季節。而這個季節中的思念,有時候是因為對未知世界的渴望——
1519年的9月,一支由5條海船、234人組成的遠航隊從西班牙塞維利亞城的外港出發,去證明“世界是圓的”。在只見海水不見陸地的漫長日子里,船上的柏油被曬化了,飲水變臭,餅干變成粉塊,蛆蟲在其中蠕動。沒有新鮮食物,船員們只好吃牛皮和艙中的老鼠,可怕的壞血病更是奪走了許多船員的生命。最終,他們歷時3年,在相繼發現了“麥哲倫海峽”與“太平洋”后,船長費迪南德?麥哲倫被蠻族所殺,他的助手埃里?卡諾于1522年9月6日帶領幸存者回到西班牙,這時他們只剩1艘船和18個人……
有時候,九月這個季節又變成了遠隔重洋卻依舊心系家鄉的落魄情節。
1903年9月,修建了6年的膠濟鐵路開始把青島和濟南連接在一起,后來的事實證明,這條德國人鋪設的鐵路,把李鴻章、翁同和、袁世凱、菲舍爾、錫樂巴等人的名字都鑿刻在從柏林運來的鐵軌上,但是,它卻單單將一位曾經叱詫風云的“維新派”人物遺忘——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沒能成為這條鐵路初次運行的見證人,流亡海外的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為什么會失敗,于是就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郊區買下了一個小海島,署名為“北海草堂”,躲在里面整日讀書……
還有時候,九月這個季節是理想的出發點,即使死亡也在所不惜。
1967年的9月,一位名叫切?格瓦拉的人,帶著對自由的思念,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他所率領的游擊隊中出現了逃兵,向玻利維亞政府軍透露了格瓦拉游擊隊的營地。數天后,當格瓦拉在尤羅山峽巡邏時,政府軍捉住了這位幫助卡斯特羅成立古巴共和國,卻又為了理想重新開始的傳奇人物。隨后,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大使館和玻利維亞軍方的共同策劃下,切?格瓦拉被俘大約22個小時后,政府軍就在恐懼中向他扣動了美式卡賓槍的板機——他們再清楚不過了:假如讓這位英雄在法庭上發表自我辯護的講演,那么他將贏得廣泛的同情,西方各國的知識界和輿論界都將掀起聲援他的浪潮……
回到現實中來,編輯部的9月,自然也充滿了思念,因為我們一直都在路上。有人說,旅行就是為了思念家的感覺而去的。
本刊著名的撰稿人金飛豹,用“踏遍地球”來形容他絲毫不為過,從最冷的南極北極到最熱的撒哈拉沙漠,他都留下過足跡。當我們聊起這個關于思念的話題時,他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思念情感。再如剛剛背包徒步探險嘉陵江源頭歸來的本刊記者嚴含,在過了數日“啃干糧、喝涼水、草為床鋪天為被”的野外生活后,回到家時連連感慨:“在家時就想出去,出去后才知道,出去的目的就是為了回家。”
我贊成他的說法。在路上的思念,真的可以讓我們想得更遼闊一些,寫得更美好一些。我也很高興我的同事們能夠在這個秋葉即將飄飛的季節里,繼續保持著這樣的行走熱情,我相信,帶著這樣的思念,我們會無所畏懼,即使是攀越群山,馳騁高原,抵近藍天。
當然,我也希望我們的努力能夠以這樣的方式獲得欣賞:比如當親愛的你瀏覽完本期雜志之后,會真正地感到若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