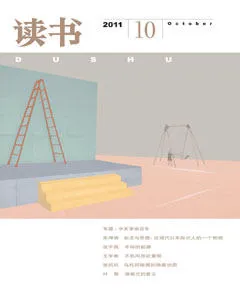被依賴的入侵者
村上春樹曾經以“到底有誰能區(qū)分下午四時半的暮色和下午四時三十五分的暮色?”(村上春樹:《雜志的快樂讀法》,載村上春樹隨筆系列《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來》,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二○○四年版,165頁)做比喻,來形容當今社會同質化的雜志出版狀況,種類紛繁與各具特色似乎難以兼顧。作為職業(yè)作家的村上春樹,與出版業(yè)、媒體的聯系自然是難以割裂的,那么,村上春樹的文本中有關新聞媒介的描寫,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村上本人對媒介這一存在的思考呢?是否存在類似于所謂村上春樹的“媒介觀”之類的東西呢?
可以說,在村上春樹的文本中,能夠讓讀者意識到其明確功能的段落和對象是不存在的,仿佛所有的敘述都是依照事物的自然呈現和發(fā)展態(tài)勢而渾然天成,雕琢和刻意的味道似乎一點也沒有。所以,硬生生地試圖解讀村上春樹文本當中的某一元素或對象這種行徑,就其本質而言,是很不村上春樹的。然而,村上文學又往往以消解意義、故弄玄虛、煞有介事的后現代形態(tài)呈現在讀者面前。倘若忽略行為本身的意義和目的,就村上春樹文本中的“媒介意識”,乃至由此推衍而來的“媒介觀”加以所謂的“解讀”與“剖析”的話,那么這番“煞有介事”也不妨被當做以村上春樹的方式對其文本的一種理解吧。
村上春樹曾在隨筆中表達過他對現象和觀念的懷疑,以及他帶有懷疑主義色彩的哲學傾向,認為事物中必然包含著樸素而自然的“疑念”,而“從懷疑當中陸續(xù)不斷地產生諸如‘大體固然如此而實際是否這樣”、“其實可能這樣”的假說,各種各樣的假說聚集將生成一個重要的可變的要素。毋寧說,“疑念”是變化的動因。“可是倘若這一個個假說在某個時候固定了、僵化了,失去本來的可變性而變成無人不曉的停滯的命題,那么,其中勢必產生某種宿命的斯大林主義。就文學世界而言,檔次不高的人就有可能將這里作為結局死死抓住不放而形成其‘蜘蛛網’。我所擔心的乃是這種斯大林主義式的細部僵化傾向……”(村上春樹:《關于精力旺盛的女人們的思考》,載村上春樹隨筆系列《終究悲哀的外國語》,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二○○四年版,110頁。)“懷疑”和“反對僵化”似乎是村上春樹所持有的重要哲學思考之一,也是他對大眾媒介進行反思的哲學基礎。如果媒體所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大體固然如此而實際是否這樣”的世界,那么,這樣的“世界”之于人類的意義又是什么呢?媒體的言說如果也被看做村上所謂的各種“假說”之一的話,充斥現代生活每個角落的“媒介假說”又是否已然固定、僵化,而成為一種停滯、板結了的“蜘蛛網”呢?村上筆下的媒介不乏這種“失去了可變性”的特征,并在此基礎之上思考媒介之于當代社會、現代人的意義。
一、作為入侵者的媒介
生于一九四九年的村上春樹,其最敏銳的青春時期應該是日本戰(zhàn)后的七十至八十年代,而其間不僅僅是日本私營媒體發(fā)展的高潮時期,更是電視業(yè)的黃金年代,稱其為日本的“電視時代”也毫不過分。在村上的小說中,看電視的人物并不多,而以讀報紙為每日必修課的主人公倒是不少,大概從某種程度上顯示了村上本人的媒介偏好。然而,關于電視,村上春樹非但不是沒有關注,反而是有其特殊思考的。僅從題目出發(fā),就很容易注意到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說《電視人》所可能含有的與大眾媒介的關聯。
“電視人”在主人公“我”最不喜歡的時間內(周日傍晚)毫無征兆地出現,其間,“我”的生理反應是“太陽穴神經與肌肉相牽扯的、輕微的疼痛”。不難體察開篇便奠定的莫名焦慮的情感基調。“電視人”服裝精密地統(tǒng)一,儼然一副“略小于實物的精密塑料組合模型”。“電視人”的機械狀態(tài)是其突出特征,以動作代替思維,以目標代替目的。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電視人”對“我”“徹底無視”的態(tài)度:“不是自我辯解,任何人假如被近在眼前的他人如此徹頭徹尾的不放在眼里,想必連自己都對自身是否存在產生疑念。”最后,“電視人”在“我”無法理解的范圍內,以篤定的言說命名著事物,預言著“我”的生活。在未言明結局的小說中,“電視人”幾乎侵占了“我”生活的角角落落,而“我”最終以慵懶和無以為繼的狀態(tài)“萎縮干癟,化為石頭,一如其他人”(此段落引文皆出自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電視人》,上海譯文出版社二○○二年版,2頁)。《電視人》或許可以被看做關于現代人媒介生活的一則寓言。“電視人”難以描摩的外形,無所顧忌的行徑、讖語式的言說,對“我”的生存空間不由分說地侵占,以及“我”在家庭生活和工作場合中的失語,這一切都讓我身陷困境,產生對“生的意義”和“自我存在”的深深懷疑。
如果這種隱喻性分析成立的話,那么“電視人”所帶來的毫無個性可言的機械復制性、空洞無物、對個體生活無孔不入的侵吞狀態(tài),無疑是當今媒介社會的真實寫照。電視在這部短篇小說中,扮演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入侵者,我們也可以在村上春樹的另一部小說《天黑以后》中發(fā)現這一意象的重復出現。在主人公淺井愛麗沉靜的睡眠中,她房間里原本關閉的電視機在無人操控的情況下開始“微微眨閃”。“電視機是房間里的新的入侵者。當然我們也是入侵者。但與我們不同的是,新入侵者既不安靜又不透明,而且沒有中立性。它毫無疑問的企圖介入……這個房間,我們直觀地覺察到了這樣的意圖。”(引文出自村上春樹著,林少華譯:《天黑以后》,上海譯文出版社二○○五年版)
自從電視在入侵人類的戰(zhàn)爭中大獲全勝之后,電視便開始了對人類進行統(tǒng)治的新紀元。正如“我”無論主動被動,都生活在“電視人”(電視)構筑的信息空間之內,并以此作為參照系,從而得出自身存在及與外部世界關系的判斷。按照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中的觀點,存在的意義首先要從時間的角度來理解。當我們破除形而上學的傳統(tǒng)來理解“存在”的時候,我們自身的存在也并不是一種自在自為的“存在”,而是在“我”或“我們”這一主體所能夠理解的范疇內去探討的“存在”。那么,這樣一種“存在”就勢必需要在自身與周圍世界的關系當中來理解。今天,大多數個體心目中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媒介構筑的世界。
與此同時,“人是一種時間性的存在,而且我們的時間性是每個人必有一死的時間性,即與無限的宇宙時空相比的有限性的時間性。……從人這種存在對自身存在的意義的理解和關切可以看到‘此在與時間性’的緊密關系:此在就‘是’時間性。此在與時間性是‘存在與時間’的一個方面,也就是從‘此在’來理解‘存在’”(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江蘇人民出版社二○○七年版,31-32頁)。村上春樹在很多作品中將媒介的存在當做背景來描寫,而這種媒介背景所代表的正是與主人公的言行共時的、平行的世界。可以說,這種“此在”和“共時”的平行關系,增加、甚至說確認了主人公的存在感,也增加了作品本身的真實感,增加了讀者與作品之間的共鳴度。在《好風長吟》中,村上春樹大量、多次描寫收聽直播類廣播節(jié)目的情景,以及廣播的內容。廣播情緒飽滿、熱鬧喧囂,而現實生活平靜、平淡,“共時”并不意味著“同質”,但“共時”的世界成為“此在”的另一端,是截然相反卻相反相成的“存在”。相形之下,廣播節(jié)目的始末,日復一日的定期播出,成為“時間性”的一種表征,自我的存在正因為媒介所具有的這種帶有流逝感的、無可抗拒的“時間性”而得到印證。
二、作為平衡感來源的媒介
不單單是針對電視,村上春樹的文本中往往流露著一種對大眾媒介不屑一顧的情緒,然而在這種情緒之上,卻又有一種無可奈何的對媒介的依賴,其文本中也并非只是對新聞媒介消極面的反復言說。正如羅杰·西爾弗斯通所說:“對社會現實來說,媒介不只是一種干擾,而且也是一種支撐。”([英]羅杰·西爾弗斯通著,陶慶梅譯:《電視與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27頁。)
在《象的失蹤》這部短篇中,“我”對于鎮(zhèn)上飼養(yǎng)的大象離奇失蹤這件事有著莫名其妙而又無法舍棄的關心。雖然“我”對媒體報道極不信任,但卻沒有拋棄新聞報道,反而將報紙上關于大象失蹤的報道做成了剪報集,并時時關注NHK電視臺關于這一消息的新聞節(jié)目。事實上,“我”從一個特殊角度偷窺大象的生活,從而了解了大象是如何失蹤的這一旁人在日常經驗下無法理解的“事實”。與這一失衡的“事實”相比,差強人意的新聞報道卻始終恰如其分地維持著一種機械的平衡感。這里的所謂“平衡”,并非新聞報道理念中不偏不倚的、“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的專業(yè)主義原則,而是在邏輯和認知上尋求一種令人舒適的平衡感。在“我”看來,新聞媒介不過是程式化地“處理”事件,并以有平衡感的方式將其呈現,“事件”終將永遠地消失于新聞媒介之中,正如“報紙幾乎不再有大象的報道。人們對于自己鎮(zhèn)上曾擁有一頭大象這點似乎都已忘得一干二凈”(本段引文皆出自村上春樹著,張潔梅譯:《大象失蹤》,載《好風長吟》,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在村上春樹的文本里,新聞媒介頗具平衡感的技術化報道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事實真相”的扭曲,而“我”、我們正生活在這樣一個由新聞媒介構筑的平衡的世界之中。媒介無時不在制造著焦慮,又不斷地以媒介自身的邏輯來消解這種焦慮。短篇小說《中斷的蒸汽熨斗把手》諷刺了媒介邏輯對藝術邏輯的左右,以及主人公“我”的生活由此而產生的失衡。小說的結尾處,“我”的生活終究復原,而恢復平靜的方式,仍然是求助媒體,以媒體行為操縱了現實結局。正如羅杰·西爾弗斯通所說:“電視節(jié)目制造出了焦慮,但也調節(jié)并解決這些焦慮。”([英]羅杰·西爾弗斯通著,陶慶梅譯:《電視與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二○○四年版,22頁)媒介制造了這個世界的幻象,或許并非全然的扭曲真實,但絕然不是真實本身。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個世界就是在電視上看到的。正如后現代主義大師詹明信所指出的,在后現代社會中,“人體未能在空間的布局中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們便無法以感官系統(tǒng)組織圍繞我們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過認知系統(tǒng)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總體設計中找到確定自己的位置方向。人的身體和他周遭環(huán)境之間的驚人斷裂,可以視為一種比喻、一種象征,它意味著我們當前思維能力是無可作為的”([美]詹明信著,張旭東編,陳清僑等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三聯書店一九九七年版,497頁)。人們往往需要將自身生活的經驗與媒體描繪的城市空間或世界圖景相印照,以此來撫慰“缺席的總體性”所帶來的不安。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媒體描繪的世界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相對封閉的平衡的環(huán)境,而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就是媒體所描繪的環(huán)境。
或許媒體提供給我們的環(huán)境遠不等同于真實的世界,但是當代社會中的人們已經適應這個平衡而舒適的環(huán)境了,并不會意識到我們實際生活在一個超真實的類像世界中。相反,大眾媒介提供給我們的模式化的世界,早已塑造了我們對這個世界先驗的認知,這種認知形成之后,從媒體中去接受應合我們腦中先驗概念的話語,是尋找生活中平衡感的重要方式。在《1Q84》中,職業(yè)殺手青豆在完成一次任務之后,緩解神經亢奮的方式是喝酒、一夜情,并在之后一條不落地“把十一點的新聞一直看到最后”。在這里,村上春樹不厭其煩地記述了電視新聞的內容:中東的戰(zhàn)爭、美國的競選、人類對太空的探索、事故、災難、金融市場等等。新聞的內容雖無不意出其表,卻又在某種程度上屬于意料之中。模式化、同質化的電視節(jié)目在長期的播出中生產了觀眾的預期,而保持這種模式便能很好地投契觀眾的預期。青豆通過收看新聞,感知到世界依舊,漸漸從“任務”中抽離,重回平靜。
或許可以說,村上在小說中展現了他對大眾傳媒平衡功能的思考,而這一思考正源于他對這個失衡世界的認識。大眾傳媒模式化地塑造了我們對于世界的認知,完成我們對總體性的想象,并且通過對這種模式的重復,賜予我們不可缺失的平衡感。
三、作為自我比照物的媒介
世界上本沒有大眾傳媒,大眾傳媒像外星人入侵地球一樣入侵了人類田園詩般的平靜生活,并以其自身相對封閉、平衡的話語模式告訴我們世界的樣貌。無論是作為存在感的依據,還是平衡感的來源,大眾傳媒無疑都成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安慰劑。然而,對于村上春樹而言,他所想要表達的東西遠非僅此而已。村上春樹在《好風長吟》中曾經有過類似認識論的表述:“我們的各種努力認識和被認識對象之間,總是橫陳著一道深淵。無論用怎樣長的尺都無法完全測出深度。”正如杰·魯賓指出的那樣,寫作之于村上春樹,是“自愿繼續(xù)測量和實驗,渴望確認自我和世界之間的關系,并檢驗這兩者間交流的本質,觀察夢想與感覺能進入‘彼一世界’的程度、所能達至的深度,確認現實和幻想的本質”([美]杰·魯賓著,馮濤譯:《傾聽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上海譯文出版社二○○六年版,53頁)。毋寧說,村上春樹小說中對大眾媒介的描寫也是服務于認識自我和世界這一終極目標而存在的。
認識自我,是村上春樹小說的重要主題,而對自我的認識無法脫離歷史與現實,需要在動態(tài)的、循環(huán)的背景中完成。王向遠在《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中認為:“如何描寫自我,如何表現自我,取決于如何處理自我與時代、自我與社會的關系。”(王向遠著:《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319頁)對于當代人而言,大眾媒介成為我們認識時代、認識社會、認識自我最重要的途徑之一。村上春樹的小說中,大眾媒介往往以環(huán)境和背景的姿態(tài)出現,并且往往與主人公的心境或現實處境形成對照。
在《1Q84》中,熟知的世界隱退,陌生的世界登場。主人公青豆明確地意識到自我的處境,是在《每日新聞》關于“一次警匪交戰(zhàn)的新聞”這一報道的對照之下。《好風長吟》中,在夢境與現實還未厘清的早晨,“我”剛剛從噩夢中驚醒,“電視機里新聞播音員自以為是地斷言今天將達到本夏最高溫度”。與困惑迷茫的人生相對照,電視里的聲音總是篤定而自信的。在《螢》中,與“我”“無可名狀的心緒”、“無可奈何的悲哀”相對照的,是每周六晚上電視照例播出的棒球轉播節(jié)目。“我把橫亙在我與電視機之間空漠的時間切為兩半,又進而把被業(yè)已切開的空間一分為二,如此反復無窮,直至最后切成巴掌大小。”規(guī)律播出的電視節(jié)目像鋼筋混凝土建筑一樣幾乎不含有感情的成分,較之孤寂、柔弱的生命體驗,媒介以熱鬧的表象顯示出一副帶著冰冷感的硬度和堅強。“我”在內心里通過幻想的空間切割,仿佛默然地汲取著某種安慰。在短篇小說《袋鼠佳日》中,“我”的生活平淡無奇,不僅如此,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記憶。“直到月末收報刊費的人來了,我才突然發(fā)現一個月的時間已經過去。”當今天了無新意,就無法與昨天相區(qū)別。《五月的海岸線》也延續(xù)了對這種日常性的描述:“一切的一切,都與十二年前無異,沒有絲毫改變,包括透過強化玻璃的五月陽光。干燥的火腿三明治的味道,索然無味地瀏覽經濟報道的那位年輕商人的側臉。報紙的標題告訴人們,大概幾個月之內,歐共體就要開始實施強硬的對日進口限制措施了。”新聞媒介永遠以動態(tài)的事件作為報道的對象,規(guī)律地出版、運行,仿佛勤奮而不遺余力地告知人們這個世界的變化。而這種對變化的追逐竟成為機械與恒常,日常在此映襯之下反而顯得無常。
《1Q84》中,主人公天吾的父親是NHK的收款員,每到周六周日就帶著還是孩子的天吾挨家挨戶地收取NHK收視費,他一生以此為業(yè),生前的遺愿就是堅持身著NHK的工作服入葬。與天吾穿插兩個世界奇譎的人生軌跡相對照,父親毫無個性可言、循環(huán)往復的職業(yè)屬性似乎是現實人生的寫照。如果在這里,這一職業(yè)的特性可以看做媒介屬性的延伸的話,那么這一屬性最終并不是被否定,而是被極大地升華了。“這套縫著NHK標志的制服,就像他皮膚的一部分。這個男人是穿著這身制服出生,再裹著它去火化的。實際一看,連天吾也想象不出他在人生最后時刻穿的衣服,除了這個還有什么更合適的。如同瓦格納歌劇里登場的戰(zhàn)士裹著鎧甲被送去火葬一般。”天吾曾因為父親帶他一同去收收視費為恥,對刻板木訥的父親也并不親近。然而,在父親去世的時刻,NHK收款員這一職業(yè)所代表的無意義的循環(huán)特質卻被神圣化了。
是否可以理解為,當村上春樹以媒介的刻板、機械為映照,而尋求自我的個性與意義時,最終的認識卻是虛無。循環(huán)就是生命的原貌,完成周而復始的日常大概就是生命的全部意義。媒介屬性所表現的就是現實最本源的屬性。
大概并不僅僅是村上春樹一人,文學創(chuàng)作者對于媒介世界或多或少有著相當程度的不滿足感吧。大眾媒介的敘述往往焦灼于單一事件或細節(jié)上的真實感,文學創(chuàng)作則往往指向帶有主觀性和體驗性的現實感。這一點,村上春樹曾在《奇鳥行狀錄》中有所表達,對于電視新聞播報的雪天車禍,“我”的感受是:“對于我,這類消息委實過于現實,同時又毫無現實意味。我很同情死于事故的三十七歲卡車司機。……我對他的同情并非個人同情,只是對這場飛來橫禍的一般同情。對于我,這種一般性既可以說是現實的,也可謂毫不現實。”就大眾媒介而言,敘述和解釋一般性事件,并由此告知人們現實是什么;就文學創(chuàng)作而言,現實與否,同個體的參與感緊密相關,現實是什么,總是夾雜著個人主觀性的判斷。伸手觸摸現實還是隔岸觀火接受現實,恐怕也是文學和媒介的不同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上的差異很可能是村上春樹對媒介話語感到不滿足的根本原因,也成為村上春樹思索現實、存在與自我的重要途徑之一。正如杰·魯賓所言:“將‘存在’和‘非存在’進行比照是村上春樹的癖性,亦是他所有作品的基礎。他喜歡在作品中并置兩個平行的世界,其一顯然是臆造的,另一個則較近于可認知的‘現實’。”([美]杰·魯賓著,馮濤譯:《傾聽村上春樹 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上海譯文出版社二○○六年版,125頁)大眾媒介并不見得是村上春樹用于表現作品主題而精心操控的重要元素,但很顯然,這一元素因其在現實生活中所具有的難以忽略的認知功能,也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出現在村上的文本中的必然性。
村上春樹注意到新聞媒介這個人類生活的入侵者,也注意到了其難以忽視的影響力。很顯然,村上春樹對媒介構筑的現實認知圖景斷然是不信服的,他所秉持的媒介觀是建立在存在與虛無的哲學思考之上的。媒介構筑的圖景自然是一種幻象,而這種幻象就是每一個生活在其中的個體尋求自我存在的依據,映照自我形象的鏡子。
如果說個體需要以媒介為參照方可感知平衡和方位,那么我們便是以虛幻為坐標。在村上春樹的文本中,媒介作為一種被表現的意象,映射出作者對生命的終極思考,以非本質的媒介來表現本質,以非現實的景觀來表達現實。正如村上春樹所言:“事實上的出入甚至可以提高真實性。”虛幻與真實的關系并不一定是表現與被表現,假如真實本身存在的話,對于真實的一次次有所偏頗的表現,是否會以無限循環(huán)的方式距離真實越來越近呢?雖然無人知曉答案,但也并非絕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