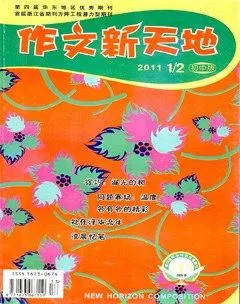130℃的煅燒
伴隨著曙光劃破黑夜,我雙眼的淚跡也凝結(jié)在了雙頰上。深秋的風吹過,回憶不露聲色裊裊地舒展開來。
我的外公是一個陶藝工作者,在他的工作室中總是存放著很多精美絕倫的陶器。可是我并不喜歡,因為我不喜歡那些脆弱易碎的靈魂。直到我的外婆去世的那一年,那時候的我還很小很小,小到我已經(jīng)失去了親人,都還不知道。我像只小貓一樣,被父母拖到東拖到西,只是在經(jīng)過外公的房間時,透過細細的門縫,我隱約地看到了一個哭泣著的背影。我小心翼翼地弓著腰走進外公的房間,外公早已察覺到我,他只是一言不發(fā),他的頭深深地埋在雙膝間。“你知道嗎?”一個悶悶的聲音從他的雙膝間傳來,“不要以為它們很脆弱,其實它們的內(nèi)部十分牢固,它們經(jīng)過無數(shù)次的打壓、碾磨和130℃的高溫鍛燒……”“130℃!”我喃喃道。外公抬起頭來,他臉上的淚痕早已干了,只是那點點悲傷還嵌在他那一道道皺紋里,深深地嵌著。他摸摸我的頭,說:“你還太小,總有一天會明白的。”
在外婆去世之后,外公經(jīng)常一個人呆在工作室中,偶爾我也會去。我對陶藝一竅不通,我也很害怕那臟兮兮的泥巴,可是外公卻總是笑呵呵地抓著我的手,耐心仔細地教我。我以為會一直在外公的呵護下擺脫對于陶藝的疏遠。但終于有一天,他的雙手失去了溫度,我永遠失去了他。那時候,我已經(jīng)懂了,已經(jīng)明白自己的世界里又少了一份炙熱的呼吸。我開始彷徨,把自己整天鎖在家里,手里緊緊攥著一個外公在生前給我燒制的小掛飾。我的靈魂被一根叫悲傷的線牽著,不斷扭曲著。
無論怎樣,在每周六晚上我還是堅持去參加陶藝培訓班,因為只有在雙手觸到泥土的那一瞬問,我才能感受到外公曾經(jīng)所給予的溫暖。放學后,我仍坐在教室里,看著那一只只不成樣的杯子,仿佛像我一樣,那么易碎。我不禁偷偷哭泣。老師是外公的好友,他只是看著我哭,聽著我訴說。他拿起一只小小的杯子說:“你不要小看它,它可是經(jīng)過無數(shù)次的打壓、碾磨……”“130℃!”我想也沒想就蹦出這個溫度來。老師愣了一下,然后微笑著點頭。他和我并排坐在土窖前,輕輕地對我說:“你看,它們是多么幸福!”看著土窖中被燒灼的碗,我不禁轉(zhuǎn)過頭來看著他。“它們只要心存理想,堅持著熬過這一段時間,那么它們出去后將會得到很多人的青睞……”我輕笑了一聲。“難道不是嗎?”他嚴肅地反問我。我把玩著手中的杯子,是啊,在成形之前它們都得經(jīng)過高溫的鍛燒,我就好像那堆爛泥巴,也許不會,外婆的去世就是那陣陣高溫。
有人說,風兒不能再回到它所經(jīng)過的地方,無論我在心里如何默念重來,我的外公都不可能再回到我身邊了。但我相信他一定在守護著我,就像當初他握著我的手教我陶藝一樣。
他的溫度有時候像土窖中的130℃高溫,讓我內(nèi)心備受煎熬:他的溫度有時候又像記憶中的雙手,會溫暖我冰涼的淚珠。不管怎樣,我明白他在我身邊,他的溫度在我身邊,指引著我去面對應(yīng)該自己面對的無法逃避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