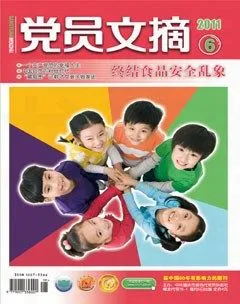食品安全亂象頻現尋因
前不久,央視曝光了河南孟州等地采用違禁動物用藥瘦肉精飼養的有毒豬,流入了南京等地市場以及雙匯集團下屬的濟源雙匯。該報道一出又引起了食品安全領域的一場地震,時隔半個多月,媒體又曝出上海部分超市多年來銷售染色饅頭。
食品安全問題似乎成了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縈繞在我們餐桌周圍……
多頭監管 漏洞百出
在近期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監管的漏洞又一次暴露出來。為什么有著一層層的監管體系,卻一再發生這類事件,人們開始對餐桌上的食品產生懷疑,到底誰來保障我們的食品安全?
抽查代替普查,無良商人就有了可乘之機。上海染色饅頭生產廠家的相關人員在記者暗訪中表示:一般來說,一個月抽查一次,他們來檢查,我們就把東西拿到辦公室給他們檢查,不讓他們去車間。在進入超市環節中,超市相關人員表示色素測不出來,只能測大腸桿菌和細菌總數這種東西,但實際上,最后什么檢測都沒做就讓染色饅頭輕易地進了流通環節。
在瘦肉精事件中,相關監管部門形同虛設,“潛規則”成了公開的秘密。事實上,通過使用鹽酸克侖特羅快速檢測試紙對豬的尿液進行檢測,就能快速篩選出喂了瘦肉精的生豬。按照規定,豬尿取樣應該由檢測人員來操作。但是河南孟州的養豬戶說,當地一些部門所進行的“尿檢”,都由養豬戶自己采集豬尿樣品。如此檢測,最終的結果可想而知。
那么又怎么過動物檢疫這一關呢?原來在河南孟州市、沁陽市、溫縣和獲嘉縣,用瘦肉精喂出來的所謂瘦肉型健美豬,每頭豬花兩元錢左右就能買到號稱“通行證”的檢疫合格等三大證明,再花上一百元打點河南省省界的檢查站,便可以一路綠燈送到南京的定點屠宰場,需檢測瘦肉精,每頭豬交十元錢就能得到一張“動物產品檢疫合格證明”。有了這張證明,瘦肉精豬肉就能堂而皇之地進入南京市場銷售了。
而多頭監管往往是,有利搶著管,無利都不管。沈陽市發現了藥水豆芽,記者舉報投訴,打了一圈電話,竟被四個部門推了回來:質監部門稱自己負責食品生產加工環節,市場上的豆芽歸工商部門管理;工商部門稱豆芽是初級農產品,應該歸農業部門管;農業部門稱沒有拘留資格,很多違法商販在檢驗結果出來前就逃跑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則稱,自己只負責檢測飯店或食堂里做好的飯菜……四頂“大蓋帽”竟管不了一根豆芽?
分段監管、“多龍治水”,最怕的是推責任、“踢皮球”。“目前,我國采取了分段監管和品種監管相結合的模式,實際工作中確實也存在監管邊界不清、監管重復和空白并存等問題。”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張勇說,“今后,我們將繼續加強綜合協調能力建設,既要強化各監管部門的工作,又要不斷消除監管漏洞、完善全程監管措施。”
為搞好分段監管銜接,2010年,商務部會同財政部在上海、大連等10個城市啟動了肉類蔬菜流通追溯體系建設試點。該體系是為了使各流通節點的信息互聯互通,形成來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證、責任可追究的質量安全追溯鏈條,實現肉菜質量安全的全過程無縫隙監管。
誠信缺失 道德滑坡
上海染色饅頭事件發生后,廈門執法部門在一家昏暗潮濕、屋頂和墻壁都已發霉變黑的黑作坊也查出了染色饅頭。此處生產的玉米饅頭、全麥饅頭,全是用添加劑調制而成的,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面對執法人員,老板還一直叫屈:“像我這樣做饅頭,算有良心的了!”
以雙匯為例,雙匯曾將“誠信立企、德行天下”作為企業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曾以“十八道檢驗、十八個放心”作為廣告語,向社會宣揚自己奉行的商業倫理、堅持的誠實信用,以及對消費者的認真負責。如果真能用這些箴言有效地自律,即使前有養殖戶添加瘦肉精,后有檢疫部門監管虛設,瘦肉精也一定會被拒之于千里之外。但是,雙匯顯然沒有依據商業道德進行嚴格的自我管理,結果,“十八道檢驗”道道落空,“十八個放心”個個讓人懷疑。含有瘦肉精的雙匯產品昭示著企業的無良,商人的少德。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說,近年來相繼發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等惡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
標準不清 令人茫然
去年8月初,“圣元奶粉致嬰兒性早熟”的傳聞讓不少家長人心惶惶。隨后不久,衛生部通報調查結果:奶粉檢測結果符合國內外文獻報道的激素含量范圍,湖北三例嬰幼兒單純性乳房早發育與食用圣元優博嬰幼兒奶粉沒有關聯。
今年4月11日,武漢市,全國人大常委會《食品安全法》執法檢查匯報座談會現場,這個發生在當地的食品事件再次成為討論熱點。說起當時的情形,一位與會者說:“醫生講醫生的,專家講專家的,沒有統一的標準。”“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國家的奶粉標準中,沒有定激素的本底是多少。哪一些屬于內源性的?哪一些屬于外源性的?”安徽省質量技術監督局總工程師程靜表示,“那問題說得明白嗎?說不明白。”
事實上,食品安全標準的不統一、不完整,或多種標準沖突,不僅困擾著執法者,也讓守法的企業茫然無措。令人欣慰的是,《食品安全法》實施后,各項工作有了良好進展:2009年11月,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家委員會正式組建,組織對食品中的有害物質、嬰幼兒奶粉中性激素等開展風險評估。2010年1月,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審評委員會成立。當年,共組織審議通過了246項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草案,目前已公布標準172項,其中包括68項乳品、102項食品添加劑產品標準、2項農藥殘留限量標準(含66種農藥)。
到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了由省、市、縣三級監測點組成的全國食品安全風險監測網絡。但是,總體來看,我國食品安全風險監測評估和標準體系建設仍處于起步階段。據了解,我國僅有30%的省級疾病防控機構能夠承擔2010年國家計劃的全部監測項目。在“圣元奶粉”事件發生時,全國的檢測機構中具備檢測食品中性激素能力的僅有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這些與實現早期發現食品安全問題隱患的要求相去甚遠,也難以適應我國食品安全相對復雜的形勢和繁重的工作任務,所以,迫切需要有關部門加大支持力度。
以罰代刑威懾偏低
“我不會吃的,打死我都不會吃,餓死我都不會吃,我自己做的東西我知道能不能吃。”上海染色饅頭事件中,饅頭制作工人的一席話令人心驚。
毒大米、地溝油、問題奶粉、化學火鍋……一樁樁食品安全事件折射出食品經營者的利欲熏心和誠信缺失、道德滑坡。而在行政執法過程中,懲罰食品安全違法行為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罰款。有一句話,“錢能解決的問題都是小問題”,食品、藥品方面的安全問題,大多數都以罰代刑,這導致這些違法犯罪的行為越來越多。
“現行法律對于食品生產經營者惡意違法行為的震懾力較小,特別是對于一些主觀故意違法、但危害后果輕微的行為,應當如何定性、量刑,如何實現懲戒的目的,還需要在今后完善相關配套法規時進一步細化。”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相關負責人表示。
違法成本低是一些食品企業以身試法的重要原因。按《食品安全法》規定,罰款上限是“貨值金額十倍以下罰款”或“十萬元以下罰款”。由于罰款不能傷筋動骨,一些違法企業即便被吊銷許可證,也能“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一家新企業又開張了。對大多違法企業而言,恐怕頂多算是隔靴搔癢。“掙的錢遠遠多于罰的錢,一些企業被罰后還接著違法。”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有人大代表一針見血地指出。
同時,相對于食品產業的高速發展和食品消費結構的快速轉變,安全監管能力未能及時跟上,也使《食品安全法》的震懾力大打折扣。目前,我國有食品、食品添加劑、食品相關產品生產企業和小作坊約46.2萬個,而全國質監系統從事食品生產加工監管的行政人員6210人,人均監管74個生產單位。絕大多數監管人員不是專業人員,缺少專業知識,無法監管到位;甚至有無編人員從事執法工作,也影響行政執法的合法性。
此外,食品產業門檻低、分布散、規模小,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食品行業市場無序競爭、惡意競爭現象比較普遍等,也是食品安全事件多發的重要原因。
(摘編自《人民日報》、《甘肅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