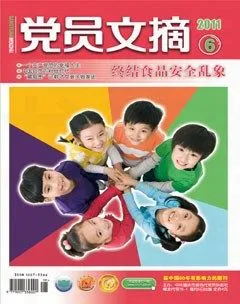道德底線失
當道德、規則甚至法律通通被無限度地破壞和踐踏,中國社會儼然已經迎來了必須深刻反思的“底線時分”,這難道是一個“底線失守”的時代?
底線是最低標準,是最起碼要遵循的規則,是逾越之后需付出巨大代價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到了關鍵時刻,應該很少有人會去討論“底線”問題。然而不幸的是,近年來,這兩個字卻頻頻出現在公眾視野。當道德、規則甚至法律通通被無限度地破壞和踐踏時,中國社會儼然已經到了必須深刻反思的“底線時分”。
“食品加工車間里垃圾遍地,污水橫流。腐爛了的豬肉,被搓上蘇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鏟進香腸攪拌機;洗過手的水被配制成調料;工人們在肉上走來走去,隨地吐痰,播下成億的肺結核細菌……”這是百年前,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在著名的《屠場》一書中所描述的場景。據說正是因為這本書,直接促使當時的美國政府下決心解決食品安全問題。
雖然百年后這場面依然看起來觸目驚心,但它卻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每個人都心知肚明而又無可奈何:三鹿倒下了,皮革奶、染色饅頭又橫空出世;拒絕了蘇丹紅,瘦肉精又開始揚名立萬;河南的健美豬被曝光,化妝豬又在重慶站了起來……
白巖松說,總有一種底線在悄然生長。只是我們還應該看清,“悄然生長”的底線是否一直在節節后退,或者它本身就只有極少數人還在苦苦堅守。當公理和常識因為稀缺而成為標桿和榜樣,人們對底線的要求就注定會一低再低,我們不再期待食品的營養、美味、天然、綠色,只要沒毒或毒性不大就可以了。
有人說,在復雜無比的人性面前談論底線顯得過于浪漫。可是底線不應該只是一種理想,尤其我們俯首當下,看到更多的都是沉重和不安。因為很多我們曾經譴責和憤憤不平的東西,卻已然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我們共同的選擇。
底線失守最可怕的后果,是公眾的無所顧忌和失去善意。
掙有數的錢,過有底線的生活,做有分寸的事。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說的就是底線。
當代儒學者蔣慶表示:“底線價值不是高級價值。一個社會沒有底線價值固然不行,但是只有權利(和法治)沒有道德的話,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冷冰冰的、利害計較的、大家都是小人的、人不堪居住的社會。”倘若真的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我們還能傷得起嗎?
(杜啟榮薦自2011年4月15日《國際先驅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