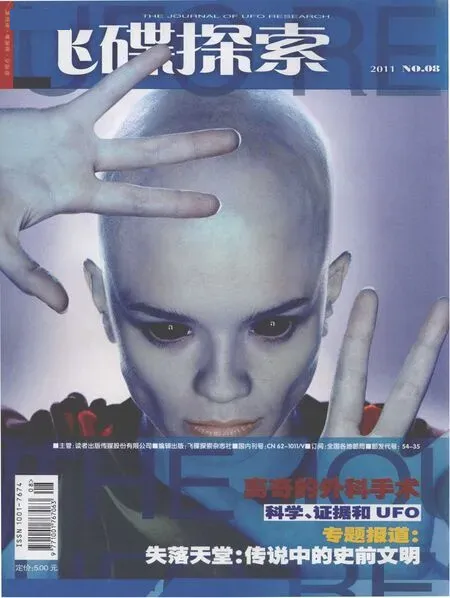那時沙漠還是綠野
■ 吳雨霖
非洲尼日爾的一處考古遺跡所含的信息,透露了撒哈拉沙漠曾是綠野的時光,也告訴我們地球悠長歲月的風水輪轉。
她過世時二十幾歲,小孩則大約是五歲和八歲。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死因或之后發生了什么事,但那并不難推測。或許她正帶著孩子們在附近的湖里捕鯰魚或河鱸,卻不幸溺斃;也許他們的親友讓他們在花叢中安息。總之,有些事發生了,而他們手臂挽繞,長眠并葬于此。
5000年后,這3具骸骨依然相互勾纏,即使骨頭早已被沙和熱磨損、固化,湖泊和花叢也早已不復存在。這使得發現他們的考古學家幾乎感動得掉淚。
近年來,在尼日爾一個被學者稱為勾貝若的地區,發現了將近200個人冢。2010年8月,在《公共科學圖書館》發表的一篇分析這些遺跡的文章,對撒哈拉沙漠所在地區仍是綠意盎然、適宜人居住時的生活情況,提供了空前詳細的描繪。當時,該區還可見到羚羊和牛細嚼植物、河馬和鱷魚在充滿魚群的湖中漫游的場景。
居于此地的先民除了墓冢之外,還留下了貝殼堆和少量陶瓷的殘跡。一般而言,環境極為嚴酷的沙漠把錯綜精微的細節都保留了下來,包括貝類大餐后堆得整整齊齊的貝殼堆。
這些遺跡顯示,過去10 000年來人類如何隨著當地氣候干濕的改變,遷入、遷出該地區的模式。得克薩斯州休斯敦萊斯大學的考古學家麥金塔說:“撒哈拉地區是全世界研究人類因應氣候變遷方式的最佳實驗室之一;在此地區發掘出的細節,確實極為出色。”
古生物學家瑟瑞諾組織了一個跨國的研究團隊,仔細地研究這處遺址。他們分析了花粉,代表那里有葬祭的花、陶瓷、巖石和骨頭;他們對周圍的沙做硬化處理,再制作一層石膏外殼將整副骨架和周遭物質一起打包回實驗室。
撒哈拉沙漠的嚴酷環境條件,造成某些分析的困難。因為這些遺跡是在松散的沙中被尋獲,不能靠周圍的沉積物判斷年代,而必須對這些遺跡直接定年。一般來說,研究者只要分析骨頭上殘余的膠原質便可以弄清楚,但高溫和沙早就把這些骨頭磨得一干二凈。所以,他們必須改用骨頭和牙齒琺瑯質中的碳酸鹽類進行C14定年,但這個方法對樣品破壞性較高。
靠著這些努力,研究者得以將此地區的一些歷史拼湊起來,了解了人類二次大批進駐此地的經過。第一次是在10 000年前的全新紀,以采集、漁獵維生的人類來到此地。他們在附近的湖泊干涸時離開,留下了一些原本用以捕獵重達百余千克的河鱸的骨制魚叉。
第二群人類則在大約7000年前到來。他們的身材較為矮小,頭顱也較為細長。他們的墳墓也比較精巧,目前研究過的墓地中,1/5有骨頭、象牙或貝殼制的飾品。在這一時期的遺跡中出現捕魚活動的遺存,代表湖泊重新出現了。
也有人并不認同這種觀點。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克校區的人類學家艾利許表示,在勾貝若地區進行的一連串調查分析的高質量頗具震撼力,但他希望分析二群遷入人類牙槽和咬合尖端的齒學特征,否則無法排除那是同一批居民在湖泊重新出現后,再回到該地區的可能性。而且,這些骨骼樣本的狀況不佳,使從中純化脫氧核糖核酸的工作更形困難。瑟瑞諾表示,他試過從4顆牙齒的牙根提取DNA,雖然并未成功,但他仍然有信心。他說:“這蠻難的,但我認為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