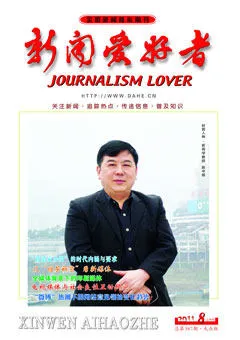兩宋時期寫真的審美功能
宋代寫真的功能從重教化轉向重審美,逐漸形成追求意境和詩性的表達,更加關注人的內心主觀世界,注重自娛性,強烈抒發個人情感和民族情感。鄭午昌指出:“唐代繪畫,已講用筆墨,尚氣韻;王維畫中有詩,藝林播為美談。自是而五代、而宋、而元,益加講研,寫生寫意,主神主妙,逸筆草草,名曰文人畫,爭相傳摩;澹墨楚楚,謂有書卷氣,皆致贊美;甚至謂不讀萬卷書,不能作畫,不入篆籀法,不為擅畫;論畫法者,亦每引詩文書法相印證。蓋全為文學化矣。明清之際,此風尤盛。”善畫者多工書而能詩,畫家不但畫技要好,而且文化底蘊也要深,“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唐則少陵題詠,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毫發。本朝文忠歐公、三蘇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后山、宛丘、淮海、月巖、漫仕、龍眠,或品評精高,或揮染超拔,然則畫者,豈獨藝之云乎?難者以為自古文人,何止數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將應之曰:‘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這里面就說明了繪畫與繪畫者之間全面修養的關系。文中所指的人物要么精于品評論畫、要么畫技登峰造極,后人仰止,文學與藝術相互融合,畫品與人品交苒互滲,達到了至善至美的程度。宋代的繪畫追求文學品位,推崇士人繪畫,貶低畫工繪畫,蘇軾有詩云:“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于維也斂衽無間言。”由此可見,即便是唐代“吳帶當風”的吳道子,到了宋代也不得不屈身于畫工了。
宋代的文人畫家通過繪畫,以解胸中之郁結,借以達到愉悅心情之目的。“且如世之相押字之術,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跡,跡與心合,是之謂印。爰及萬法,緣慮施為,隨心所合,皆得名印;矧乎書畫,發之于情思,契之于綃楮,則非印而何?”一語劃破,直抒胸意,使繪畫的本體美學逐步掙脫社會倫理的桎梏,進一步升華。
世人寄情抒懷的內斂與外化
借畫像作為情感依托,是人們表達尊崇、愛慕、祈福乃至閑情逸趣、自娛自樂的手段。將個人內心情感外化為寫真向世人傳達。唐代崔徽就以寫真為愛情信物,表述衷腸,“唐裴敬中為察官,奉使蒲中。與崔徽相從,敬中回,徽以不得從為恨,久之成疾。自寫其真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如卷中人矣。”崔徽為唐代河中歌妓,裴敬中使蒲州,與崔徽相戀,數月后,裴離去。崔思念成疾,便繪制一幅自己的寫真,寄給敬中,不久相思而亡。后世遂以此為典,喻指情真愛深的女子,歌頌偉大的愛情。故事真實與否無法考證,但至少說明一個問題,寫真可以假借感情的信物,寄托人們無盡的思緒。為此,蘇門四子之一的秦觀曾寫過《南鄉子·妙手寫徽真》,把崔徽描繪得貌美如仙,加以歌頌。由此可見,宋代寫真的審美意味更濃,意義也更深遠。
寫真可以作為表現人們自娛自樂、閑情逸趣的工具,“君不見潞州別駕眼如電,左手掛弓橫捻箭。又不見雪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饑寒富貴兩安在,空有遺像留人間。此身常擬同外物,浮云變化無蹤跡。問君何苦寫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巖中。勛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何充秀才畫蘇軾像,不過是為了“好之聊自適”,還有趙元儼,也就是后人所說的八賢王,“元儼生而穎悟,太宗尤所鐘愛,不欲令早出宮,每朝會宴集,必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就封,故宮中呼為二十太保。廣顙豐頤,資質嚴毅不可犯,其名聞于外夷。性喜儒學,在宮中時,孫奭為侍講,平日與論經藝,尤所親禮。多畜書,好為文詞,頗善二王書法及飛白書,嘗自繪太宗圣容”。他愛好廣泛,詩文書法,樣樣精通,對繪畫也很偏愛,自己曾親手繪制其父圣容,這種雅致應和何充一樣,自適而已。還有金代王庭筠(字子端,號黃華山主)也曾為其父寫真,將其描繪得如仙人雅士,居青松碧水間,清靜空閑,如入仙境,贊美之情,溢于畫面。“仙人紫霞衣,危坐古松間,玉色映流水,不動如丘山。平生黃華老,得意每相關;九原如可作,與君相對閑。”畫中此景,確實令人思緒繞梁,浮想聯翩。
寫真還可以用來展示內心的宏圖大略,金海陵王完顏亮曾通過繪己像于吳山絕頂,彰顯豪情滿懷,壯志凌云,欲投鞭南下,一統江山,體現其內心強烈沖動的一次宣泄,“金主又潛使畫工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繼則繪為屏而圖己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后題以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蓋金主所賦也”。由于這次軍事冒險徹底失敗,其人也橫尸瓜洲,他的深思妙想,最終也變成了臨安遺夢。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人們把深藏在內心的情感,諸如渴望、追求、苦悶、糾結、贊美等來之于心,行之于筆,表現于紙,外化為寫真,展現給世人,才能得以解脫。
文人審美情態的記錄與再現
宋代,文人學士深受統治階級器重,他們在當時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發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或寫詩作賦,寄情山水,激情雅集;或為民請命,嫉惡如仇,一身正氣;或血流戰場,視死如歸,丹心汗青;當然這其中也有投敵叛國、陷害忠良,令人厭惡的齷齪之徒。宋代的寫真能表現出文人特有的內在思想和生活態度。但是,見之于記載和流傳的寫真,大部分是表現文人悠閑自適、雅然聚會的情景,用于顯示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我們可以看一下傳為李公麟現存的寫真《西園雅集圖》(圖1),水墨紙本,白描入畫,以寫實的方式描繪了李公麟與眾多文人雅士,包括蘇東坡、黃庭堅、米芾、蔡襄、秦觀等名流,在駙馬都尉王詵府中做客聚會的情景。畫中之人或揮毫潑墨吟詩賦詞,或撫琴唱和,或打坐問禪,每個人的表情動態在李公麟筆下皆栩栩如生、動靜自然,人物衣紋草石花木,每一筆線條都處理得十分精致,游動的墨線節奏率然朗快、迂回蕩漾,整幅畫面瀟灑、雋逸、嫣然欲絕。
另外,看一下《耆英會圖》,文潞公將當時的很多名士繪于耆英堂,“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勝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其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幾、衛州防御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壽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公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愿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末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富、文二公之后。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后傳溫公像,又至北京傳王公像,于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余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剎,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須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常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資勝院。其后司馬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當時傳寫諸公之真像,盡顯逸士之風采,“然一時衣冠人物之華,水竹林亭之勝,朝野升平之象,髦老康寧之福,藹然見于毫素,使人展卷而為之嘆息企慕,恨不身生其時而目睹其事,蓋有非后世俗史之所能及也”。《耆英會圖》與李公麟乘興所繪《西園雅集圖》很相似,此圖景物全作初春,同時它也表現了當時文人的生活情態,人物形象鮮明,極盡瀟灑之態。
我們再看通過繪像對當時文人學士的描繪,就更容易走進當時的生活。“荊公退居金陵,多騎驢游鐘山,每令一人提經,一仆抱《寧說》前導,一人負木虎子隨之。元祐四年六月六日,伯時見訪,坐小室,乘興為予圖之。其立松下者,進士楊驥、僧法秀也。”金人所繪《蘇子瞻游赤壁圖》所繪蘇軾游赤壁中的情景“扁舟駕浩蕩,水月聊相娛。低頭俯清冷,照見髯與須,仰視蒼蒼天,與身同一虛”。他們通過這些寫真繪畫記錄了宋代文人的一種生活態度和審美理念,再現了那個時代文人的音容笑貌和時代特征。
文人贊美他人與自我評價的依托媒介
“贊”是一種文體,贊文一般簡潔、明了。“像贊”則表現出對所繪人物的贊美,它往往與當下的社會思潮、經濟發展、人文歷史、人情世故等密切相關,是文人學士生活情態、道德追求和意識形態的一種反映,有自寫贊和贊他人兩種。漢代,像贊就已經出現了,如“初,父奉為司隸時,并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到了宋代則非常流行,通過它可以了解到所繪對象的很多信息。文人學士往往利用自寫像贊來描述自己的經歷、成敗等,抒發對理想與現實的憧憬、苦悶,甚至超脫。蘇軾則曾這樣評價自己:“予過金山,見妙高臺上掛東坡像,有東坡親筆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系之舟。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今集中無之。”蘇軾作為宋代古文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是一位為人耿直、剛正不阿、才華橫溢,頗受爭議的人物。一生都郁郁不得志,在改革派和元祐黨之間,他都不被認可,備受打擊。發配、流放相伴相隨,一貶再貶,飽經風霜,最后隕落于常州,可悲可嘆。和蘇軾相對的黃庭堅也因仕途坎坷,屢遭貶謫,最后篤信佛教,以禪入詩,以詩釋禪,尋找到了精神安慰,自寫禪味十足詩一首:“似僧有發,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這是他淡泊自適的內心寫照,也完全是另一種生活態度。
我們再看一下對他人的寫贊,像陳亮,他在《辛稼軒畫像贊》中,稱好友辛棄疾:“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戴四國之重。”他淋漓盡致地歌頌辛棄疾照映一世、流芳百世的英雄形象。國家之棟梁,英雄蓋萬世,而卻無用武之地,隱含對南宋朝廷茍且偷安、屈膝投降政策的唾棄。宋代曹勛曾對趙伯駒(字千里)、趙伯骕(字希遠)兄弟的寫真寫下了這樣的像贊:“此尊者雙瞳瞭然,奮髯虬然,志趣丘壑,風神□仙。昆季燕處,華萼相鮮,芝蘭庭戶,筆墨山川。此特妙發天藏,為金馬之隱爾,詎知高視物表,居玉牒之賢。甚抱負磈礧,凌礫萬象,雕龍海陸,顧丹青不可得而傳也。”“天潢流派,濯秀玉潭,豐姿英發,神宇粲然。彼天下能事,琴書筆墨,固不可寫,而難兄難弟,一丘一壑,亦安得而傳。霜松雪竹,宗籍之賢。”贊美之詞,洋溢于表。
像贊這種題材有時也會成為相互吹捧的手段,王荊公之子雱作《荊公畫像贊》曰:“列圣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是圣其父過于孔子也。雱死,荊公以詩哭之曰:“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是以兒子比孔子也。父子相圣,可謂無忌憚者矣。”這里的王荊公指的是王安石,兒子對父親寫真進行贊美很正常,此處異乎尋常的是父親對兒子的贊美有點出格,父子二人皆不遺余力地吹捧對方為孔子,較為滑稽。
參考文獻:
1.鄭午昌:《中國畫學全史》,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年版。
2.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版。
3.李福順:《中國美術史》,遼寧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
4.宿白等:《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2墓室壁畫》,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5.楊辛:《文潞公耆英會圖考析》,《文物》,1999(12)。
6.單國強:《古書畫史論集》,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7.朱志學:《兩宋“寫真”的社會功能研究——根據兩宋史料對宋代繪像重構》,2007年版。
(作者為中州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