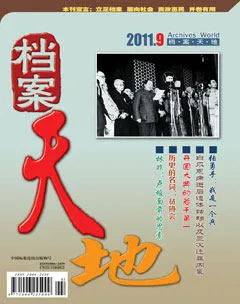盧梭面前的思索
我站在日內瓦的羅納河邊,眺望著一團火紅的朝陽,正懸掛在東方緩緩起伏的山巒上,它燃燒出的滿天霞光,輕輕地灑落在多少樓宇的頂端,灑落在面前這條清澈的河水里。我披著陣陣耀眼的光芒,急急忙忙地往盧梭島走去,得趕快找見他的那一尊銅像,仔仔細細地觀看著,好將許久以來閱讀他著作的過程中間,逐步得到解開的有些疑問,在他面前再認真地回憶和思索一番。
是將近60年前的往事了,卻還影影綽綽地在我的心里蕩漾著。記得那一位很威嚴的國文老師,挺立在中學的課堂里,頭頭是道地串講著《論語》里的章節,宣揚那“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倫理觀念。班上的同學們都聽得昏昏沉沉,惶惑不止,不是早已廢除了帝王的統治,為什么還要畢恭畢敬地歌頌那古老得發霉的秩序呢?
好不容易下了課,趕緊走進圖書館的時候,我很偶然地找見了一本《民約論》,似懂非懂地瀏覽起來。盧梭在兩百多年前寫成的這部論著里面,就訴說著“人是生而自由的,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還說是“如果沒有平等,自由便不可能存在”,而如果“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放棄人類的權利”。
我被這幾行似乎是閃爍著亮光的文字深深吸引住了,在心里反復地誦讀著,覺得如果整個的人類,都能夠這樣自由地過活,平等地相待,那將會充滿多么巨大的親和力。只要厭棄與憎惡那種臣服帝王的說教,不再愿意磕頭跪拜,溫馴地去充當奴才,那就一定會憧憬此種自由與平等的境界。而如果真像是這樣的話,整個熙熙攘攘的世間,肯定會無比的美麗起來。
盧梭的這些話語,真是道出了我一種朦朧的向往,還鼓勵自己去消除滿腹的疑惑和憂慮。于是,這個多么輝煌的名字,就像從我頭頂升起的太陽一般,永遠在心里不住地閃耀。
我在后來畢生的讀書生涯中間,就常常思考著盧梭的這些話語。如果在遵守公正的法律,和服膺高尚的道德這種前提底下,人人都有權利去自由地安排各自的生活,自由地發表各自的意見,肯定就能夠熏陶成充滿自由精神的習慣和心態,從而迸發出一種巨大的創造能力來,歡樂和豪邁地推動著自己生存的環境,始終都朝向前方邁進,讓它變得更合理、更健康、更和諧、更美好。
然而,在人類歷史上長期肆虐的君皇統治,卻擬定了根深蒂固的等級特權的制度,藉以牢固地控制和奴役千千萬萬的民眾,正像魯迅在《燈下漫筆》里所說的,“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像這樣“一級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在這種跟平等和自由迥然相異的社會氛圍中間,當然就只好戴著沉重的精神枷鎖,被囚禁在嚴酷、愚昧、落后和野蠻的秩序底下。
只有高揚著平等和自由的理想,才能夠鼓舞、召喚和敦促人們,英勇地去沖破專制帝王統治民眾的牢籠。呼號著自由與平等的盧梭,真值得后人永遠地感激和尊敬。不過,為什么如此的欽佩和推崇他,自稱是他學生的羅伯斯比爾,竟會在法國大革命的滾滾熱潮中,推行起雅各賓專政的恐怖統治來?誰只要持有不同的意見,就很可能被視為這場革命的敵人,經過他所把持的國民公會表決通過之后,立即處以絞刑了事。為什么聲稱懷抱著平等和自由的理想,卻又絲毫都不能夠容忍與自己相左的意見,要這樣殘忍地大開殺戒,屠戮那些跟自己發生了意見分歧的盟友呢?我多么想迅速地趕到盧梭的銅像底下,再好好地想一想這個長期困擾過自己的問題。
我又匆匆地往前走了幾步,就瞧見那一座橫跨著羅納河的長橋,瞧見在盧梭島的頂端,幾棵高聳的楓楊樹底下,一座方正的石礅頂部,這靜坐在椅子上的銅像,正英氣勃勃地揮起右手,是不是向趕來看望他的人們致意?當我走到濃密的樹陰底下,默默地站在他的面前時,才清楚地看出來了,原來他是握著一枝細小的筆桿,還睜開明亮的眼睛,張望那捏在左邊手掌里的紙張,正沉思冥想著要書寫或者修改什么呢?
我又想起遙遠的中學時代,多么神往地閱讀著《民約論》的情景,然而,我讀得實在太潦草了,只不過是一目十行,飛快地翻過紙頁,面對著有些深奧與艱澀的說理,竟懶得去進一步地梳理和把握,而對于有些容易激發自己興趣的話語,就一唱三嘆地背誦著,還生發出無窮無盡的感喟來,自己向往平等和自由的理想,不正是從這兒萌生的嗎?
我還想起上個世紀的60年代初期,也曾經反復地閱讀著這本剛被更名為《社會契約論》的新譯本,當時真是下定了決心,想要徹底地弄懂,究竟是羅伯斯比爾違背了盧梭的主張,抑或是盧梭在什么地方錯誤地引導了羅伯斯比爾?于是,我花費了不小的功夫,在夜晚昏暗的燈光底下,一字一句地鉆研起來,斷斷續續地琢磨這個始終困惑著自己的疑問。
直到在后來又經歷了40載艱辛的歲月中間,我也并沒有放棄過對于這本典籍的思索,終于在逐漸深入到字里行間的過程中,開始明白了他在自己論述中間產生的失誤。
原來,盧梭把領導公民和國家的“主權者”理想化了,認為 “主權者既然是只能由各個人所構成”,因此“不可能具有與他們的利益相反的任何利益”,“不可能想要損害共同體的全部成員”,這樣的話當然就并不需要對大家“提供任何的保證”,而完全可以將自己的一切主張付諸于行動。這實在是構想得太天真和幼稚了,難道那些領導者在掌握了龐大的權力之后,一點兒也不會滋生出霸道與貪婪的念頭來?況且是在消解了任何有效的保證措施之后,難道就不會開始走上假公濟私和為所欲為的邪路?不會這樣一步步地膨脹和墮落下去,成為說一不二和肆意壓制別人的獨裁者?
盧梭在自己的《社會契約論》里面,多次提到過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足見這位只比他年長二十余歲的啟蒙主義大師,對于他具有多么深刻的影響。可是,為什么在這部杰出的著作里,十分強調過的“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這一真知灼見,竟沒有很好地成為他論證和判斷問題的出發點?
孟德斯鳩目光如炬地抓住了“濫用權力”的這個問題,是因為他深刻地理解人性的本質弱點和歷史的運轉規律,才會提出必須建立一種平行的“權力”,以便去“約束權力”,這樣才能夠保證民主體制的正常運行。比起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顯得很幼稚和迷茫的盧梭來,孟德斯鳩真是萬分的清醒和睿智,他在這一方面所形成的系統的主張,為人類歷史的健康發展,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貢獻。他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和感謝的人。
盧梭在闡述自己這個形成了失誤的問題上面,比起早生于自己80年的英國哲學家和法學家洛克來,也可以說是遠遠地離開了謹嚴與科學的原則。洛克卻正好是跟他相反,十分審慎和確切地強調,政府只是掌握管理社會的公共權力,而每個公民則完全應該享受自由的權利,這在任何情況底下,都是絕對不能被轉讓和剝奪的。他在自己的《政府論》“下篇”里說道,“不能運用契約或者通過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去奴役,或者置身于別人絕對和任意的權力之下,任其奪去生命”,而應該“使統治者被限制在他們適當的范圍之內”。盧梭如果能夠做到像洛克那樣,一開始就嚴格地區分開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的界線,應該是會杜絕自己這個致命性的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