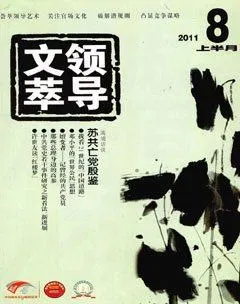鐵托:強權維護南斯拉夫統一
回憶起發軔于整整20年前的那一場驚心動魄、影響深遠的歷史進程,人們不禁要問,南斯拉夫的解體究竟是歷史的必然,還是人為的偶然?鐵托究竟有沒有機會挽回這場悲劇?
歷史沒有假設,但仔細觀察,人們依然可以發現,南斯拉夫的解體是內因長期積累,并被外因一朝誘發的地緣政治災難。
讓人吃驚的是,這個國家的面積僅25.58萬平方千米,但其民族、宗教關系之復雜,對國際格局變動影響之大,竟不亞于蘇聯。俄羅斯的幸運之處在于,它足夠強大,即便暫落下風,終非美歐所能征服。塞爾維亞人的悲劇在于,它沒有俄羅斯那樣的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即便頑強地與命運抗爭,也只能留下歷史的慨嘆。
生來就要面對內憂外患
1945年,鐵托領導的民族解放軍將納粹趕出南斯拉夫。與波蘭等國不同,鐵托及其部下幾乎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下的江山。蘇軍幫他們解放了貝爾格萊德,但蘇軍對南斯拉夫的貢獻也僅此而已。因此戰后,鐵托成為這個國家毫無爭議的主宰。
此時,鐵托一定在考慮,如何統治這個獲得新生的國家。對內,南斯拉夫除了主體的塞爾維亞人,還有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等民族,雖然同被認為是“南部斯拉夫人”,但其實各民族間的關系并非完全融洽。克羅地亞就一直有強烈的離心傾向。當初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一世曾經想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國家分崩離析,1934年,他因此遭到克羅地亞極端組織烏斯塔西的暗殺。此外,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以及伏依伏丁納的匈牙利人也不是省油的燈。
對外,作為巴爾干上的一個大國,地理位置決定了任何想要在國際上有所作為的國家都會試圖在南斯拉夫插上一腳。遠如哈夫斯堡王朝、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近如德國、意大利乃至沙俄,都曾試圖向這塊地區施加影響力。
納粹占領南斯拉夫期間,烏斯塔西為實現建立“大克羅地亞”的迷夢,屠殺約50萬人,驅逐25萬人。外部大國的插手加深了內部民族矛盾。
鐵托的鐵腕是穩定局勢的關鍵
鐵托最終還是想出了些辦法。對內他效仿蘇聯,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黑、斯洛文尼亞、黑山、馬其頓分別成立了社會主義共和國,科索沃則是自治省,而南斯拉夫成為一個“聯盟”的概念。加盟共和國權力平等,且擁有各自的國旗、最高法院、議會、總理。鐵托甚至想以此模式,與同為“南部斯拉夫人”的保加利亞進行兩國合并的談判。1947年,布萊德協議簽訂,眼看大事將成,斯大林的強力插手使得此事作罷。
表面上,各自治共和國擁有很大的自主權,但事實上,鐵托運用自己的威望和權力運作,使得南斯拉夫實現中央集權。他被任命為南斯拉夫的終身總統,在貝爾格萊德向各大自治共和國發號施令。任何對體制不利的人或事,都會被迅速清除。
為掌控局勢,出身于克羅地亞的鐵托對于任何民族主義思潮都進行壓制,無論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還是克羅地亞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分子會遭到逮捕,極端民族主義團伙則會遭到最嚴厲的打擊,甚至會遭處決。
對外,鐵托則奉行不結盟主義,與蘇聯、美國保持“等距離”,盡一切可能將外部的風雨推到國門之外。
歷史證明,在民族關系復雜、內部裂痕深重的國家,強力人物往往能夠穩住局勢。鐵托對內軟硬兼施、對外縱橫捭闔,使得南斯拉夫在納粹被趕走后的30多年間保持大體的穩定。
無奈的“克羅地亞之春”
但深刻的民族裂痕并沒有在鐵腕壓制下消失。鐵托在經濟上實行中央集權,各自治共和國的外匯收入統一上繳,建立聯邦團結基金,來幫助落后地區發展。
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的經濟情況一直要明顯好于其他自治共和國。有統計數據表明,南斯拉夫50%的外匯收入來自克羅地亞,但克羅地亞自己只能保留其中的7%。至于聯邦團結基金,從1965年到1970年,塞爾維亞使用了該基金的46.6%來幫助科索沃的發展,而克羅地亞只拿到其中的16.5%。
鐵托的原意是讓各自治共和國平衡發展,但在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看來,這是“塞爾維亞人的剝削”。1967年,一群克羅地亞詩人和語言學家發表《有關克羅地亞標準語言的名字和地位的宣言》,宣稱克羅地亞語并不屬于南斯拉夫語言的一種。
軍人出身的鐵托可能不會料到,這份宣言迅速在克羅地亞人中間引起共鳴。1971年,南斯拉夫經濟處于困境,《宣言》的影響力也被最大程度地放大。當年薩格勒布爆發了大規模學生運動,示威人群高喊反對“塞爾維亞人霸權”的口號,要求克羅地亞獲得更多自治權,這起事件被西方稱為“克羅地亞之春”。
“克羅地亞之春”的影響是深遠的。南斯拉夫為此于1974年進行修憲,主要是限制塞爾維亞人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提升其他各自治共和國以及自治省的權力。這部憲法還允許各自治共和國脫離南斯拉夫獨立。
潘多拉魔盒緩緩地掀開了蓋子。
6年后,強人鐵托因為血栓被切除了左腿,不久病逝。在他之后再也無人能擁有他的手腕以及威望,繼續維護一個統一的南斯拉夫。但這個巴爾干大國依然要再過10年的時間才走到終點。
(摘自《上海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