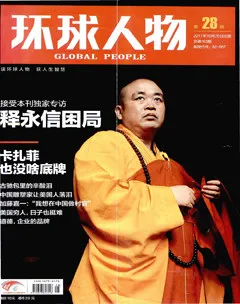加藤嘉一:“我想在中國(guó)做村官”
2011-12-31 00:00:00胡婷婷
環(huán)球人物 2011年28期


與加藤嘉一見面,是在首都機(jī)場(chǎng),身高1米85的他拖著一只行李箱,疾步如風(fēng)地向我走來。遞來的名片上只有“加藤嘉一”4個(gè)豎排的宋體字,不帶任何頭銜。但記者的腦海中卻蹦出了若干個(gè)與這個(gè)名字相連的標(biāo)簽:“著名青年時(shí)評(píng)家”、“21世紀(jì)日本遣唐使”、“‘80后’人氣偶像”、“北京大學(xué)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日本慶應(yīng)大學(xué)高級(jí)研究員”、“英國(guó)《金融時(shí)報(bào)》中文網(wǎng)專欄作家”。沒錯(cuò),這些都是指加藤嘉一,這個(gè)坐在記者對(duì)面的年方27歲的日本青年。
在中國(guó)“走基層”
8年前,作為一名日本公派留學(xué)生,加藤嘉一從東京來到北京,當(dāng)時(shí)正值非典高峰。一句中文都不會(huì)的他把“北京大學(xué)”4個(gè)字寫在紙上,交給出租車司機(jī),就這樣開始了他的中國(guó)生活。
“我要感謝人民日?qǐng)?bào),他是我學(xué)中文的好老師。”加藤笑著沖記者眨眼,“剛來北大時(shí),每天下午跟傳達(dá)室的大哥借人民日?qǐng)?bào),然后翻著字典,把報(bào)紙上的文章逐字逐句地背下來。”
如今,加藤已經(jīng)在北大國(guó)際關(guān)系學(xué)院念完了本科和碩士,口語流利,可以用日、中、英三種語言擔(dān)任國(guó)際會(huì)議的同聲傳譯。但加藤的要求是不僅能說,還希望說出來的話有分量。“剛來就靠喝酒——干了!”加藤對(duì)記者做了個(gè)一飲而盡的動(dòng)作,“就這樣來跟別人套近乎,打開話匣子。”“現(xiàn)在爭(zhēng)取到了一點(diǎn)話語權(quán),就要幫老百姓說話。”
“老百姓”3個(gè)字從他口中說出來,并不令人覺得詫異。加藤在中國(guó)旅游時(shí),發(fā)現(xiàn)一個(gè)旅游團(tuán)時(shí)間安排不合理,游客根本來不及游玩,他義不容辭地給主管部門打電話。在南方的大學(xué)舉辦講座,加藤曾發(fā)自肺腑地對(duì)設(shè)宴款待他的無錫官員說:“無錫是一個(gè)很美的城市,交通狀況很好,不需要建地鐵。”也不管會(huì)不會(huì)鬧得滿席尷尬。加藤還去貴州最貧困的農(nóng)村考察,“他們不想讓我看到有些東西,就派人來跟我喝酒,結(jié)果我把那個(gè)人灌醉,他睡著了,我就溜走了。我喜歡跟農(nóng)民交談,中國(guó)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所依賴的正是這些農(nóng)民。”
說到這里,加藤睜大了眼睛:“我其實(shí)很想在中國(guó)當(dāng)個(gè)村官,如果有這樣的實(shí)習(xí)或就業(yè)機(jī)會(huì),我非常愿意!”加藤稱自己是“貧二代、農(nóng)三代”,因此一直對(duì)基層群體抱有極大的興趣和同情心。這無關(guān)國(guó)籍,而與他的“個(gè)人史”有關(guān)。
跑一場(chǎng)名為“人生”的馬拉松
1984年4月,加藤出生在日本靜岡縣的旅游勝地伊豆。3歲時(shí)曾遭遇車禍,昏迷了兩周才醒過來,恢復(fù)則花了半年。“也算曾命懸一線,所以現(xiàn)在對(duì)生死看得很淡。要把握當(dāng)下,抓緊每時(shí)每刻去積累。”
加藤遺傳了當(dāng)運(yùn)動(dòng)員的父親的體魄,上小學(xué)一年級(jí)時(shí)身高就有1米5,在合影照片里總是最顯眼的那個(gè)。“因?yàn)閭€(gè)子高,所以從小就覺得自己是個(gè)不同的人,要做得跟別人不一樣,希望突出自己。有時(shí)別人說往東,我就偏向西,內(nèi)心里有種叛逆,甚至有時(shí)被看作‘異類’,我都已經(jīng)習(xí)慣了。”
在父親的訓(xùn)練下,14歲的加藤成為了一名優(yōu)秀的柔道運(yùn)動(dòng)員,之后又改練田徑,曾獲全國(guó)大賽第四名。但他的腰由于過度鍛煉而受傷,加藤只好忍痛割愛,就此放棄了比賽。不過,跑步卻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內(nèi)容。現(xiàn)在,他仍堅(jiān)持早上4點(diǎn)半起床,然后跑步1小時(shí)。他告訴記者:“跑步時(shí)大腦一片空白,但有時(shí)會(huì)突然冒出靈感。我是在跑一場(chǎng)名為‘人生’的馬拉松。”
但是,這個(gè)飛奔的陽光少年也經(jīng)歷過一段極灰暗的時(shí)光,“曾經(jīng)憎恨過社會(huì),怨恨自己不能擁有別人享有的安寧。”加藤上中學(xué)時(shí),家里的經(jīng)濟(jì)狀況急轉(zhuǎn)直下,為了貼補(bǔ)家用,他每天凌晨3點(diǎn)就出門送報(bào),再騎車15公里去上學(xué),不管風(fēng)雪還是勞累,他都沒有休息過一天,逃避過一天。為了讓父母全心去掙錢,念高二的他甚至獨(dú)自與向父親逼債的黑道談判。每次談判,他必被毒打,留下了好幾道永久的疤痕。但下一次,他還是會(huì)走進(jìn)夢(mèng)魘般的談判場(chǎng),高中生加藤把自己看成一個(gè)能擔(dān)當(dāng)?shù)哪腥耍瑳]有退縮的余地。
背負(fù)著如此多的重?fù)?dān),有時(shí)甚至到了心力交瘁的邊緣,加藤排解壓力的渠道之一就是瘋狂學(xué)習(xí),因?yàn)椤澳顣日勁腥菀锥嗔恕薄8咧挟厴I(yè),加藤考上了日本最好的東京大學(xué)。他將這歸功于父母對(duì)教育的重視,“雖然家里窮,但我和弟弟妹妹都有書念。”他一直對(duì)父母抱有一顆感恩的心。走進(jìn)大學(xué)后,他不想讓父母承擔(dān)高昂的學(xué)費(fèi),選擇了日本政府提供的公費(fèi)留學(xué)項(xiàng)目,來到中國(guó),來到北京大學(xué)。
“生活是有種延續(xù)性的。”加藤喜歡這么說:“現(xiàn)在的每一點(diǎn)每一滴都能從過去找到影子,我感謝曾經(jīng)的‘個(gè)人史’,成就了現(xiàn)在的加藤。”
“糾結(jié)”的人
現(xiàn)在的加藤在某種程度上從草根變成了精英,他擁有名校背景、高漲的人氣和有分量的話語權(quán)。
在中國(guó),他在諸多媒體露面,寫專欄或接受采訪——就高鐵事故深思,就地溝油現(xiàn)象譴責(zé),就中日摩擦發(fā)言。他擁有一大批“粉絲”,其中以大學(xué)生居多。“我最喜歡去高校講座,跟大學(xué)生交流,因?yàn)槲覀儾畈欢嗍峭g人,有很多共同話題,我可以發(fā)問,也可以被他們反駁,我享受這種相互碰撞的感覺。”
有時(shí),加藤更像是一位訓(xùn)練有素的政治家:語氣雖不咄咄逼人,但表達(dá)觀點(diǎn)清晰有力。說到“堅(jiān)定的立場(chǎng)”時(shí),他會(huì)握緊拳頭;說“你看”時(shí),會(huì)向記者攤開手掌。他曾經(jīng)將奧巴馬稱為“同類人”,但當(dāng)記者問他是不是正在為從政做準(zhǔn)備時(shí),他說:“這不是我唯一的方向,只是一種可能。雖然很多長(zhǎng)輩都覺得我應(yīng)該走政治這條路。”
在鎂光燈下頻頻亮相的加藤,稱自己“是個(gè)內(nèi)向的人”。“我喜歡跑步、看書、旅游,這些都是一個(gè)人可以完成的活動(dòng)。我喜歡自己獨(dú)處的狀態(tài)。”他最喜歡讀的是哲學(xué)書,尤其是古典哲學(xué),比如柏拉圖的《理想國(guó)》。
加藤也是感性的。他在專欄里寫道:“在一片水田上,我看到了無數(shù)發(fā)亮的螢火蟲。我很受感動(dòng),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靜靜地聽著這些螢火蟲飛翔的聲音,看著它們螢火閃爍的樣子,直到它們消失……”
聽記者說起這一段時(shí),加藤微微地笑了:“只身來到中國(guó)的第一夜,我就掉下了眼淚。想媽媽了。” “之后的一些夜晚,有時(shí)醒來,發(fā)現(xiàn)枕頭上也是濡濕的一片。媽媽從小教育我,男孩子的眼淚不要給別人看。”加藤還跟記者分享了他媽媽的另一句“名言”:“吃飯只吃六分飽。”這被加藤貫徹到了自己的人生態(tài)度中——求知若渴,虛心若愚。“永遠(yuǎn)保持一個(gè)饑渴的狀態(tài),對(duì)世界的未知充滿渴望。”
加藤說,他從來不知道什么是“足夠好”,他對(duì)自己有種近乎完美主義的要求,唯一沒有要求的就是飲食。“我永遠(yuǎn)在家門口吃8塊錢的雞蛋面或炒飯。有時(shí)剛寫完稿子,會(huì)多獎(jiǎng)勵(lì)自己一個(gè)1塊錢的鹵蛋。”他對(duì)錢也沒有什么概念,加藤現(xiàn)在每個(gè)月要寫25篇專欄文章,每篇2500字,他太忙了,忙到根本想不起來自己到底賺了多少稿費(fèi)。
精明、沖動(dòng);感性、理性;理想、現(xiàn)實(shí),哪一個(gè)是真實(shí)的他呢?加藤笑稱:“都是吧,我就是一個(gè)特別糾結(jié)的人。”
“我顯然不是間諜”
加藤現(xiàn)在幾乎每個(gè)月都要在日本與中國(guó)之間往返一次,“有兩件主要的公務(wù):一件是推進(jìn)日本的災(zāi)后重建,另一件就是推動(dòng)日本與中國(guó)的關(guān)系。”他這次回日本是為了在慶應(yīng)大學(xué)的講課,主要內(nèi)容是中國(guó)問題與東亞的國(guó)際關(guān)系。此外,他還要參加一個(gè)演講,主題是“年輕人推動(dòng)下的中日關(guān)系”。日本教育部、外務(wù)省和財(cái)務(wù)省的官員也都與加藤保持著聯(lián)系,他們常就一些中國(guó)問題傾聽加藤的意見。
“所以就這樣,中國(guó)—日本,日本—中國(guó)地飛來飛去,成了常態(tài)。”他用手指來回畫著弧線。
環(huán)球人物雜志:你在中國(guó)待了8年,你對(duì)中國(guó)印象如何?
加藤嘉一:中國(guó)正處在一個(gè)想知道外國(guó)人對(duì)她的看法的階段,一個(gè)比較包容的階段。而我正是一個(gè)想了解中國(guó),并樂于見到她往越來越好、越來越人性化的方向發(fā)展的外國(guó)人。中國(guó)有很多地方做得不錯(cuò),最大的問題在于太要面子,以至于現(xiàn)在做什么不像什么。機(jī)場(chǎng)不像機(jī)場(chǎng),農(nóng)村不像農(nóng)村,高校不像高校。
環(huán)球人物雜志:有人質(zhì)疑你對(duì)了解中國(guó)社會(huì)的熱情為何這么高漲,猜測(cè)你是間諜,你對(duì)此有何回應(yīng)?
加藤嘉一:這些人首先要搞清楚間諜的概念。間諜是利用不正當(dāng)?shù)拿孛苁侄危@得政府機(jī)密,以金錢為目的的人。而我的一切行為都是透明、正當(dāng)?shù)模私庵袊?guó)也不是為了賺錢。我顯然不是間諜。
但我并不害怕被他們誤解,他們的攻擊也傷害不到我,我只會(huì)從他們的聲音中反觀中國(guó)的“憤青”。我是抱著一種學(xué)習(xí)的精神來觀察中國(guó)的,每天都在積累,每天都“在路上”。
環(huán)球人物雜志:在你看來,日本人對(duì)中國(guó)的真實(shí)情感是怎樣的?
加藤嘉一:我們從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對(duì)中華文明始終抱著一種崇敬的態(tài)度。更由于戰(zhàn)爭(zhēng)的原因,我們對(duì)中國(guó)也抱有愧疚的感情,我本人就有。有些政府官員,礙于面子,礙于西方的態(tài)度,不會(huì)承認(rèn)得這么痛快。但從根本上來說,日本人不會(huì)像西方的觀察者一樣,抱著傲慢與偏見的態(tài)度看中國(guó)。
環(huán)球人物雜志:你經(jīng)常就一些敏感問題發(fā)表看法,也表達(dá)過一些與官方聲音相左的觀點(diǎn);但你在媒體上,包括一些官方色彩濃厚的媒體,以及民眾當(dāng)中,都很受歡迎,你是怎么做到的?
加藤嘉一:這有賴于表達(dá)的藝術(shù)。我的表達(dá)方式一向是溫和的、中庸的、辯證的。(隨手在紙巾上畫出一個(gè)田字格)我能表達(dá)的空間只有正中間這一點(diǎn),而我要考慮的有4個(gè)方面:首先,我是日本人,日本的利益,不能違背;其次是中國(guó)的國(guó)情,我考慮到日本立場(chǎng)的同時(shí),一定也會(huì)提到中方的立場(chǎng)是怎樣,怎么尋找共同點(diǎn);再次是決策層,只有對(duì)決策層有說服力,我的話才有建設(shè)性;最后是中國(guó)民眾,要面向他們,讓他們?nèi)菀捉邮堋?br/> 在中國(guó)的我,只是觀察者,而不是傳播者。
環(huán)球人物雜志:作為一個(gè)“80后”,你怎么看中日兩國(guó)的同齡人?
加藤嘉一:日本“80后”的生活自理能力強(qiáng)一些,因?yàn)榻?jīng)常打工。而中國(guó)學(xué)生的爆發(fā)力很強(qiáng),思維很活躍,這一點(diǎn)我很欣賞。其實(shí)現(xiàn)在日本和中國(guó)的“80后”都面臨著一些同樣的困境和焦慮,比如工作、對(duì)象、房子,這些都是由兩國(guó)的國(guó)情和社會(huì)決定的,都很正常,社會(huì)不該對(duì)他們過多指責(zé)。
中國(guó)有個(gè)“80后”作家韓寒,我們倆雖然沒有見過面,但經(jīng)常被拿來比較。韓寒是一位我很尊敬的作家,也是我反觀中國(guó)的一面鏡子。
環(huán)球人物雜志:你如何評(píng)價(jià)自己?我覺得你是我見過的最不像“80后”的“80后”。
加藤嘉一:(笑)我自己有一套為人處世的完整的體系。總體目標(biāo)是:做與眾不同的人。中立、自立、獨(dú)立是戰(zhàn)略,理智、中庸、辯證是戰(zhàn)術(shù)。
編輯:劉心印 美編:陳思璐 編審:張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