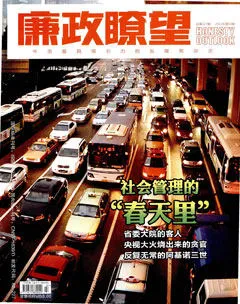資源省緣何頻成問題省
2012-01-01 00:00:00
廉政瞭望 2012年2期

2011年,云南大旱,水貴如油。
就像放在烤箱上的樹葉,云南的土地在慢慢的蜷曲。在經過了差不多持續(xù)半年的旱情以后,池塘干涸,莊稼滅頂,救命之水逐漸消失。春天的陽光下暗藏殺機,汽車駛過的大路上揚起一陣塵土。
云南雖為水資源大省,水資源總量2222億立方米,排名全國第3,但同時又是水資源窮省,開發(fā)利用率僅為6.9%,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1/3。大旱如一場慢性病,日積月累地加深著這塊土地的傷痛。這也是該省繼2010年大旱后,再次受災。
2011年,礦難依舊,掩面啜泣。
出事的不論是河南焦作,還是山西朔州、貴州荔波,事故現(xiàn)場往往都是廢墟一片。巨大的爆炸力已然把礦井附近的建筑和設備都夷為平地,很多人安全帽散落在地,還有一些破舊的衣服,這些情景似乎就是汶川地震中的某一處一樣。后果是多人遇難、受傷,而家屬情緒依然淡定。
專家分析,地方政府和開采者擁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對地方政府來說是高速的GDP發(fā)展,對開采者來說是巨額的利益。他們都不想在開采自然資源方面有更多的技術投入,而往往采用極其廉價的技術,加上極其廉價的勞動力,暴露出的則是地方開采的毫無規(guī)劃性。
這些本是資源豐富的省份,不僅出現(xiàn)了新問題,對長期發(fā)生過的問題,依然沒得到有效控制。
一條不可持續(xù)之路
這些資源省份自然資源非常豐富,但人才資源嚴重缺乏;很多地方對自然資源的開采,仍然停留在相當原始的水平,技術成分很低,沒有掌握現(xiàn)代高科技的人才,而當?shù)噩F(xiàn)有人才外流更是嚴重。
以山西為例,在采礦過程中,獲得利益的主體包括國有開采者、地方政府和私人開采者。私人開采者既來自山西本地,也來自外省,并且數(shù)量不少。這些人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山西作為整體并沒有獲得多大的利益,一些社會群體更是成為了這一過程的受害者。
前些年,山西因為多年來采礦過程中接連不斷的安全事故,國家一度從私人手中收回了開采權。其實,允許私人采礦并沒有為山西帶來多大的好處。同時,一些煤老板們以不正當手段取得自然資源開采權,但不能提供有效的生產安全,工人則是高強度勞動,以致采礦過程中造成安全問題和人員傷亡問題,這些與政府對企業(yè)的監(jiān)管不到位有關。
與之相關的一個現(xiàn)象是這些地方中產階級缺失,收入分配分化嚴重,一部分人過于富裕,過度消費;而大多數(shù)人消費不足,仍處于貧困線的邊緣,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也不少。
靠“羊煤土氣”發(fā)達起來的鄂爾多斯就是其中代表,一夜暴富的故事在這個小城里真實地發(fā)生著,煤老板和那些被征地的農牧民成為故事的主角。遽然而來的財富迅速拉抬了這座城市的消費水平,而不論是在包頭還是北京,只要被老板聽出鄂爾多斯口音,就甭想再砍價了。但這些浮躁風氣在近期各地民間借貸恐慌的發(fā)酵下,鄂爾多斯債權人從“中富危機”迅速陷入破產危機。人均擁有3至4套房的豪氣逐漸在淪為笑話。
很顯然,資源既是一個地方發(fā)展的優(yōu)勢,又是各種問題的根源。在世界上很多資源豐富的國家,都存在著這樣的問題。這些國家往往高度依賴于資源的開采,導致產業(yè)單一化,各方面的產業(yè)發(fā)展很不均衡,工業(yè)化尤其是加工業(yè)發(fā)展程度很低。從簡單的資源開發(fā)中可以獲取巨大的利潤,資源開發(fā)往往成為各種力量爭取的權力。中國的資源省必須面對的一個現(xiàn)實問題就是,如何把優(yōu)勢發(fā)揮到極致的同時把劣勢最小化。
形形色色的短視思維
和普通的安全生產事故不同,云南近幾年遭遇的大旱,是天災,也有人力不及的地方。該省水利廳一名相關負責人就表示,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云南的水利設施是在吃老本。小型水庫幾乎沒有進行過修繕,結果造成1/4的鄉(xiāng)鎮(zhèn)政府駐地飲水困難。其間除了缺乏資金修繕,更沒有相應的科學管理。
諸如云南的這種困境,表明地方政府在缺錢和缺技術外,還缺少服務意識。除此之外,西氣東輸、北煤南運、南水北調,資源省份往往還擔負起了全國戰(zhàn)略。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長王宏英就表示:“山西要保障國家能源戰(zhàn)略安全,要滿足發(fā)達地區(qū)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加之山西自身發(fā)展對煤炭的過度依賴,所以煤炭產量是不可能下降的。但目前的生產力水平又決定了事故無法從根本上杜絕,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確實是一對現(xiàn)實矛盾。”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則分析,因為資源省對國家整體發(fā)展非常重要,資源省份官員的任免也異常嚴格。之前因安全事故“下課”的官員名單很長:孟學農、于幼軍、張建民、夏振貴……其中不乏省級大員。
尤其在地市一級,一些官員單方面地追求政績主要由兩個因素促成:一是GDP主義,二是干部交流制度。在之前很多年里,GDP是中央衡量地方官員最重要的指標。地方官員為了政績,多創(chuàng)造GDP,就會對當?shù)氐馁Y源進行毫無節(jié)制的開采。其次,在干部交流制度下,地方一把手至多在一個地方從政10年,就必須調往外地。有些官員的任期更短,幾年就被調走。
為了控制地方主義的產生,干部調動的頻率越來越甚。地方主義得到了控制,客觀上也促使地方官員對地方的發(fā)展毫無長遠計劃,沒有長遠利益觀。
資源省的財富外流
就可持續(xù)發(fā)展而言,資源省份則面臨另外兩個巨大的問題,那就是財富的保護和轉移機制的缺失。這些省份盡管從開采資源方面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但財富很難留在本地,而是流向了外地。
也許很容易理解外來的開采者沒有動機把財富留在本地,但即使是本地的開采者也沒有把財富留在本地。因為過度依賴于自然資源的開發(fā),其它方面的產業(yè)沒有發(fā)展起來,這使得資源省往往缺少投資領域。沒有投資領域,資金外流不可避免。
日益惡化的環(huán)境也是財富出逃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由于毫無計劃和節(jié)制的開采,山西的地貌和水系已經遭到嚴重破壞,一些人有了足夠的財富,就想搬遷到其它地方,甚至國外。
其次是社會環(huán)境。因為貧富差異過大,社會上仇富心理盛行,富人們自然感到很不安全。此外,對很多擁有財富者來說,資源省份缺少高質量的教育,也是他們移民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為了后代而移民。
專家建議,地方政府應該學會把從資源領域得到的財富,轉移到其它產業(yè)領域,以達成各產業(yè)的比較均衡的發(fā)展。例如山西完全可以以煤文化來開發(fā)文化旅游業(yè),反過來又可以減少對煤的依賴,保護煤的開采,從而達到可持續(xù)的發(fā)展。對教育的投入和環(huán)保的投入,也會產生類似的功效。
鄭永年認為,資源省份既要服務于整個國家,但也要著眼于地方的長遠利益。在這方面,新疆已經開始了一些積極的政策舉措,例如根據(jù)價格征收資源稅,類似的方法可以推廣到其它省份。
其實,資源稅也好,其它方式也好,最主要的目標就短期來說,就是要把來自資源的財富轉移到本地人民,實現(xiàn)社會公平,從而保障社會穩(wěn)定;從長遠來說,就是要把財富轉移到本地其它產業(yè)的發(fā)展,實現(xiàn)產業(yè)均衡可持續(xù)的發(fā)展。(綜合《21世紀經濟報道》、《經濟觀察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