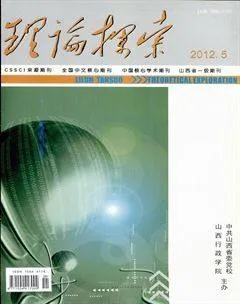關于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的法律規制
〔摘要〕 當前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法律規制面臨補償目的不明確、補償相關主體難以確定、補償標準不統一、監管乏力的困境。造成這些困境的原因在于現有研究無法為實踐提供正當性基礎、未考量基本農田保護補償對地力提升的重要意義、漠視基本農田保護補償中的國家責任。為此,應從明確補償目的、充分考量補償的經濟激勵功能、凸顯補償的國家責任、維護直接從事基本農田保護者的合法權益、健全監管機制等方面完善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的法律規制。
〔關鍵詞〕 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法律規制,困境,原因,完善
〔中圖分類號〕D91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2)05-0125-04
基本農田是耕地中的精華,保護基本農田對于強化農業基礎地位、維護農業生態以及保障糧食安全具有重要意義。我國土地管理法、農業法規定國家實行基本農田保護制度,國務院依據土地管理法的授權專門頒布《基本農田保護條例》,規范基本農田的劃定、保護、監督管理行為。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基本農田保護提出了兩個全新理念,其一是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其二是建立保護補償機制,以確保基本農田總量不減少、用途不改變、質量有提高。各地積極推動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的劃定,對基本農田保護行為進行補償。與實踐的積極推動相比,基本農田保護補償作為一項重要法律制度,現有研究對其存在的困境明顯缺乏關注,筆者以“基本農田保護補償”作為主題詞,在中國知網上僅搜索到6篇相關文獻,現有研究顯然無法為劃定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的實踐提供理論支撐。鑒于此,本文通過分析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法律規制面臨的困境,探究法律規制面臨困境的原因,最后提出完善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法律規制的思路。
一、當前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法律規制面臨的困境
(一)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的目的不明確。2008年以來,國家一直在積極推動劃定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建立保護補償機制。但當下關于基本農田保護的補償目的仍存紛爭。汕頭市《基本農田保護補貼資金暫行管理辦法(暫行)》規定補償的目的在于平衡建設用地和基本農田間的巨大利益差距,以此增加農民收入,激勵農民保護基本農田,保障糧食安全;廣州市《基本農田保護補貼資金管理試行辦法》規定補償的目的是要落實基本農田保護任務,從而形成基本農田保護的激勵機制;成都市《耕地保護基金使用管理辦法(試行)》規定保護補償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護耕地,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從這些地方性規范文件來看,其規定的補償目的過于籠統,并未認清基本農田保護與一般耕地保護的本質區別,使法律制度構造缺乏科學性與可行性,必然導致補償效果欠佳,徒費納稅人資財。
(二)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的相關主體難以確定。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相關主體可分為補償主體和受償主體。基于基本農田在維護農業生態和糧食安全的功能,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應負有補償的義務。但具體承擔補償義務的主體為中央政府抑或是地方政府,并不確定。實踐中,地方政府負擔全部補償資金的方式對于基本農田保有量較多的地方政府無疑會增加其財政負擔。而從受償主體來看,補償給集體經濟組織抑或承包經營權人,亦難以確定。若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之后,確定適格的受償主體則會更加困難。
(三)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標準不統一。現行各地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標準并不統一,成都市規定對于一般耕地保護補償金額是每年每畝300元,基本農田保護補償金額為每年每畝400元;廣州市規定根據地域不同分為每畝每年500元、350元和200元;汕頭市規定的補償標準較低,每年每畝僅30元,同時,規定補償依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每3年原則上調整一次;佛山市《基本農田保護補貼實施辦法》規定不同地區設定每畝每年500元、200元等不同標準,并與汕頭市要求相同,需依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每3年原則上調整一次。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標準應在激勵農戶保護基本農田的積極性與不對政府財政構成過重的負擔之間尋求平衡,補償標準的不統一,造成受償主體之間的不公平,十分不利于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的劃定。
(四)對基本農田保護監管乏力。實踐中對于基本農田保護行為的監管,受償主體一般要與補償主體簽訂基本農田保護責任書,約定雙方的權利義務。但所謂的基本農田保護責任書往往是一種軟約束,受償主體履行基本農田保護義務的行為難以監督。眾多分散的農戶是否在維護基本農田的質量,在有限的執法資源之下,執法部門面臨沉重的執法負擔,導致執法部門實際上根本無力監管基本農田保護行為。基本農田補償發放之后,受償主體是否按照法定和約定的義務履行基本農田保護義務,亟需健全基本農田保護監管機制。
二、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法律規制面臨困境的主要原因
(一)現有研究無法為實踐提供正當性基礎。基本農田補償目的的研究在于對相關法律制度的構建提供有意義的導向,有學者認為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的劃定屬于對土地發展權的限制,基于此種限制應給予農戶補償。〔1 〕 (P104 )此觀點可稱之為“土地發展權受限說”。有學者則認為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內土地權利人喪失土地開發機會,承受本應由全社會承擔的土地開發機會喪失的成本,構成管制征收,土地權利人因其“特別犧牲” 應有權獲得額外的公平補償。〔2 〕 (P77 )此觀點可稱之為“管制征收說”。此兩種觀點顯然皆無法為基本農田保護補償實踐提供正當性基礎。
主張“土地發展權受限制說”的學者注意到我國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的劃定使集體土地所有權人和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利用土地的行為受到限制,但我國的農用地是否存在所謂的“土地發展權”?如果我國現行土地制度并不存在土地發展權,何談土地發展權的限制。一般認為,土地發展權指的是土地所有權人發展或開發土地的權利,是為保護農用地、環境敏感地區而實施的政策性工具。〔3 〕 (P133 )但在我國土地使用權利生成之時,權利人并沒有取得所謂的改變土地用途以獲取更大收益的權利,一旦土地規劃之后即產生權利內涵明確的土地使用權,權利本身界限已經明確。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權,僅取得該幅地塊當時的法定使用類別、強度的權利,并未包括未來變更使用的土地發展權及其所帶來的發展價值。〔4 〕 (P2-35 )集體土地所有權人和土地使用權人皆不可能改變土地的使用用途。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土地權利人并不享有土地發展權,更談不上對土地發展權的限制,“土地發展權受限說”無法為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提供正當性基礎。
農用地劃定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的限制是否超出特別的界限而構成“特別犧牲”,達致與“征收”同樣的效果,從而構成“管制征收”?美國經過司法判例逐步發展的管制征收理論認為如對不動產的管制已達到類似征收的效果應考量是否予以補償。管制性征收理論認為必須衡量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衡量的本質是評估公共利益和加諸財產所有權人的負擔,具體可以分為四點:管制性的法律是否為了合法的公共利益,此種法律是否合理地促進此項公共利益,加諸財產所有人的負擔是否過大,此種負擔是否不成比例。〔5 〕 (P159-167 )《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第17條第2款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占用基本農田發展林果業和挖塘養魚,是否使權利人承擔遠超過農用地社會義務的負擔,有否侵害農戶的經營自主權?根據土地管理法第四條和2007年頒布的《土地利用現狀分類》國家標準,可知農用地根據土地的地形、灌溉設施等情形,具有不同的農業用途,基本農田作為耕地中的精華應在其上種植農作物,發展林果業和挖塘養魚應在林地、園地和養殖水面上進行,方符合土地的最佳利用。因此,對基本農田施加的限制并沒有超出社會容忍的限度,本身屬于基本農田社會義務范圍之內,并不會構成所謂的“管制征收”。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劃定的“永久”是否會達到過度的限制呢?根據《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第12條規定,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并不會影響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因此,即使劃定為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并不會對土地權利人造成不可容忍的負擔,不構成“管制征收”。 “管制征收說”顯然同樣無法為基本農田保護補償實踐提供正當性基礎。
(二)未考量基本農田保護補償對地力提升的重要價值。基于基本農田對于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我國對基本農田實行特殊保護。《基本農田保護條例》對基本農田保護法律規制的方式,主要包括通過規劃確定基本農田保護區嚴格保護,將基本農田保護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作為政府領導任期目標責任制的一項內容,并由上一級人民政府監督實施。對基本農田的轉用和征地審批不考慮數量多少一律由國務院批準;在劃定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區的地方,建立基本農田保護目標責任考核制度,地方人民政府應當與下一級人民政府簽訂基本農田保護責任書。通過層層目標責任分解,明確具體的保護主體。《基本農田保護條例》還設定禁止性行為規范,嚴格禁止在基本農田之上進行破壞基本農田的活動。通過建立基本農田保護監督檢查機制,收集基本農田保護的信息。但總體而言,現行立法僅注重從基本農田數量的維持上保護基本農田,而對基本農田地力的提升這一攸關基本農田糧食生產綜合能力的因素熟視無睹。從法律實施來看,我國土地法律制度實施中遇到的重要問題,一是建設行為違法占用耕地,另一個就是耕地地力下降,兩個問題對糧食安全皆會帶來極大威脅。城市化進程中必然面臨的現象是建設行為不斷擠占農業用地的空間,在耕地數量不斷下降的情況下,確保耕地的質量顯得尤為重要。確保耕地數量可保障糧食安全,通過不斷提高基本農田的地力,保障耕地的質量,同樣亦可保障糧食安全。現行基本農田保護法律對于基本農田地力的提升缺乏規范,必然導致在受償主體的確定、補償標準以及基本農田保護行為的監管等方面出現困境。
(三)忽視基本農田保護補償中的國家責任。基本農田保護補償不是政府的恩惠,而是國家應該承擔的責任。基本農田保護所負載的利益除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獲得的經濟利益之外,更多的是其產生的農業生態利益和維護糧食安全的社會利益,此生態利益和社會利益為全社會所享有,而作為利益的生產者的農民并未從利益享受者處獲得其應支付的對價,形成正外部性。對于正外部性內部化的途徑一般認為有征稅和補償,對基本農田保護正外部性的內部化,征稅并不適用,因此,對承擔保護基本農田的農民進行補償是正外部性內部化的合理途徑。從基本農田保護中獲得利益的為不特定的社會公眾,不可能與作為利益生產者的農民達成補償協議,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理應負有補償農民因產生農業生態利益和社會安全利益而付出的成本。在具體補償主體的確定上,不可把補償的責任全部推至地方政府,基本農田保護是全社會的義務,若僅由地方政府承擔補償責任,勢必造成擁有基本農田數量較多的糧食主產區為其他擁有基本農田數量較少的經濟較發達地區承擔責任,形成區域間的不公平。忽視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的國家責任必然導致補償主體難以確定、補償資金投入不足,難以形成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的長效機制。
三、完善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的法律規制
基于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法律規制所面臨的困境,“土地管理法”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修改時應進一步完善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法律制度,以推動永久基本保護區劃定工作,實現基本農田保護的目標。
(一)明確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的目的在于提升基本農田的地力。耶林指出“目的是整個法律的創造者,并不存在不源于目的(即一個實際動機)的法律規則。” 〔6 〕 (P54 )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既不是對農民土地發展權限制的補償,也并未因為過度管制基本農田利用行為而構成“管制征收”。以“土地發展權限制”和“管制征收”作為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目的的實質是以私人土地所有權的保障作為基點,而進行法律制度的構造,與我國土地公有制的國情并不相符。因此,若盲目引進以私人土地所有權為基礎的西方經驗,不僅忽視了我國的制度基礎,而且必然會導致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法律規范在行為調整上的困境。以地力提升作為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的目的,有利于塑造基本農田保護的長效機制。依此目的,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的法律制度構建應以地力提升為價值目標,法律制度實施效果的評估亦應以地力提升程度作為考量因素。
(二)充分考量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的經濟激勵功能。基本農田保護補償是對農戶所為保護基本農田公益行為的利益誘導,內含有經濟激勵功能。利益法學派的代表人物赫克認為,“立法者必須探究、關照及評價需要規范的生活關系及利益沖突,這些探究、關照及評價在每個規范都不相同,因為它取決于不同的利益狀態。我們應該去尋找個別的利益,并且認識到是何種沖突處于對立狀態,這可以說是一種信息搜集工作。” 〔7 〕 (P251 )基本農田上負載有農民的生產利益,通過在基本農田之上從事農業生產,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才有物質基礎;基本農田之上亦負載有全社會的公共利益,其中既包括每一個人獲得糧食安全的保障,也包括良好的農業生態、優美的農業景觀等。一方面,農業生產中農民維護基本農田地力的行為與公共利益的實現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如果農民過度追求自己的生產利益,一味削弱地力,將有損公共利益。認識到農戶的行為選擇與公共利益實現密不可分,就涉及到如何選擇規制農戶行為的手段問題。在命令式和激勵式手段之間,命令式手段在規制農戶維護地力行為方面效果不佳。因為對于基本農田質量的保護不但要求農戶消極的不為,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勵農戶積極的為。因此,應充分考量基本農田保護補償這一利益誘導機制,激勵農戶選擇提升地力,從而更好的實現公共利益。
(三)凸顯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的國家責任。基本農田保護產生的農業生態利益和糧食安全利益受益者為全社會,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必須承擔長期以來被忽視的補償責任。補償不是政府對農民的恩惠,而是農民基于其提升基本農田地力的行為而應享受的合法權益。中央政府在財政預算中應將基本農田保護補償資金投入列入預算科目,保障補償資金的來源。國家還應建立基本農田保護補償資金的增長機制,以使基本農田保護者獲得的補償資金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而增長。中央政府承擔基本農田保護補償資金投入的主要部分,地方政府應從土地出讓收入中提取相應的比例投入到基本農田保護基金,以調動地方保護基本農田的積極性。
(四)維護直接從事基本農田保護者的合法權益。依據地力提升理論,基本農田保護補償的受償主體應是切實有助地力提升的基本農田保護者。根據土地管理法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的規定,負有基本農田保護職責的主體包括地方人民政府、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承包基本農田的農戶。首先,地方人民政府作為行政主體承擔的為法定的行政職責,其不得放棄保護基本農田的行政職責,否則會構成行政失職,地方人民政府不可能作為受償主體,而應是補償主體。其次,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是基本農田的發包主體,對基本農田保護具有管理職責,但在家庭承包經營制下,基本農田一般已經發包至本集體成員,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并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將其作為受償主體激勵效果不彰,無法實現地力提升的補償目的。最后,承包基本農田的農戶直接在基本農田之上從事農業生產,是基本農田地力的“養護者”和農業生態利益和糧食安全利益的生產者,而農戶從農業生產中所獲的收益與由其生產的為全社會所享有的利益相比存在巨大利益差距。因此,應將其作為受償主體,維護直接從事基本農田保護者的合法權益。
(五)健全完善的基本農田保護監管機制。基本農田補償發放之后,必須通過完善的監管機制,監督農戶在基本農田之上所為的農業生產行為有利于地力提升。首先,完善基本農田地力分等定級制度和地力檔案制度,根據地力分等定級情況確定補償標準,相同地力等級應統一補償發放標準。其次,應在現行受償主體與補償主體簽訂基本農田保護責任書的基礎上,設計完善的基本農田保護合同條款,進一步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在合同中依據地力分等定級標準,明示受償主體所承包地塊締約之時的具體質量等級并約定補償期間應達到的質量等級。最后,建立地力等級抽查制度,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有權對受償主體的地力提升情況進行隨機抽查,對未達到基本農田保護合同約定地力等級的農戶,要求其限期治理,治理期間內暫停補償發放,若經治理仍難以符合地力等級標準的農戶取消其基本農田保護補償資格。
參考文獻:
〔1〕蔡銀鶯,張安錄.規劃管制下基本農田保護的經濟補償研究綜述〔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7).
〔2〕楊 惠,熊 暉.農用地管制中的財產權保障——從外部效益分享看農用地激勵性管制〔J〕.現代法學,2008,(3).
〔3〕John C. Danner. TDRs——great idea but questionable value〔J〕.The Appraisal Journal,1997,(4).
〔4〕許文昌,等.土地政策〔M〕.臺北:高點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
〔5〕謝哲勝.財產法專題研究(二)〔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6〕Rudolf Von Jhering.Law as a means to an end〔M〕. The Lawbook Exchange, Ltd.1999.
〔7〕吳從周.概念法學、利益法學與價值法學: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論的演變史〔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 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