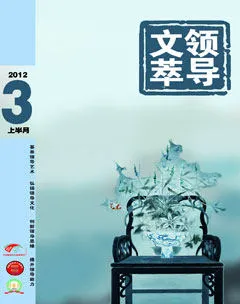跟漢文帝學用人
漢文帝劉恒開啟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成為儒道各家都交口贊譽的一代明君。究其原因,這與他高超的用人藝術有著重要關系,在用人方面,他有很多地方值得從政者學習和借鑒。
任用會說的還是會做事的
對于一個明智的領導者來說,在用人的過程中,不僅要能做到獎懲嚴明,知人善任,而且還應具有大局意識和長遠眼光,善于從全局的高度來權衡各種關系和利弊得失,然后選擇最為滿意的用人方略。在這方面,漢文帝堪稱楷模。
文帝平時比較喜歡打獵。一次,他帶著大小隨從到皇家園林上林苑打獵游玩,只見奇珍異獸,應有盡有,心里非常高興。來到老虎園的時候,上林苑的主管官員前來拜見,文帝就向他詢問上林苑的面積以及動物種類。沒想到這隨口一問,那位主管官員竟然支支吾吾,回答不上來,文帝很生氣。
這時,旁邊的一個老虎管理員卻對各種禽獸的情況非常熟悉,自告奮勇地跑了出來,回答了文帝的問題,并且口齒伶俐,言簡意賅。文帝聽了非常高興,就打算撤掉原先的那個主管官員,改用這個老虎管理員。他剛想下令,卻被大臣張釋之攔住了。張釋之問道:“陛下覺得絳侯周勃這個人怎么樣啊?”文帝說:“這還用問嗎?堪稱長者。”張釋之又問:“那東陽侯張相如呢?”文帝說:“也是長者。”這兩個人都是漢初重臣,但是都有些木訥,不太會說話。
于是,張釋之說道:“既然如此,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都曾對有些事情說不清楚,哪里像這個管理人員這么伶牙俐齒啊!”接著,他闡述了自己的主要顧慮,說:“秦朝的時候,很注重耍嘴皮子的功夫,結果朝廷官員以耍嘴皮子為能事,文過飾非,導致亡國。今天的這件事陛下是不是應該再考慮一下。”文帝一下子就明白了張釋之的話,如果提拔了這個老虎管理員,確實有可能獲得一個好的上林苑主管官員,但其他大臣則會認為這是耍嘴皮子的結果,若聞風而動,人人以耍嘴皮子為能事,定會造成巨大的社會危害。
權衡利弊之后,文帝決定不提拔那位老虎管理人員,只是撤了那個主管官員,因為玩忽職守是必須受到懲罰的。自此,漢文帝在用人上就特別注意“聽其言觀其行”,從而樹立了正確的用人導向,官場之風得以凈化,其統治地位也得以鞏固。顯然,這與他用人上的明智是分不開的。
從細微處識人
文帝六年,匈奴大舉入侵邊境,周亞夫被任命為將軍,駐軍細柳營。按照當時軍法規定,軍隊中必須聽將軍命令,且軍營中不能驅馬快跑。于是,文帝在慰勞軍隊之時,不得不派使臣拿著符節下詔令給周亞夫,由周亞夫傳話打開營門才得以進入軍營,入營后,還不得不依法控制馬韁繩慢行。對此,其他大臣覺得是對文帝尊嚴的冒犯,但文帝卻不以為然。他透過周亞夫嚴格按軍法辦事的舉動,睿智地看出了他的耿直可用所以對其盛贊不已。退卻匈奴后,就將周亞夫升為中尉,掌管京城兵權。他臨終前還叮囑景帝,關鍵時刻要重用周亞夫。周亞夫亦不失文帝期望,后來平定了七國之亂。
文帝時期,為了招攬更多的人才來治理國家,他確立了特科察舉制度。在其即位第二年及第十五年,曾兩次下詔進行特科察舉,專求“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當時的察舉程序主要有:皇帝下詔指定舉薦人才類型;丞相列侯公卿及地方郡國按要求舉薦人才;皇帝對被舉者進行策問,按對策高下授予官職。由于上至中央官員,下至地方政要,均要盡力推薦優秀人才,所以文帝的察舉取士在選拔人才的范圍上有了極大擴展,使全國上下許多人才可以不受出身限制,直接踏上仕途。正是在察舉選賢中,一大批才能杰出者,如賈誼、張釋之、晁錯等,脫穎而出成為文帝時期的智囊名臣。文帝的察舉制,只看才能而不論門第、籍貫、貧富、學派,拓展了人才選拔范圍,網羅了大批智識之士。
對正反意見都會說好
大凡領導者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就必須具有容人、容言、容事之雅量,既要聽得進順耳之語,也要聽得進逆耳之言,要有聞過則喜、則改的大度和涵養。
有一次,漢文帝和馮唐閑聊,提及廉頗、李牧等戰國名將,這使正在為匈奴之侵而犯愁的文帝大發感慨,認為自己若能得廉頗、李牧為將,就不用如此發愁。這時,馮唐就直言說,朝中即使有廉頗、李牧這樣的將軍人選,也不能被你使用。這明擺著是罵文帝乃無道昏君。對此公開挑釁和羞辱,文帝雖大怒,但以其寬容大度,并未對直言犯上的馮唐進行處罰。相反,在過了一段時間后,他倒想知道馮唐為何如此講,于是馮唐就道出了其中緣由。云中太守魏尚在抗擊匈奴入侵時,公正無私、勇猛殺敵,從而使匈奴聞風喪膽,不敢侵犯,但就因為報功時多報了六個首級,被撤職查辦,此足以說明文帝有將而不能用。這時,文帝以其寬厚仁慈的胸懷,諒解了魏尚之錯,派馮唐持符節到云中,赦免魏尚并官復原職。文帝待人以寬的用人氣度由此可見一斑。
據《資治通鑒》記載,文帝每上朝,只要大臣提出意見,文帝就必然會停下來專心聽取。意見如果不可用就先擱置,意見如果合理可用就及時采納。文帝的可敬之處就在于,無論意見可用與否,他都會說好,這就極大地鼓勵了群臣繼續提出各種建議。
一次,文帝過橋,有人從橋下走出來,驚了御馬,文帝要求對其處以極刑,而廷尉張釋之則認為“法者,天下所與天下公共也”,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應因人而異,所以按照法律只能對此人處以罰金。這種無視皇帝尊貴的諫言,最終被皇帝點頭稱是。從文帝一生看,他自始自終做到了接納諫言,并且沒有殺過諫官,由此足可以看出他納諫之真誠。(摘自《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