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一個塵封垢埋卻愈見光輝的靈魂
◎梁衡
從來的紀念都是史實的盤點與靈魂的再現。
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了。這是一個歡慶的日子,也是一個緬懷先輩的日子。我們當然不會忘記毛澤東、鄧小平這兩位使國家獨立富強的偉人;我們不該忘記那些在對敵斗爭中英勇犧牲卻未能見到勝利的戰士和領袖;同時我們還不能忘記那些因為我們自己的錯誤,在黨內斗爭中受到傷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領導人。這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就是張聞天。
一把鑰匙解黨史
張聞天曾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說,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書記: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實際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張聞天。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張接替博古做總書記,真正是“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張領導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華民族命運的重要轉折期。
現在回頭看,張在第五任總書記任上干了三件影響中國歷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澤東扶上了領袖的位置,成就了一個偉人。二是正確處理“西安事變”,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得到了難得的喘息之機,并日漸壯大。三是經過艱苦工作實現了國內戰爭向民族抗日戰爭的轉變,共產黨取得了敵后抗戰領導權,獲得民心,從此步步得勢,直至取得政權。
張聞天性格溫和,作風謙虛,決不戀權。他任總書記后曾有三次提出讓位。第一次是遵義會議后黨需要派一個人到上海去恢復白區工作,這很危險,他說“我去”。中央不同意,結果派了陳云。第二次是張國燾搞分裂,向中央要權,為了黨的團結,張說“把總書記讓給他”,毛說不可,結果周恩來讓出了紅軍總政委一職。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會前王稼祥明確傳達了共產國際支持毛為領袖的意見,張就立即要把總書記的位子讓給毛。因為其時王明還在與毛爭權,毛的絕對權威也未確立,還需要張來頂這個書記,毛就說這次先不議這個問題。
忍辱負重20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張作為政治局委員要求去東北開辟工作。他先后任兩個省省委書記。
早在晉西北、陜北調查時,張就對經濟工作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急切地想去為人民實地探索一條發展經濟、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熱心研究新問題,又幾乎是張的天賦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后,他和戰友們成功地促成了從國內戰爭向民族戰爭的轉變,這次他也渴望著黨能完成從戰爭向建設的轉變。他總結出未來的6種經濟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資。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東北時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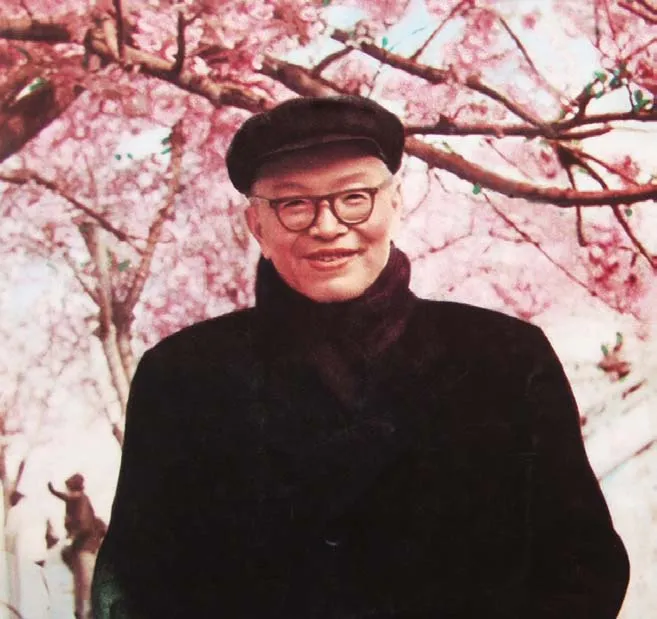
但是好景不長,1951年又調他任駐蘇聯大使,這顯然有外放之意。當時周恩來兼外長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議調張聞天回來任常務副部長,但外事活動又不讓他多出頭。1956年黨的八大,張聞天以一個從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身份要作一個外交方面的發言,不許。雖然遠離權力中心,但作為旁觀者,張聞天在許多大事上表現得驚人的冷靜。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盡力抵制,保護了一批人。1958年“大躍進”,全國處在一種燥熱之中,浮夸風四起。他雖不管經濟,卻力排眾議,到處批評蠻干,在政治局會議上大膽發言。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是個標志,提出鋼鐵產量翻一番,全國建人民公社,運動一哄而上。10月他在東北考察,見土高爐遍地開花,就對地方領導說這樣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壘起了小高爐。他說這是胡來,要求立即下馬。
張聞天在黨內給人留下的形象是犯過錯誤,不能用,可有可無。對張來說,這20年來給多少權,干多少活,相忍為黨,盡力為國,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個勤于思考的人,整日在基層調查研究,接觸工農群眾,工作親力親為,又有扎實的理論基礎,自然會有許多想法。無論怎樣地看他、待他,為黨、為國、為民、為真理,他還是要說實話的。廬山上的一場爭論已經不可避免。
一鳴驚破廬山霧
1959年7月2日中央開廬山會議,張聞天本可不去,但看到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他決定去。彭德懷本不準備上山,張力勸彭去。不想這一勸竟給兩人惹下終身大禍。
21日下午,張帶著幾天熬夜寫就的發言提綱,向華東組的會場走去。又一顆炸彈將在廬山爆炸。
華東組組長是柯慶施。張在柯主持的小組發言,可謂虎穴掏子,他的發言不斷被打斷,會場氣氛如箭在弦。張卻泰然處之,緊扣主旨,娓娓道來。
他足足講了三個小時,整個下午就他一人發言。稿子整理出來有8000多字。
毛澤東大為震怒。兩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個疾言厲色的發言,全場為之一驚,鴉雀無聲,整個廬山都在發抖。8月2日毛又召集所有的中央委員上山,工作會議變成了中央全會(八屆八中全會)。這天毛在會上點了張聞天的名,說他舊病復發。當天又給張寫成一信并印發全會,滿紙皆為批評、質問。
毛的講話和信給張定了調子:“軍事俱樂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黨集團”。會議立即一呼百應,展開對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賬,說什么歷史上忽左忽右,一貫搖擺。就這樣他成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副帥。
為了黨的團結,張聞天顧全大局違心地檢查,并交了一份一萬字的檢查稿。但是還是通不過,9日那天他從會場出來,一言不發,要了一輛車子,直開到山頂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漢茫茫,四野蒼蒼,亂云飛渡,殘陽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無淚。
他幾次求見毛澤東,毛澤東拒而不見。會議結束,8月18日張聞天下山,回到北京。
留得光輝在人間
廬山一別,張與毛竟成永訣。
到“文革”一起,他這個曾經的總書記又受到當年農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士窮而節見,他已經窮到身被欺、名被辱、命難保的程度,卻不變其節,不改其志。他將列寧的一句話寫在臺歷上,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
1969年10月18日,他被化名“張普”流放到廣東肇慶。肇慶5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輝頂點。軟禁張聞天的這個小山坡叫“牛岡”,比牛棚大一點,但仍不得自由。他像一個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臺下,但他并不急著爬起來,他暫時也無力起身,就索性讓自己安靜一會兒,躺在那里看著天上的流云,探究著更深一層的道理。
每當夜深人靜,繁星在空,他披衣攬卷,細味此生。他會想起在蘇聯紅色教授學院時的學習,想起在長征路上與毛澤東一同反思五次反圍剿的失利,想起廬山上的那一場爭吵。毛澤東比他大7歲,他們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吵出個結果,而國家卻日復一日地政治混亂,經濟崩潰。他將這些想法,點點所得,寫成文章。這些文字已是紅葉經秋,寒菊著霜,字字血,聲聲淚了。
張聞天接受七千人大會后的教訓,潛心寫作,秘而不露。眼見“文革”之亂了無時日,他便請侄兒將文稿手抄了3份,然后將原稿銷毀。這些文章只有作為“藏書”藏之后世了。這批珍貴的抄件,后經劉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來,學界稱之為《肇慶文稿》。
1974年2月經周恩來干預,張聞天恢復了組織生活。1976年7月1日,在黨的55周年生日這一天,這個五朝總書記默默地客死他鄉。他臨死前遺囑,將解凍的存款和補發的工資上交黨費。這時距打倒“四人幫”只剩三個月。
他去世后三個月,“四人幫”倒臺,三年后中央為他開追悼會平反昭雪。鄧小平致悼詞曰:“作風正派,顧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爭。”1985年,他誕辰85周年之際《張聞天選集》出版,1990年他誕辰90周年之際四卷本110萬字的《張聞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誕辰110年之際,史學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張聞天熱,許多研究專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