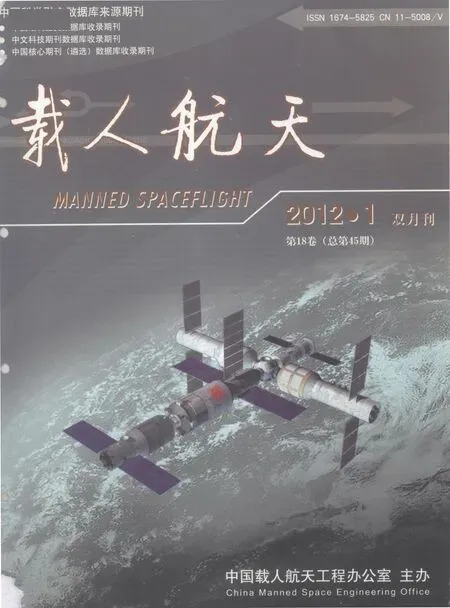論中國載人空間站國際合作的法律環境
夏春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北京100083)
1 引言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實施以來,成就斐然,引發了主要航天大國媒體的一系列反應,有對中國科技進步的贊嘆和祝福,有希望擴大同中國合作的意愿,也有對自身優勢地位受到挑戰的擔憂。中國載人空間站工程實施和首次無人交會對接圓滿成功之后,世界更加關注中國的航天工程,國際合作會更加頻繁;美國航天飛機終止服役,國際空間站于2020年達到設計壽命,中國和其他國家在載人航天領域開展合作,面臨著較為有利的航天市場機遇和共贏的局面形勢。中國一貫反對外空武器化和外空軍備競賽,堅持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并主張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增進和加強空間領域的國際合作。目前中、德兩國合作的空間生命科學實驗,即是這一原則立場的具體實踐,也為今后我國載人空間站的國際合作創立了良好開端。
本文以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法上的國際合作原則為基礎,探討與分析國際空間合作這一特殊國際合作形式的理念、現實與前景,揭示我國載人空間站國際合作的法律環境,并以國際空間站的國際合作法律框架為參照,研究構建我國載人空間站國際合作法律框架的重要因素,為其他國家參與我國載人空間站活動提供法律依據。
2 國際合作原則與國際空間合作的理念和現實
2.1 國際關系和國際法上的國際合作原則
自現代主權國家成立以來,沖突與合作一直是國際關系的兩種重要模式。《聯合國憲章》第一條明確將“促進國際合作”作為聯合國宗旨之一。1945年以后,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系列文件進一步對“國際合作原則”作出規定,并將該原則上升為一項具有普遍意義的現代國際法基本原則。例如,1955年亞非會議通過的《關于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就提到了“促進相互的利益和合作”的原則。1970年通過的《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確立了七項原則,其中第四項規定了“各國依照《憲章》有彼此合作之義務”。1974年聯合國大會相繼通過了《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行動綱領》和《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指出“所有國家有義務個別地和集體地進行合作”,并把“國際合作以謀發展”規定為所有國家的“一致目標和共同義務”。從以上文件來看,國際合作已成為國際法的基本原則。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結束、全球經濟一體化速度加快以及環保問題、難民救助、毒品控制、恐怖主義等新的全球性問題的出現,各國開始在反恐以及國際環境保護等非傳統安全問題領域開展大規模合作。但應看到,并非在所有領域的國際合作都取得了有效進展。著名國際法學者安東尼奧·卡塞斯指出,聯合國體系下的國際合作主要在經濟與社會領域展開合作,特別是在農業與發展、環境保護、兒童福利以及人權保護方面較有成效,而在一些敏感領域——例如裁軍和核不擴散,國防合作的成就最小。他認為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這些問題的決定權仍然控制在主權國家手中,而相互沖突的經濟、地緣政治及意識形態利益已經深深地使這些國家分化了。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將政治分為高級政治和低級政治,其中高級政治是指政治、軍事、安全等領域;而低級政治則是指經濟、文化、環境等領域。該理論認為,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各國之間在高級政治領域里主要關注的是相對獲益,這里充滿了沖突,因此很難協調;而在低級政治領域中國家關注的是絕對獲益,相關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相對容易找到共同點,因此合作的可能性較大。非傳統安全問題多為低級政治領域中的問題,易于謀求合作。
2.2 國際空間合作的理念與現實
2.2.1 國際空間合作的國際法
人類探索外層空間的活動始于1957年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成功。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外空活動被打上了冷戰的烙印,外層空間成為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彰顯國家實力的戰場。隨著冷戰結束和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動,空間大國由對立轉為適度合作。
最早規范外層空間活動的國際文件中已經提及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1961年聯合國成立和平利用外空委員會,并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外空和平使用之國際合作》決議,提及加強外空領域國際合作的迫切需要,但該決議主要是強調了聯合國應在外空和平探測及使用方面成為國際合作的焦點,負責協調和協助有關空間物體登記以及國際合作方面的活動。1967年生效的《外空條約》是外空活動的國際法基石,該公約第三條指出締約國探索和利用外層空間應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及增進國際合作與諒解而進行;該公約第九條具體規定了外空活動的合作和互助原則,并指出締約國進行外空研究和探索時對可能產生的有害干擾應負有進行國際磋商的義務,這是外空活動中國際合作義務的具體體現。1968年生效的《營救協定》對發射國與締約國就航天員營救和外空物體歸還方面的規則,表明了外空領域國際合作的進一步深化。1972年生效的《責任公約》以及1976年生效的《登記公約》所制定的規則和程序,也都有助于加強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層空間方面的國際合作。1984年生效的《月球協定》除了再次確認國際合作原則之外,還在第15條中規定“每一締約國應查明其他締約國從事探索及利用月球的活動確是符合本協定的規定,并為此目的,在月球上的一切外空運載器、裝備、設施、站所和裝置應對其他締約國開放。”以公約條文形式,規定了締約國的月球站所和裝置應對其他締約國開放的義務。1996年12月13日,聯合國大會還特別通過了《關于開展探索和利用外層空間的國際合作,促進所有國家的福利和利益,并特別要考慮發展中國家的需要的宣言》(簡稱《國際空間合作宣言》),該宣言鼓勵各國在公平和可以相互接受的基礎上、采取最有效和適當的方式、自行決定參加探索和利用外層空間的國際合作,并要特別考慮發展中國家的需求。
由此看來,多個國際文件提到了外空國際合作原則。此處有必要對這些國際文件的效力作一分析。《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列舉了幾種重要的國際法淵源,分別是國際條約、國際習慣法、一般法律原則、司法判例和各國權威最高之公法家學說。一般認為,前三種是有約束力的國際法淵源,而其中又以國際公約為最便于使用的國際法。《外空條約》、《營救協定》、《責任公約》、《登記公約》和《月球協定》這五大外空條約對締約國來說是有約束力的國際法,這些公約均不同程度地提及了國際合作原則。除了《營救協定》和《月球協定》為營救航天員和歸還空間物體以及開放月球站所及裝置設定了較為具體的國際合作義務之外,其他針對國際合作的規定較為概括,并未明確外空活動的國際合作的實體性或程序性規則,也未規定不進行合作的法律后果,可以說,這些規定多為倡導性的指南。而《月球協定》迄今為止只有13個成員國,主要航天大國均未參加這一協定,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協定的效力,也反映了航天大國對承擔外空國際合作義務的保留態度。
2.2.2 國際空間合作的現實
自人類開始探索外層空間以來,不乏國際合作的實踐。特別是在東歐劇變、冷戰結束以后,美、蘇兩個航天大國也開始進行適度的空間合作。目前,國際空間合作有以下幾種模式:
第一,各國通過聯合國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及其分委會以及其他國際平臺,共同應對外空活動的新問題,比如空間碎片減緩等。
第二,成立區域性空間合作組織,協調區域性空間活動。例如,歐洲18個國家于1975年成立的歐洲航天局(ESA)通過其理事會制定空間探索計劃、共同開展空間探索活動。再如,中國等八國于2005年成立亞太空間合作組織,以期推動亞太地區空間科學技術及其應用領域的合作。
第三,通過雙邊或多邊形式,在具體工程或項目上開展深入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際空間站這一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空間合作項目,其法律框架不僅繼承了現有聯合國五大外空條約的原則和規則,又通過特有制度豐富了國際空間法的內容。
從我國的空間國際合作實踐看,主要是與阿根廷、巴西等多國簽署了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合作協定和空間項目合作協議,與一些國家建立了航天合作分委會或聯委會合作機制、或簽署了空間合作諒解備忘錄,與巴西開展地球資源衛星合作,與德國開展載人航天空間科學實驗研究。同時,與法國在空間科學、衛星應用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取得重要進展,還為其他國家提供整星制造與發射服務。通過具體工程和項目的深入合作,是目前國際空間合作的典型模式,也更容易取得明顯的成效。
3 中國載人空間站國際合作法律框架的構建——以國際空間站法律框架為參考
3.1 國際空間站的法律框架
建設國際空間站的目的是探測、研究和開發空間,以美國和俄羅斯為首,包括加拿大、日本、巴西和歐空局(其中的11個國家)共16個成員國參與研制建設。國際空間站的成員國通過提供空間站的組成部分,獲得對空間站一定的使用權。隨著我國載人航天事業的不斷發展,必將在更大領域和范圍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因此,我國有必要了解國際空間站的法律框架,并提早籌劃與其他國家在載人航天領域開展合作所應遵循的法律框架。
以國際空間站成員國于1998年在華盛頓簽署的《加拿大、歐空局成員國、俄羅斯聯邦、美國政府間關于民用國際空間站合作協議》(簡稱《協議》)為基本法,輔以成員國之間簽署的諒解備忘錄、一系列執行安排和合同等,共同構成了國際空間站的法律框架。依據內容和發揮作用的不同,可將該法律框架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是現有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外層空間條約體系的規定。《協議》首先宣布其活動遵守國際法、特別是外層空間條約的規定,繼承了《外空條約》關于外層空間無主權的規定;肯定了各成員國依據《登記公約》對其提供的空間站組件進行登記并由此享有管轄權、控制權和所有權;《協議》并未否認《責任公約》規定的兩種責任形式,但是鼓勵通過空間站進行外空探索、開發和利用活動。
第二是根據國際空間站實際情況所創設的特有制度。主要包括:(1)《協議》首次開創性地制定了交叉豁免制度,即對不同成員國(包括其相關實體)之間在參與“受保護的空間活動”時所產生的損害賠償之請求給予責任豁免;(2)《協議》第22條規定,針對出現在國際空間站的刑事犯罪活動,一國除了可以行使屬人管轄權之外,還可針對其他國家國民的犯罪行為同犯罪嫌疑人所在國進行磋商,而在犯罪分子所在國允許、或者雖未允許但在90日內未承諾將該犯罪嫌疑人送本國有權機關起訴的情況下,該國可以對他國的國民行使刑事管轄權,同時該國可以將《協議》視為引渡該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基礎,這一刑事管轄權的創新突破了原有國際空間條約僅規定對空間物體的管轄權和控制權的規定,是載人航天活動催生的法律制度;(3)《協議》第21條為保護知識產權,將在空間站各組成部分上進行的活動視為在該組成部分登記國領土上進行的活動,從而符合了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特征以及有關國內法律的規定。
第三是成員國之間的諒解備忘錄以及規范國際空間站人員行動的《行為守則》。諒解備忘錄是處理較小事項的條約,對簽署國也有法律約束力。
第四是更為具體的執行安排以及成員國之間、或者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以及私營主體之間簽訂的一系列使用空間站的合同。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國際空間站項目具備了一套完備、但并不算復雜的法律制度,這套法律制度既繼承了現有國際空間條約的規定,使參加國在空間站法律下的權利義務與其在外層空間條約下的權利義務保持一致,又切合實際地發展了新的法律制度來應對國際合作的需要。這套法律制度的構成,既有總括性的基本法、從而保證重要制度的基礎性地位,又允許更為靈活多變的諒解備忘錄、雙邊協定和合同的存在,滿足了各參加國空間探索活動和國際合作活動的需求多樣式。《協議》作為契約型多邊條約,有序地指引著成員國參加空間站的活動。
3.2 中國載人空間站的國際合作法律框架構建
中國載人空間站的法律構建應當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國內層面的載人空間站法律,主要規定空間站的建設和管理主體及管理機制,國內參與者、參與方式和活動內容,以及與之有關的知識產權、融資、保險等一系列制度;第二個方面中國載人空間站的國際合作法律框架,探討這個問題的前提是在未來載人空間站的建設和運營當中,國際合作不可避免,而法律框架的構建有助于我們在掌握主動權的情況下,與其他國家實現共贏。
構建中國載人空間站國際合作法律框架,應注意以下四個問題:
首先,應承諾遵守我國已經加入的主要聯合國外空條約(《外空條約》、《責任公約》、《登記公約》和《營救協定》)的規定,并作為國際合作的基礎。但同時在一些敏感和關鍵問題上,要把握主動權。比如,《外空條約》規定締約國應專為和平目的使用月球和其他天體,并承諾不在外層空間設置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種類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有學者將這一規定籠統地解釋為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原則,但是對于何為“和平利用”,各國有不同的解釋。《協議》將國際空間站定性成為和平目的而設的民用空間站,但是對于在某個空間站組成部分上進行的空間探索活動是否符合和平目的,由提供該組成部分的成員國決定,這一規則給空間站組成部分的提供國以一定的主動權。我國載人空間站的建設讓一些國家懷疑我國將對空間進行軍事利用,因為這些國家可能誤認為中國的太空計劃“實際上是由人民解放軍主導推進的”。其實,其他許多國家的太空活動均有軍事人員參與,這并不意味著有關太空活動就成了對外空的軍事化利用,何況《外空條約》也“不禁止為了科學研究或任何其他和平目的而使用軍事人員”。但盡管如此,對于諸如“為和平目的之定義”等敏感問題,在構建載人空間站國際合作法律時,我國應掌握定義的主動權。
第二,應根據我國允許外國參與我國載人空間站建設和使用的程度和范圍,同時考慮外國參與的意愿與能力,來設計我國載人空間站國際合作的基本法。從宏觀方面,該基本法應定明此種國際合作的前提、原則、重要決策規則和程序;從微觀方面,應規定載人空間站的管轄權、可獨立區分的空間物體的登記管理辦法、在空間站進行實驗所產生的知識產權歸屬等具體問題。基本法的設計可以參考國際空間站的法律框架,但同時必須注意到國際空間站的建設模式與我國載人空間站的建設模式的不同,應在充分維護我國權益的基礎上,設計國際合作的各種基本原則。
第三,可以通過雙邊協定或者諒解備忘錄形式,與有關國家開展具體合作。對與神舟八號飛船上中德合作項目相類似的活動,就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其特點是更為具體、靈活。
第四,應考慮到未來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外空商業化利用的趨勢,法律設計應具有前瞻性。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為促進以空間資產為擔保進行融資,正在起草《空間資產特定問題議定書》。2011年2月第五次專家委員會會議之后形成的草案文本,將提交給2012年2月在柏林召開的外交會議,以便討論通過。目前看來,中國以及其他航天大國很有可能會批準這個議定書,該議定書會在很大程度上便利衛星、空間站、太空艙、指令艙以及其他可獨立識別的航天器或者有效載荷等高價值空間資產的跨國融資和流轉。中國在設計國際空間合作的法律規則時,要考慮到該議定書的影響,并作出有效應對。
4 結束語
和平利用外層空間以及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基礎上增進和加強空間領域的國際合作,一直是我國政府在航天領域的政策和立場。在我國載人航天工程后續研制建設過程中開展s國際合作符合上述原則,具有現實性和可行性。國際合作原則不僅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外空法上的重要原則。若僅作為一項倡導性的原則,國際合作并不難被各國所接受。然而,通過多邊公約、在一般意義上設定更為具體的合作義務的動議,則很難獲得廣泛支持,主要航天大國拒絕加入《月球協定》就是一個明證。國際合作原則的實現首先取決于國家的意愿,其次則需要在具體航天工程中推動規范合作的法律框架的構建。國際空間站完備的法律框架為國際空間合作提供了良好范本,中國載人空間站項目應及時籌劃國際合作層面的法律框架,在遵守主要外空條約的基礎上,根據各國的參與程度,設計以我國為主導的空間合作的基本法來規范空間合作的一般性重大問題,并輔之以雙邊合作協議或者諒解備忘錄來規定具體合作內容。空間合作的法律既要適應現實需要,又要具有前瞻性,特別是應對日益發展的空間商業化利用的要求。 ◇
[1][意]安東尼奧·卡塞斯.國際法(蔡從燕等譯)[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He Sibing.What Next for China in Space after Shenzhou.Space Policy[J].2003-19(3).
[3]大衛·鮑德溫.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4]賀其治.外層空間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
[5]李浩培.條約法概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王鐵崖.國際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7]王秀梅.論非傳統安全與國際合作原則.世界經濟與政治[J].2005(7).
[8]夏春利.論國際空間站的法律框架與國際空間合作立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2010(5).
[9]趙長峰.現實主義國際合作觀探微.現代國際關系[J].2005(1).
[10]中國科學院空間領域戰略研究組.中國至2050年空間科技發展路線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