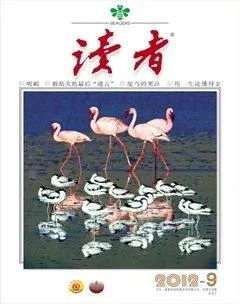一百年前的領(lǐng)導(dǎo)干部
柴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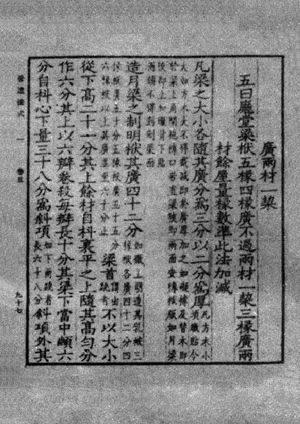

一
看了胡勁草的紀(jì)錄片才知道,梁思成與林徽因的一生,與一個(gè)人關(guān)系巨大。
1928年,他們選擇在3月21日結(jié)婚,選這個(gè)日子,因?yàn)槭撬未ㄖ蠼忱钫]墓碑上刻的日期。
慚愧,我只知魯班,不知李誡。
李誡的《營造法式》是梁思成的父親梁啟超寄給他們的,信中寫道:“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己朱桂辛校印莆竣贈(zèng)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寶之。”
這本書影響了梁林終生。
二
像我這樣對建筑一無所知、只知道些梁林往事的人,只能模糊猜測,營造學(xué)社?這是清華大學(xué)或者東北大學(xué)的吧?
看了紀(jì)錄片才知道,這完全是個(gè)私人機(jī)構(gòu)。
創(chuàng)辦人就是梁啟超信中所說的贈(zèng)書者“朱桂辛”——朱啟鈐。李誡的書失傳多年,也是由他發(fā)掘的。
我沒太留意,以為朱也是像梁啟超一樣的知識(shí)分子。再看他的照片,穿長袍,一副老實(shí)樣子,看上去是一個(gè)土氣的老頭兒。
紀(jì)錄片中說,這人是當(dāng)時(shí)的內(nèi)務(wù)部總長﹑交通部總長﹑國務(wù)總理。
咦?領(lǐng)導(dǎo)干部?
三
后來查資料才發(fā)現(xiàn),朱啟鈐是個(gè)好玩的人。
他這人,用曹聚仁的話說,“會(huì)做官”,一輩子,從晚清、北洋政府、民國、新中國……一個(gè)都沒耽誤。
他的外祖父是漢學(xué)大師的弟子,他舊學(xué)很好,母親常把一些宋錦碎片綴合成荷包,祖父書畫的包頭用的是《紅樓夢》里寫過的寸金寸絲的緙絲。他后來對藝術(shù)的感情,一直有童年的這一縷纏綿。
他在湖南長大,正趕上清末鐵銹的大門被“嘎嘎”推開,天風(fēng)海雨,交織而來。湖南又是晚清牛人輩出的地方,就算是官僚,像巡撫陳寶箴和學(xué)政江標(biāo),也是氣象開闊。
小朱同學(xué)正年輕,風(fēng)華正茂,“往來吳會(huì),頗與其邦賢士大夫游,益憤切,喜改革之說”。
但朱不僅是文人,22歲從地方上的工程小官做起,一路干活干起來的,走的是經(jīng)世致用的路子。
1905年,他在晚清創(chuàng)建了“京師警察”制度。當(dāng)時(shí)的警察什么都得管,安全、交通、消防、衛(wèi)生、社保、救濟(jì)……曹聚仁寫過:“我們?nèi)缃窨磥恚焖愕檬裁矗吭诋?dāng)時(shí),卻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輕有膽識(shí)敢作敢為的敢去推行。”
比如,你動(dòng)一盞燈試試。
北京的晚上一直烏漆墨黑,朱啟鈐想在北京街上裝路燈,京師某御史以自家數(shù)世夜不燃燈為由,向皇帝彈劾他。
曹聚仁說:“朱啟鈐還在外城大柵欄推行過單行道制,而敢違犯這規(guī)矩的乃是肅王善譽(yù)的福晉,他們有勇氣判罰那福晉銀元十元,真是冒犯權(quán)威,居然使肅王聽了折服,這才施行得很順利。”
在一個(g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國,有什么公共生活可言?但朱啟鈐才30出頭,決心動(dòng)它一動(dòng)。
四
袁氏當(dāng)國時(shí),1913年,朱啟鈐當(dāng)了內(nèi)務(wù)部總長。中國的城市化是被資本的力量拱出來的,京奉、京漢兩條鐵路一路修到了前門,兩邊商鋪雜立,首都第一次出現(xiàn)擁堵。
最堵的地點(diǎn)就在正陽門,要想治堵,就得在這個(gè)門上動(dòng)土開洞,這是個(gè)扎手的事兒,而且政府說了,修路挺好,但我沒錢。
朱找到鐵路經(jīng)營者,說,你看這也是為你們好,你們出錢吧,出了錢,回頭舊城的土你們還可以拉走墊路,留下點(diǎn)兒給我種草種花就成。就這樣,他把清理的費(fèi)用都省下來了。
他把正陽門兩側(cè)打開兩個(gè)大洞,東進(jìn)西出,又打通府右街、南長街與北長街、南池子與北池子,開通長安街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
當(dāng)時(shí)的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評價(jià)他:“作為一個(gè)建設(shè)者,他成了北京的奧斯曼男爵。”
奧斯曼是拿破侖三世時(shí)期法國塞納省行政長官,對巴黎做過大規(guī)模市政改造,建設(shè)新的給水和溝渠系統(tǒng),建設(shè)新的輻射狀街道網(wǎng)絡(luò)并開辟公園。
不過我覺得這個(gè)比喻背后還隱隱有一層意思,是指朱啟鈐和奧斯曼都受到了背后的獨(dú)裁者的支持。
袁世凱為了支持他,送他一把銀鎬,紅木銀箍,上鐫“內(nèi)務(wù)部朱總長啟鈐奉大總統(tǒng)命令修改正陽門,朱總長爰于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舊城第一磚,俾交通永便”。
五
1928年,梁思成﹑林徽因搭火車回京。“車頂上坐滿了搭霸王車的旅客……就這樣到了北京,一個(gè)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個(gè)鼻孔里是糞臭……”
這不奇怪。1900年,仲芳氏在《庚子記事》里寫:“近來各界洋人,不許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潑倒凈桶……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經(jīng)洋人撞見,百般毒打,受此凌辱者,不可計(jì)數(shù)。”
中國城市公共衛(wèi)生的開始,居然是這么個(gè)方式,看了讓人心里有說不出的滋味。
一直到了民國,公共廁所是什么樣子?徐城北寫過——當(dāng)時(shí)京城最繁華的前門,大戲園子的右側(cè),有一個(gè)非常大的露天尿池,無論觀眾還是演員,一旦需要,都立刻跑到那里“直射水龍”。
朱啟鈐當(dāng)內(nèi)務(wù)部總長的時(shí)候兼京師市政督辦,治理北京街市溝渠,“辟城門,開馳道,浚陂阪池,治積潦,塵壤壅戶者除之,敗垣侵路者削之,經(jīng)界既正,百堵皆興”。
中國的城市從來沒有過行道樹,朱啟鈐第一次在北京道路兩旁種上槐樹,沿護(hù)城河栽上楊柳,這才有了今天的秋黃冬白春綠,以及盛夏時(shí)我們頭頂?shù)臐馐a。
六
北京的第一座公園也是朱啟鈐開辟的,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園。這里原是皇家祭祀的社稷壇,清帝退了位,沒人管,壇里榛莽叢生,蛇鼠為患。
朱啟鈐說想建個(gè)公園,北洋政府說行,你干吧,但我還是沒錢。
他就自個(gè)兒干,先捐出一千元,成立一個(gè)董事會(huì),然后對外募捐。不到半年就籌了4萬多元,捐得最多的是徐世昌、黎元洪、楊度和他自己,公園就這么建成了。
朱啟鈐又出面交涉,在公園與故宮之間開了扇門,把西華門內(nèi)的武英殿辟為展室,展出皇家珍寶,起名“文物陳列所”。這是中國第一個(gè)博物館,也是故宮博物院的前身。
七
1915年,他43歲,支持袁世凱稱帝,還是大典籌備處處長。袁死后他被通緝。咒罵他的人當(dāng)然很多,但也有人為他叫屈,說他當(dāng)時(shí)也是無奈,必須擁袁來保全自己,還有人說他是被挾持的之類。他終生沒提這事,沒辯解、沒懺悔,晚年在自己的年譜上寫過一字,說袁世凱“知”他,這大概算是芮恩施說的“骨子里他是完全中國式的人物”。
后來因?yàn)椤捌洳派锌捎谩保芸毂簧饷猓€被特派為南北議和總代表。談判破裂了,但路過南京時(shí),在藏書家陶湘那里淘到《營造法式》,這才見到最為完備的關(guān)于中國古代建筑的記載。
寫書的李誡生在北宋,北宋的建筑正值巔峰時(shí)期。李誡的記錄“上可以溯秦漢,下可以視近代”,像一個(gè)剖面,能看到什么是進(jìn)化,什么是退步;什么為固有,什么是輸入。建筑是一個(gè)國家文化史的演進(jìn)縮影,“移身換形,躍然可見”。
但古人的用語、句讀在千年之后已經(jīng)難看明白,朱啟鈐發(fā)起“營造學(xué)社”,專門研究這本書。一開始地點(diǎn)就在他家中,牌子也沒掛,幾張桌,請了幾位國學(xué)家,但老頭們懂古字,卻不懂建筑,還是搞不明白。
當(dāng)時(shí)在美國讀建筑系的梁思成也看不懂這書:“當(dāng)時(shí)在一陣驚喜之后,隨著就給我?guī)砹四蟮氖涂鄲馈驗(yàn)檫@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書一樣,無法看懂。”
一般人到這兒就停下了,這么復(fù)雜的事,傳之后世,讓將來的人去研究吧。但徐世昌對朱啟鈐有個(gè)評價(jià),叫“事必果干”,這個(gè)人有口倔強(qiáng)之氣,他的書房叫“一息齋”,出自朱熹的話“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八
費(fèi)慰梅說營造學(xué)社最初是“有錢人業(yè)余愛好的副產(chǎn)品”,用詞輕慢了點(diǎn)兒。朱確實(shí)會(huì)掙錢,在南北議和失敗后,退出政界從商。他娶的是曾國藩后人之女,她10歲才隨父親從巴黎回國。岳父對朱最大的影響是“西人以制造致富”,實(shí)業(yè)是一個(gè)國家現(xiàn)代化的基礎(chǔ)。朱興辦輪船公司、煤礦,是中國第一代實(shí)業(yè)家。但如果只是失意政客的賞玩,營造學(xué)社走不了那么遠(yuǎn)。學(xué)者王世襄曾經(jīng)受朱啟鈐的委托,注釋中國唯一的古代漆工專著《髹飾錄》。他說過:“可惜現(xiàn)在的人對朱啟鈐知道得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xué)術(shù)上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xué)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為學(xué)社請來當(dāng)時(shí)的學(xué)術(shù)精英,看了名單讓人感慨,一個(gè)私人組織可以達(dá)到這樣的規(guī)模——東北大學(xué)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學(xué)建筑系教授劉敦楨,建筑師楊廷寶、趙深,史學(xué)家陳垣,地質(zhì)學(xué)家李四光,考古學(xué)家李濟(jì)……美籍有瞿孟生、溫德、費(fèi)慰梅;德籍有艾克、鮑希曼;日本學(xué)者有松崎、橋川、荒木。
這是1929年。
朱啟鈐說:“全人類之學(xué)術(shù),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東鄰之友,幸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與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鄰之友,貽我以科學(xué)方法,且時(shí)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勵(lì)。”
這胸襟。
抱負(fù)也夠浩蕩的:“凡彩繪、雕塑、染織、鑄冶,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傳說儀文樂歌,一切無形之思想背景,屬于民俗學(xué)家之事,亦皆本社所應(yīng)旁搜遠(yuǎn)紹者。”
有這樣的愿望,就非得有大的視野不可,“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須作一鳥瞰也”。
當(dāng)時(shí)朱啟鈐57歲,雄心勃勃。
九
他邀請梁思成擔(dān)任法式部主任,其中一大任務(wù)就是對這部《營造法式》進(jìn)行研究。
梁受西學(xué)訓(xùn)練,知道要讀懂這部《營造法式》需要做大量的野外考察,這是最笨拙、最花錢、最費(fèi)力但也最有效的辦法。
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車和毛驢,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遠(yuǎn)的深山荒野,晚上冷了要把報(bào)紙蓋在被子上保暖。常常“暴雨驟至,下馬步行,身無寸縷之干……終日奔波,僅得饅頭三枚,人各一,晚間又為臭蟲蚊蟲所攻,不能安枕尤為痛苦”。
安全也不能保證,學(xué)社成員曾被扣押。朱啟鈐私人給各地官員寫信,要他們護(hù)衛(wèi)、照顧這些“柔弱書生”。
傳承幾千年的建筑,沒人知道是哪個(gè)朝代所建,沒數(shù)字、沒圖片、沒記錄。莫宗江說他們找到應(yīng)縣木塔后,“九層重疊,我們硬是一層一層,一根柱、一檁梁、一個(gè)斗拱一個(gè)斗拱地測,最后把幾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測完了。當(dāng)我們上到塔頂時(shí)已感到呼呼的大風(fēng)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剎還有十多米高,唯一的辦法是攀住塔剎垂下的鐵鏈上去,但是這900年前的鐵鏈,誰知道它是否已銹蝕,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雙腳懸空地攀了上去。”
林徽因當(dāng)時(shí)已患肺結(jié)核,但對艱苦考察中的記述卻是近乎天真的狂喜之情:“在草叢里讀碑碣,在磚堆中間偶然碰到菩薩的一只手、一個(gè)微笑,都是可以激動(dòng)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覺來的……我樂時(shí)就高興地笑,笑聲一直散到對河對山,說不定哪一個(gè)林子,哪一個(gè)村落里去!”
在山西他們確證了中國現(xiàn)存最古老的唐代佛光寺。夕陽西下,人都浸在滿天紅霞里,他們坐在寺院里,把帶去的全部應(yīng)急食品沙丁魚、餅干、牛奶等統(tǒng)統(tǒng)打開,大大慶祝了一番。
工作完,看舊報(bào)紙,他們才知道“盧溝橋事變”的消息——戰(zhàn)爭爆發(fā)已經(jīng)5天了。
十
梁林決定全家離京,朱啟鈐年老體邁,不堪跋涉,另外他有一層更深的考慮。他對樂達(dá)義說:“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我別的都不擔(dān)心,就擔(dān)心北平這座古城。北平就像一個(gè)珠寶店,處處是寶。如今仗打大了,炮彈、炸彈落在這兒,很容易就毀了文物古跡,而且無可挽回。”
他說從歷史上看,歷代宮室都難逃500年一輪回的大劫之災(zāi),而傳統(tǒng)木結(jié)構(gòu)建筑經(jīng)不起火焚、雷擊,圓明園的石結(jié)構(gòu)也逃不過兵燹之災(zāi)。
他要守住這老城。即使這座城被燒光了,他也要把它原樣再建起來。他對當(dāng)時(shí)北平最好的建筑師張鎛說:“應(yīng)對北平明清兩代保存下來的建筑做現(xiàn)場精確實(shí)測,留下真跡圖卷,否則難免遭日寇蹂躪或反攻時(shí)的兵燹之災(zāi)。”
張鎛用了3年半的時(shí)間,完成了這項(xiàng)工作。
有一年遇上天津水災(zāi),營造學(xué)社存在銀行庫房里的全部調(diào)查測繪資料都被水浸了,古建筑測繪圖稿的紙薄,又經(jīng)水泡,一不小心就潰破,朱啟鈐請人把它們逐頁晾干,再裱在坐標(biāo)紙上。由于底片已毀,朱啟鈐又將過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從這批復(fù)制膠片中選出了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筑圖片各加印兩套,寄給梁思成。
菜油燈的微光里,梁思成能寫成11萬字的《中國建筑史》,憑借的就是朱啟鈐寄來的史料。
十一
1946年,因?yàn)椤吨袊ㄖ贰返呢暙I(xiàn),美國耶魯大學(xué)邀請梁思成訪美并做學(xué)術(shù)報(bào)告,那是梁思成在學(xué)術(shù)上灼灼其華的時(shí)刻。
這一年,朱啟鈐已家財(cái)散盡,開始陸續(xù)變賣收藏的冊頁、手絹、鋼琴、舊錦等來維持生計(jì),再加上學(xué)社人員分散各地,營造學(xué)社只能停止活動(dòng)。
營造學(xué)社共走過中國11個(gè)省,總計(jì)190個(gè)縣、市,1937年前詳細(xì)測繪的建筑群有206組,所及建筑共2738幢,測繪圖稿1898張。中國人對中國建筑自遠(yuǎn)古至明清時(shí)期的歷史發(fā)展脈絡(luò),第一次有了較清醒的認(rèn)識(shí)。
這些資料最后都給了清華大學(xué)。清華大學(xué)的建筑系,就是靠這個(gè)起家。
直到現(xiàn)在,如建筑學(xué)者楊宇振所說:“中國古代建筑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基本框架,依然是六七十年前營造學(xué)社的成果,而且這些成果的獲得,主要集中在朱啟鈐任社長的短短十來年間——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實(shí)在不能不引起思考和反省。”
十二
1956年,已經(jīng)是清華大學(xué)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終于出版了《營造法式》(上卷),細(xì)加注釋,使《營造法式》不再是無人能識(shí)的天書。不過,此時(shí)中國營造學(xué)社卻被視做“反動(dòng)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已經(jīng)消散。
梁思成為這本書寫序時(shí),曾經(jīng)反復(fù)斟酌,做了3次修改。他先寫道:“另一方面,我們又完全知道它對于今天偉大祖國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并沒有什么用處。”想了很久,他把“用處”畫掉,改成“直接關(guān)聯(lián)”。后來,他又畫掉,留下了一份未定稿:“另一方面,我們又完全知道它對于今天偉大祖國的社會(huì)主義建設(shè)并沒有什么現(xiàn)實(shí)意義。”
這幾個(gè)詞,沉吟之間讓人心酸。
(徐道原摘自中國社會(huì)出版社《聲音博動(dòng)中國》第二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