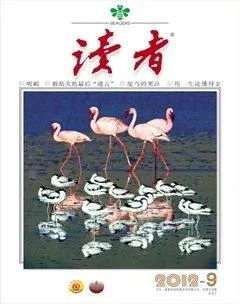老校長

我以前從來都不覺得香港的大學有多好。你看那些學生,畢業典禮上總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幼稚園結業呢。至于老師,不是不好,只不過研究成果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論文為主,書店很難見得著,不像大陸學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看他們的作品一字排開擺在書店,威風得不得了。校園氣氛就更不要提了,許多大牌學人來演講,也都只有小貓幾只去捧場。學術沙龍?那是什么東西呀?沒聽過!
直到近幾年在大陸跑多了,見過不少名牌學府的另一面,聽過不少著名“大師”的笑話,了解到整個內地高等教育界的運作方式之后,我才知道,原來香港的大學也不算太差。
你看,英國《泰晤士報》公布全球大學排行榜,香港有3家進了前50名呢。可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的前校長高錕,拿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這難道不是很威風嗎?但坦白講,當年我念書的時候可不認為他有這么厲害,相反,我們一幫學生甚至認為他只不過是個糟老頭罷了。那時,我的一個同學是學生報的編輯,他趕在高錕退休之前,在報上發了一篇文章,總結他的政績,標題里有一句“八年校長一事無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不只如此,當時高錕還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請,出任“港事顧問”,替將來的回歸大業出謀獻策。很多同學都被他的舉動激怒了,認為這是學術向政治獻媚的表現。于是在一次大型集會上面(好像是畢業典禮),學生們發難了,他們站起來,指著臺上的校長大叫:“高錕可恥!”而高錕則憨憨地笑,誰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后來,一幫更激進的同學主張“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營”,他們覺得那是洗腦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輸以母校為榮的自豪感,其實是種無可救藥的集體主義,很要不得。就在高錕對新生發表歡迎演講的那一天,他們沖上去圍住了他,塞給他一個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學生玩偶,意思是學生全被校方蒙成了呆頭。現場一片嘩然,高錕卻獨自低首,饒有興味地檢視那個玩偶。
后來我們才在報紙上看到了他的回應。當時有記者跑去追問正要離開的校長:“校長,你會懲罰這些學生嗎?”高錕馬上停下來,回頭很不解地反問那個記者:“懲罰?我為什么要懲罰我的學生?”畢業之后,我才從當年干過學生會和學生報的老同學那里得知,高錕每年都會親筆寫信給他們,感謝他們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這些熱心做事的學生忙得沒時間和大家一樣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會自掏腰包,私下捐給這兩個組織各兩萬港幣的補助金,請他們自行分配給家境比較困難的同學。我那位臭罵他“一事無成”的同學,正是當年的受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經回到母校任教了,在電話里他笑呵呵地告訴我:“我們就年年拿錢年年罵,他就年年挨罵年年給。”
前段時間,被我們中大人戲稱為“殖民地大學”的香港大學也出了條新聞,他們把名譽院士的榮銜頒給了宿舍“大學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蘇妹,因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響了大學住宿生的生命”。這位連字都不識的82歲的老太太,不只把學生們的肚皮照顧得無微不至,還不時充當他們的愛情顧問,在他們人生路上遇到困難的時候,以自己的歲月澆灌他們茫然的青春。
那一天,“三嫂”戴著神氣的院士圓帽,穿上紅黑相間的學袍,是一群重量級學者之間最燦爛的巨星。她一上臺,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來大聲吶喊,掌聲雷動。不管他們的頭發是黑是白,不管他們現在是高官議員還是富商名流,他們都曾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錕可就從來沒這么親近過了。8年里,我只當面對他說過一句話。那一天我和幾個同學從圖書館出來,正好看見他走在前面,馬上揉搓了一個紙團朝他丟過去。他一回頭,我就指著另一個同學笑著大喊:“校長,你看他居然亂丟垃圾!”總是笑得有點傻的校長一如以往,頓了一頓才反應過來,慢吞吞地說:“這就不太好了。”我們立即笑作一團,看著他的背影漸漸遠去。前一陣子,香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講“領導的藝術”,居然大談什么“包容是領導最重要的美德”,我聽了忍不住搖頭輕嘆:“你來我們這里講包容?”
2003年,高錕得了老年癡呆癥,記性有點衰退了。這也不是不好的,因為我希望他忘記我們當年的惡作劇,忘記我們侮辱他的種種言行。但我又是多么多么的盼望他,我們的老校長,能夠記住他得到的是諾貝爾獎;記住他提出光纖理論時的喜悅;記住他和夫人一起拖著手在校園里散步的歲月;記住我們畢業之后,偶爾在街上碰見他,笑著向他鞠躬請安“校長好”時的由衷敬意。
(極品咖啡摘自網易梁文道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