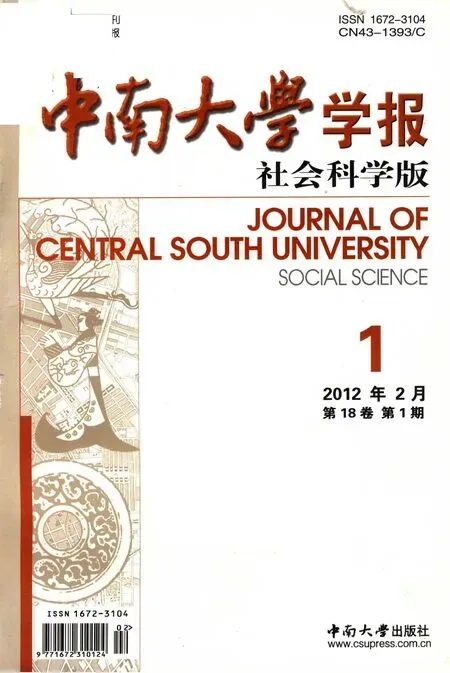論道學對榮格分析心理學的影響
呂錫琛
(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長沙,410083)
世界著名心理學家榮格堪稱研究、理解東方文化極為深刻的西方學人,他對易經、瑜珈和漢、藏佛教均有研究,對老莊思想和《太乙金華宗旨》等道教丹書尤為推崇。更值得關注的是,他不是從玄理的層面而是在心理學的框架中來討論和吸收道學的智慧。但學術界對于榮格與道學之聯系的研究尚不夠充分,其關注點多集中于榮格與道教內丹學的關系,有些評價還似顯保守。①
我們認為,不應忽視或低估道學對榮格分析心理學的影響,因為這些影響因子正可凸顯中國哲學的特性、優長及其現代價值。榮格從道學中獲得了哪些思想營養,而從榮格的探索中我們又能得到什么啟迪?本文試就這些問題作一探討。
一、對立統一思想對榮格的啟示
道學的對立統一思想對榮格的研究具有解困破冰的意義。當榮格在集體潛意識理論研究等方面陷于困境之時,他讀到德國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所翻譯的道教丹書《太乙金華宗旨》和《慧命經》,“被這部中國著作的奇思異想深深迷住”。[1](71)故他在《金華秘旨》德文第二版前言中強調:“正是《金華秘旨》(即《太乙金華宗旨》)這部著作,第一次把我推到了正確的方向上。結合對中世紀煉金術的長期研究,我找到了在意識自我和集體過程中存在的聯結點。”榮格對老子可謂推崇備至,他在自傳的結語中稱:“老子是有著與眾不同的洞察力的一個代表性人物……見多識廣的這位老者的原型是永恒地正確的。”[2](338)
通過《太乙金華宗旨》和《慧命經》的研究,他從實際操作的層面找到了一條實現人格整合的道路。榮格認識到,道教修煉是一個結合對立面的過程,而《太乙金華宗旨》這部著作就是一條能夠“從對立面的對立中解脫出來的道路”,由此,榮格開辟出了一條整合意識與潛意識,促進精神的正常發展的道路。關于道學對榮格潛意識理論的影響我們將在本文第二部分詳論,在此我們首先從方法論的層面論述榮格思想與道學對立統一思想的聯系。
對立統一思想是道家學派的基本哲學原則。《老子》第二章指出:“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恒也。”老子看到,善惡、有無、難易、長短、高下、前后等對立面皆存在著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關系。由此可以推論,對立事物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相互轉化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普遍規律,執著于一端、非此即彼的態度是不明智的,以這種思維定勢去處理問題往往會導致刻板僵化,主觀教條,激化矛盾等一系列的弊端。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這段話語啟示人們,如果人們一旦對于美丑、善惡產生分別之心,特別是了解到由它們所帶來的一系列利害,必然會自覺地努力追求美和善,也會去爭奪美、善之名,這種道德自覺意識的產生雖然有利于引導人們趨善棄惡,這是積極的一面,但與此同時亦有消極的一面,即人們會否認內心中的一些惡的東西,而掩蓋自己內心的陰影。但掩蓋和否認并不能真正驅除惡的陰影,反而會產生嚴重的問題,如此一來,豈不是“斯惡矣”、“斯不善矣”?
在對立統一的辯證智慧指引下,老子采取了與眾不同的處世之道:“不尚賢”、“和其光,同其塵”,更提供了一種可操作原則“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老子》第三章、第四章、第四十九章)這就進一步彰顯了運用對立統一智慧的實際功效。如果以排斥的態度對待不善,其實并不能真正達到預期的目的。而包容不苛、不棄不離的仁慈之心才是醫治心理疾病的良方,才能更好地挽救那些有缺點、有過失甚至有嚴重錯誤的人,真正化解人們心靈深處的郁結;而以兼收并蓄的廣闊胸懷來處世治世,才有可能感化頑冥,從根本上化解社會矛盾,創建一個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和諧社會。
在道學對立統一思想的啟示下,榮格從治療方法上突破了西方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他在《現代靈魂的自我拯救》一書中深刻地批評西方人在這方面的誤見:“我們有個錯誤的觀念,認為一旦從陰暗面去解釋的話,那么明亮的一面已不復存在矣。很不幸的,佛洛伊德本人就犯了這個錯誤。其實,陰暗是光明的一部分,正和惡與善之關系的道理是一樣的,而且其逆亦真。因此,我愿不顧眾人的驚愕,毫不遲疑地暴露我們西方思想的錯幻和渺小……這便是一項東方人的真理。”[3](74?75)“有一千年之久的東方典籍能把富有哲理性的相對論介紹給我們。”[3](325)在這里,榮格雖然未具體指明這種“真理”出自哪一位“東方人”或“東方典籍”,但以榮格對道家思想的熟悉和推崇程度來看,我們有理由認為,榮格所說的“富有哲理性的相對論”的“東方典籍”當指老莊的學說。
《莊子》不僅發展了老子的對立統一思想,強調“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莊子·則陽》),更從不同的角度指出了事物性質的相對性。如,在《齊物論》中,他從事物本身差異來說明事物認識標準的相對性:“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鰍然乎哉?木處則惴栗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而在《秋水》中,他又從認識主體的觀察高度和角度的不同來說明事物認識標準的相對性:“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這些思想的提出,讓莊子成為公認的相對論鼻祖。
在榮格的心中,東方人這一“富有哲理性的相對論”有著極不尋常的分量,他稱其“具有無比貢獻”,“非常欣慰而且歡迎它的出現”,“根本沒預料到它會對我們產生這么深遠的影響力”因為正是這些思想為榮格提供了批判西方非此即彼“錯誤觀念”的理論根據,提供了超越弗洛伊德理論之片面性的精神力量,讓他認識到“陰暗是光明的一部分,正和惡與善之關系的道理是一樣的,而且其逆亦真”。[3](325)
在此基礎上,榮格提出了著名的陰影理論,深刻指出了人類壓制陰影所帶來的嚴重后果,以及如何正確面對陰影的思路。榮格認為,陰影(5hadow)是心靈中遺傳下來的最陰暗的、隱秘的方面。它包括一個人違背道德的所有的體驗和心靈內部所有最受壓抑的或不發達的部分,是人格中的卑劣部分。所有個人與集體精神因素的總量,出于這些因素無法與被選擇的意識態度共相并存,因此這些因素在生活中便被拒絕表現出來,因而就接合到一種相對自治的帶有與相反傾向的“分裂人格”中去。“陰影將一切個人不愿承認的東西都加以人格化,但也往往將它自己直接或間接地強加在個人身上——例如,性格中的卑劣品質,和其他不相容的傾向。”
榮格認為,對待陰影這一人格中的卑劣部分不能簡單采取壓抑的方式,否則將會引起嚴重的后果。榮格學派的學者美國心理學家卡爾·S·霍爾曾引述榮格的評述,以說明這一問題:當我們心中的野獸受到壓抑時,“我們心靈中的野獸只會變得更加兇狠殘暴”;“毫無疑問,這就是為什么再沒有一種宗教象基督教一樣用無辜者鮮血的飛濺來褻瀆宗教的原因,這就是為什么世人從未目睹過比基督教國家之間的戰爭更為殘酷的戰爭的原因。”[2]霍爾認為,榮格上述看法的言下之意是說,由于基督教教義對于陰影具有強烈的抑制作用,“被壓抑的陰影向回撲過來,以肆虐的流血殺戮來吞噬種種民族。”這是基督教國家之間的戰爭更為殘酷的原因,甚至在可以從歷史中引證的無數其它的事件中,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繼二次大戰之后的種種戰爭亦可從這一角度來理解。[4](46?47)
榮格提出陰影理論是為了克服壓抑陰影所導致的惡果,為了以更為理智的態度來面對陰影,最終目的是“把人類的惡根找到”,“把世上的某些罪惡鏟除掉”,拯救現代人的靈魂。關于這一點,他在《現代靈魂的自我拯救》一書中有明確的表述,他說:
然而我們能夠在我們內心深處發覺到這么多的惡魔,幾乎可算是一大慰藉了。至少,我們可相信,我們終于把人類的惡根找到了。雖說一開始我們不免驚訝、失望,然而,由于這些都是我們內心的最好說明,我們算是多多少少已把它們控制在我們手中,因此,我們便可去糾正它們,或至少可有效地去撲滅它們。我們想作個假設,如果我們真能成功的話,我們一定能把世上的某些罪惡鏟除掉。[3](306)
榮格注意到陰影與光明的相互聯系以及陰影對于促進光明的出現所具有的積極作用。他說:“作為人類的一分子,在我體內的陰影可為我喚起了有利的光明,因此在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黑暗也同樣可帶來光明。”[3](314)因此,榮格認為,有效地撲滅人格中的陰影決非通過簡單地進行壓抑,而是要以寬容的態度來進行整合,這又促使榮格通向了老子兼容不苛的主張,他在為《太乙金華宗旨》注釋所作的評述中就指出了這一點。他說,“迫切需要整合的人格其結果究競如何?追求整合的必要性究竟多大?于是我們又踏上了這條東方人在遠古就已走過的道路。很顯然,中國人之所以發現了這條道路,是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迫使人性中的對立因素分離得太遠,以至于喪失了各因素間所有自覺的聯系”,中國人具有一種“包容各極的意識”,“認為是與否本是近親”。[1](81)顯然,這里所說的“包容各極”的思想正是老子“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的翻版;而“是與否本是近親”等思想亦來自老子關于善惡、美丑等對立面之辯證關系的論述。
道家的對立統一思想亦受到榮格學派心理學家的推崇和運用,將其作為“突破黑暗面”智慧。在榮格學派學者路格· 阿伯罕所著的《人生黑暗面》中,作者提到了“積極影像”這一心理訓練和治療方法與道家的聯系,他說:“創造積極影像所使用的最廣泛的方法,乃是將我們自己和道家的訓誨調和為一體,于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壞事將全部為好事所代替。”[5](175)該書作者還指出,如果我們對自己中的黑暗面懷有敵意的話,“它將會變得愈來愈令人難以忍受;反之,如果我們的態度是友善的——亦即了解到它的存在是自然的——則我們的將出現令人驚異的轉變。”[5](175)
也就是說,如果能以道家“包容各極”的辯證思維來善待自己或他人,就會對那個“陰影與光明”并存的個體有更多的寬容,從而以友善的態度面對“不善”,這不僅能夠感化不善者而實現“德善”,更能化解埋藏在自己心中的怨恨,淡忘不快,走出煩惱,讓生活充滿友愛和快樂的陽光。
老子的智慧給了榮格以啟迪,而從榮格的理論來詮釋老子思想,又讓人們更主動地吸收這些智慧來善待人的黑暗面,這就有助于糾正人們以往在這方面存在的簡單片面做法,從而有可能找到另外一條緩解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和矛盾的道路,并激發人的內在創造力和生命力,促進人格更為協調地發展。
運用對立統一原則,榮格進一步指出,在生命的進程中,沖突和對立是無處不在的事實。假如沖突能夠被承受,那么,它們就可以為創造性的成就提供動力,并且賦予人的行為以活力。反之則會導致人格的分裂,或者瀕臨干瘋狂的邊緣。因此,榮格努力尋找綜合那些對立力量的各種途徑,以圖推進對立的統一,實現和諧、平衡、統一的人格的完形。[4](51?52)在此基礎上,榮格提出了整合意識與潛意識、陰影與光明、阿尼瑪與阿尼瑪斯等一系列理論,在西方心理學領域內創建了獨樹一幟的宏大體系。
二、“元神”“識神”概念對榮格的影響
《太乙金華宗旨》中所說的“元神”、“識神”是道教內丹學兩個十分重要的基本概念,它們是一對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制約的生命要素。道教認為,“元神”是人的“本來面目”,來自無極之真性,無識無知;“識神”稟太極之元炁,有識有知。元神喜靜,識神喜動。識神動則情欲盛,情欲盛則耗散元精,進而耗散元神。人在出生以后,原本沒有意識但能主宰生命的“元神”逐漸被“識神”所侵擾,成為人的主宰,因此人難以長生。
結合自己以往的研究,“元神”、“識神”的概念啟迪榮格找到了在意識自我和集體潛意識過程中存在的聯結點,正式形成了他關于集體潛意識的理論。他將“元神”看成是“潛在于集體潛意識領域深處的本來自我”,將“識神”看成是“自我意識的活動”。他認為,人格結構分為意識和潛意識,潛意識又分為集體潛意識和個人潛意識兩個層次。意識即是經驗者自己能夠知曉的心理經驗,普通心理學對其有相當多的論述。潛意識是榮格心理學理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按照榮格《心理結構與狀態》一書所下的定義,潛意識的內涵包括:“所有我知道,但在當時并未思考的事情:所有我曾意識到,但現在卻已忘掉的事情;所有我的感覺已感知到,但并末被我的意識頭腦注意到的事情;所有我不是主動地、對其不加注意地去感受、思維、記憶、渴望和做的事情,所有將塑造我,并在某些時候會進入意識的未來的事情。”“個人潛意識”除了上述內容以外,“還包括那些或多或少具有全球性的對痛苦想法和感覺的諸多壓抑”,榮格關于個體潛意識的看法與弗洛伊德基本一致。他的獨到創建在于提出了集體潛意識的概念。榮格認為,集體潛意識并非來自個人的經驗、不是個人所習得,而是人類在歷史進化過程中積淀下來的、通過遺傳而先天存在的原始意象和本能,榮格之所以將其稱為“集體”的,是因為它并非由個體和或多或少有些特殊的內容所構成,而是“由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所構成,由那些習以為常地發生的事物所構成”。[2]
在為《太乙金華宗旨》注譯本所作的評述中,榮格進一步指出,潛意識的心理結構是超越人類所有文化和意識的共同基底,“集體潛意識的實質就是與所有種族差異無關的大腦結構全同性的心理表現”。[1](78)在自我(ego)形成之前,支配人的精神活動的主要是集體潛意識,人主要依靠本能、情感活動,潛意識決定意識。但隨著人生經驗的增多、自我的成長,人的活動漸為有意識。意識的形成和發展常常使人的精神逐漸擺脫潛意識的束縛。因此,意識過度發達的結果,卻招來了集體潛意識的報復,因而產生了精神疾病。
可見,忽略潛意識的存在這是現代人產生孤獨等心理問題的重要根源。榮格在《現代靈魂的自我拯救》一書中指出,“一位道道地地被我們稱為現代人者是孤獨的”,這是因為與集體潛意識日益疏離,每當他要向意識領域作更進一步之邁進時,他就和他原本要和大眾“神秘參與”——埋設在普通的中——的初衷離得愈來愈遠遠,“每當他要舉步向前時,其行動就等于強迫他離開那無遠弗屆的、原始的、包括全人類的”。[3](294?295)榮格認為,上述情況在西方人這里尤甚,因為西方人的精神是意識太過發達的精神,這種發達導致精神與原初狀態(即意識與集體潛意識)的分離,這種分離導致“精神失常”或“意識的連根拔起”。
而我們知道,在這方面道家道教有著獨特的方法,他們認識到,過度發達的理性意識和名利算計、概念邏輯、封建名教的束縛,往往使人們日益與本真之性相脫離,產生各種煩惱和痛苦,故強調要摒除后天知覺和意識,通過修煉心性以復歸至清、至潔、至靜的真心。老莊提出致虛守靜、心齋坐忘,《老子想爾注》要人們拋卻“計念思慮”“情欲思慮怒喜惡事”,司馬承楨《坐忘論》中概括出“收心”“簡事”“真觀”“泰定”等等七個階段,清代傅金銓《性天正鵠》告誡修煉者“施煉心養性之功,庶不以賊為子,錯認識神”……
眾多內丹家千言萬語的叮嚀囑咐,目的都在提醒修煉者自覺地調控心理,防止意識過分發達,清除頭腦中的私心雜念,實現“返本歸元”。從榮格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實際上是為集體潛意識的自然發展開辟道路。
榮格力圖通過意識與潛意識的融合,實現人格轉化,達到完整的、統一的新人格——自性。而他認為正是《太乙金華宗旨》將他“推到正確的方向上”,促使他找到了整合意識自我和集體潛意識的聯結點。何以如此呢?這就需要考察道教內丹學特別是《金華宗旨》的修煉思想,從中找出它和榮格這一思想的相通性。
從道學內丹修煉理論來看,榮格所說的集體潛意識這種所有人類都具有的“大腦結構全同性的心理”正是修煉所說的“本性”“真性”。道學認為,“道”是生發天地萬物包括人類的本源,人的真性與具有普遍意義的宇宙節律——“道”在本質上是同一的、相通的,心是性的載體,性由心生,當心處于無為清凈的狀態時,則顯現出“表里瑩徹……一塵不染”的本性。因此,通過煉心以求“明乎本心”乃是體認“至道”、展發本性的根本途徑。張伯端在《悟真篇·自序》中指出:“欲體至道,莫若明乎本心,心者,道之樞也。”
因此,道教內丹修煉的目標就是要現出真我、真性、本性,或稱之為“本命元神”。如,唐代高道成玄英就曾在《老子注》卷一中強調,修煉者就是要“復于真性,反于慧命”,這只有在守樸棄詐、排除后天意識干擾的狀態下才能實現。
因此內丹家主張通過修煉主張自覺地進行致虛守靜、坐忘心齋等活動以返歸本真之性,現出那個被后天意識所遮掩了的“真我”。這種放棄對于意識自我的執著以回歸與大道相合的本來真性的活動,其實類似于榮格所說的“原本由集體潛意識支配精神活動的狀態”,建立起“意識自我和集體潛意識的聯結點”。而且,這里所追求的“復于真性”并非真要回到人生初始之時,而是認識到意識過度發達的弊害因而自覺地通過修煉而超越意識自我的過程,是個體發展的更高階段,這與人生初始還未形成自我(ego)之前由集體潛意識支配精神活動、依靠本能和情感活動的狀況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是追求人性在更高層次上的返樸歸真,是通過修養之后所達到更高人生境界。關于這一點,《莊子·天地》中“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的論述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榮格的人格理論的最終目標是“個體化”,也就是發展集體潛意識,從自我過渡到自性“與我們最深處的、最后的、而且不可比較的太一相結合,實現個體化”。[2]我們看到,這一所謂“個體化”過程其實與《太乙金華宗旨》以及道教內丹所追求的“返本歸元”——從后天狀態返歸先天狀態也是非常相似的。返本歸元的目標就是要消除在人格中的潛意識與意識的對立,使得先天之氣在一身之內流行,以恢復元神的主宰,恢復人之本真存在狀態。《太乙金華宗旨金華·元神識神》章說:“惟元神真性,則超元會而上之,……然有元神在,即無極也。先天地生皆由此矣。學人但能守護元神,則超生在陰陽之外,不在三界之中,此惟見性方可,所謂本來面目也。”[6]
集體潛意識對人格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促進集體潛意識的發展,進而達到意識與潛意識的合一,實現自性呢?道教的心性修煉活動正是一個重要的方式。榮格看到了無為思想的心理治療意義,并將這一思想吸收到他的治療實踐中。以下我們就來討論這一問題。
三、 無為思想對榮格的啟示
榮格在心理治療實踐中提出了“無為藝術”,這是他將中世紀德國神秘主義者愛克哈特所說的“任物自行”與《太乙金華宗旨》所說的無為之道相結合而產生心理治療方法,他認為,這一鮮為人知的藝術乃是促使精神正常發展的關鍵。
榮格意識到西方文化中意識過度發展對人的精神心理的危害,他看到,與西方意識片面發展的情形不同,中國人善于平衡理智和情感這兩個對立方面,他說:“中國人對于生命體內部與生俱來的自我矛盾和兩極性一直有著清醒的認識。對立的兩方面永遠是彼此平衡的——這是高等文明的象征。”榮格毫不掩飾地批評說,西方文化中的片面性,盡管它提供了發展的動力,但是,“它仍然是末開化的標志。如今在西方發端的反抗理智祟尚情感或者崇尚直覺的這個反響,我認為是文明發展的一個標志,是意識對專橫的理智設定的過分狹窄之界限的突破。”
榮格希望采用道教的“自然無為”來抑制意識的過度發展,保持意識與集體潛意識的聯系,以保證精神的正常發展。他通過對《太乙金華宗旨》的研究和自己的實踐,發現“無為藝術”正是道教內丹修煉的體驗。在自然無為的狀態中,他畫下許多作為體道象征的曼荼羅。他所創建的由“意識自我”到“集體潛意識的深層世界”的道路——“積極想象法”,與道教內丹“回光返照”,“凝神入氣穴”等進入潛意識深層世界的方法在本質上多有相合。[7](76)
榮格進一步認為;人們如果要促成“自我”的解放,就必須遵循“無為”這種東方道家的處世態度。《太乙金華宗旨》的《天心》《回光返照》等多處皆強調無為的重要性,如“自然曰道,道無名相……丹訣總假有為而臻無為”,又如“惟無為,故不滯方所形象,惟無為而為,故不墮頑空死虛”等等。這也就是《太乙金華宗旨回光返照》中呂祖所說:“日用間,能刻刻隨事返照,不著一毫人我相,便是隨地回光,此第一妙用。清晨能遣盡諸緣,靜坐一、二時最妙。凡應事接物,只用返照法,便無一刻間斷。如此行之,三月兩月,天上諸真,必來印證已。”[6]
文中“不著一毫人我相”“遣盡諸緣”的“靜坐”方法,雖然揉入了佛教的語言,但其實質內容就是一種“無為藝術”,它與老莊“滌除玄鑒”“坐忘”“心齋”乃至道教內丹修煉的方法一脈相承,內丹修煉皆奉無為之旨。“無為”在內丹修煉中主要指毫不勉強、自然放松的調整身形的技術要求,也包含了清凈寡欲的心理狀態。如全真七子之一的馬丹陽在繼承發展祖師王重陽清凈修行原則的基礎上,將修煉工夫概括為“清凈無為”,他告誡門徒說:“道則簡而易行。但清凈無為。最上乘法也。……夫道。但清凈無為。逍遙自在。不染不著。此十二字若能咬嚼得破。便做個徹底道人。”[7]必須排遣物欲和各種私心雜念的干擾,不斷地修煉,增加定力,不為外物所動,才能保持虛靜的心理狀態,實現修煉的目標。這也正是《慧命經》中所說的:“務要綿綿,久久鍛煉,將此陰魔②化為陽光,則身心自然安樂,情欲自然不能攪動……如法鍛煉,用之得力,欲不用除而自除,心不用靜而自靜,所謂以道制心而心自道。”[8](222)這種通過修煉而獲得的“欲不用除而自除”“心不著跡”“我與聲色無干而聲色自與我無涉”的自在境界,正是榮格所推崇的。
榮格看到,《慧命經》《太乙金華宗旨》等道教丹書雖然將節制欲望作為修煉的基本要求,“這似乎與基督教的禁欲道德并不相距太遠”,但是,“如果認為它們闡述的是同樣的事,那可是大錯特錯了”。他們的方式“與基督教的禁欲主義道德不同”,因為這部書的背景是持續了數千年之久的古老文化,這種文化有機地建立在原始的本能之上,因而,在這種文化中,我們不會看到專斷的道德指令對本能的侵犯,而這種侵犯已經成為我們的一個特征標志了。由于這個原因,中國人根本不存在粗暴地壓抑本能的沖動,而這種沖動卻歇斯底里地膨脹且毒害我們的精神。與本能同在的人也能超脫本能,這種超脫與同在同樣是自然而然的。[1](117)榮格這里所說的“不會看到專斷的道德指令對本能的侵犯”“不存在粗暴地壓抑本能的沖動”“自然而然”等對待人性、對待自然欲望的態度,正是道家在自然無為宗旨支配下的心性修煉智慧。
榮格深刻體悟到《太乙金華宗旨》中的“無為藝術”對心理治療的意義。他寫道:“為了獲得自身的解放,這些人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就我所知,他們什么也沒有做(無為),而只是讓事情任其自然地發生,正如呂祖在本書令所傳授的那樣,如果一個人不放棄自己的俗務常事,光就依其自然的規律運轉。讓一切順其自然,無為而為,隨心所欲,在心靈方面,也一定要順其自然。”
榮格看到,這種無為而為的技術正是西方文化中所沒有的,“對我們來說,這的確是一種鮮為人知的技藝”。榮格看到,在意識過分發展的西方文化中,“意識總是與心靈的發展摻合在一起,吹毛求疵,好為人師,從未讓心靈在平靜的環境中質樸地發展。”而如果改變這種做法,以質樸無為的態度處事,“問題就會變得十分簡單”。[1](84)
榮格通過自己的心理治療實踐,從多方面印證了道教的“無為”原則對于保證精神正常發展的作用。因此,他治療的指導原則是個體化的自然過程,讓潛意識自發的精神在它渴求完善的本能、自發的沖動中實現意識與潛意識的調和。
榮格認為,治療家“必須遵從自然的指導”,治療師“不是治療的問題,而是發展潛伏在患者自身中的創造的可能性問題”。榮格觀察到:那些成功地使他們自己擺脫生活問題的纏擾,達到心理發展和整合的更高層次的患者,實質上什么也沒做,只是簡單地順其自然,讓該發生的事情發生。他們允許自己的潛意識在寂靜中與他們交談,他們耐心地傾聽它的信息,并給予它們最大和最認真的關注。而只有當這一過程不受外界控制、不受治療學家干預,自然產生作用時,才能最完滿地完成。在治療中,不要拘泥于先入之見和理論假設的影響,放棄一切方法和技巧。當允許這種心理過程平靜地發展時,潛意識豐富了意識,意識又照亮了潛意識,于是這兩個對立面的融合和結合,使認識增強、人格擴展。[9]
榮格運用自然無為的原則收到了明顯的療效。他在為衛禮賢所作的《太乙金華宗旨》的評述中,榮格記述了這樣的案例:一位經他治療而康復的病人寫信告訴他自己所經歷的重要轉變:“保持安靜,不壓抑什么,保持注意力,接受現實——按事物的本來面目接受它,不是按照我想要它成為的樣子接受它——由于達一切,我獲得了非凡的知識和非凡的能力,以前我從未想象得到。”對此,榮格十分認同,他強調:“如果我們想要獲得更高層次的意識以及文化,就必須要以這樣一種心態作為基礎。”[1](118)
榮格不僅以無為作為治療原則,更以自己的親證實驗,實踐著“無為藝術”,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榮格體現了“那種無為之為,也即中文之‘無為’”。這也意味著一種靈性的自發與再生。[10](196)
榮格試圖借鑒道家道教“自然無為”的思想,避免西方意識片面發展或某一方面過度成長所帶來的危害,對于現代中國人重新認識這一中華民族的心理保健智慧是有積極啟示意義的。自近代以來,在西方文化的沖擊和影響下,中國人對于理性的盲目崇拜和對非理性的粗暴排斥,是否也有可能在將來再現榮格曾指斥過的意識過度發達的弊病呢?我們不應忘記,理性和非理性、意識和潛意識皆是人類精神心理健康發展不可或缺的方面,我們既需要吸收西方的理性和科學精神,但也決不可對中國先賢的無為、直覺、頓悟等非理性智慧妄自菲薄。榮格對無為思想的評價和應用,對我們正確認識這一道學基本概念在心理治療方面的價值是有啟示的。
當然,作為西方現代心理學家,榮格對《太乙金華宗旨》《慧命經》以及道家道教的理解不可避免地會有誤解之處。同時,榮格對于“無為”這一概念的理解又是不可能十分到位的。如他在談及《太乙金華宗旨》的“無為藝術”時說:“為了獲得自身的解放,這些人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就我所知,他們什么也沒有做(無為),而只是讓事情任其自然地發生,正如呂祖在本書中所傳授的那樣……讓一切順其自然,無為而為,隨心所欲……”[1](84)榮格以“無為”來對治西方意識過分發達所引起的弊端取得了積極的效果,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這里將“無為”理解為“什么也沒有做(無為)”,卻又是失之于簡單、片面的。
在內丹修煉中,“無為”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它既指毫不勉強、自然放松的調整身形的技術要求,又指清凈寡欲、精神穩定的心理狀態,更是指修煉過程中運用火候③的基本原則,所謂“采藥于動與不動之中,行火候于無為之內”。[11]要求在采藥煉丹時要“勿忘勿助”,注意調節火候,達到心息相依,凝神定志,不假人力又不放任的程度。
在《太乙金華宗旨》中,“無為”也決非“什么也不做”。如,該書的《回光返照》中說:“惟無為,故不滯方所形象;惟無為而為,故不墮頑空死虛。”這段話十分清楚地表明,“無為”其實是一種特殊的“為”的方式,一方面,它要求行為主體在修煉中不執著、不刻意、順應自然;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落入“什么也不做”的“頑空死虛”,而是有所行動的“無為而為”。
實際上,榮格在實踐中也是將“無為”作為一種特有的行為方式來踐行的。正如榮格心理學專家戴維·羅森所說,榮格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體現了“那種無為之為,也即中文之‘無為’”。正是在這種特殊的修煉行為中,榮格的心靈中出現了“一種靈性的自發與再生”。[10](196)這就從實踐的層面證明了榮格原來對“無為”所作闡釋的局限性。我們當然沒有理由苛求榮格這位西方現代心理學家,但認識這些局限,這對于當代中國人厘清對道學的誤解并更準確地把握其豐富內涵也是不無啟示的。
三、簡短的結語
榮格在結合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礎上,吸收道學對立統一、自然無為等思想,開創了西方心理治療學的一片新天地;他在東方古老的內丹修煉與西方現代心理學之間搭起了融通互補的橋梁;而通過他的潛意識理論,亦有助于我們探討或解釋致虛守靜等修煉方法具有心理保健、人格發展等積極作用的內在機理,啟示我們自覺地應用內丹修煉而進入潛意識層面,調治現代人類的心理問題,開發人類未知的潛能。在這一系列探索中,我們也必將深化對中國哲學的特性及優長之處的認識,進一步開掘道學智慧的現代價值,促進中國哲學智慧走進生活世界,撫慰和滋潤當代中國人的心靈。
注釋:
①在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王宗昱的《榮格的道教研究》,景海峰的《試析容格評論<太乙金華宗旨>的意義》,臺灣學者劉固秋的《榮格與道教內丹之心理分析──個體化》等論文;美國戴維·羅森的《榮格之道:整合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等。而王宗昱先生在《榮格的道教研究》中就認為:“《太乙金華宗旨》對于榮格的理論建構并未增添多少磚瓦,而是使它的輪廓驀然清晰。”詳見《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②按《慧命經》作者的說法,陰魔,“即身中之陰氣”。見《慧命經 正道修煉直論》,徐兆仁主編的《東方修道文庫·伍柳法脈》第22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③內丹家將人體比作鼎爐,將真炁比作藥物原料,將意念、呼吸比作“火候”,進行烹煉。故“火候”實質是指意、神、氣等的運用。
[1]榮格,衛禮賢.金華養生秘旨與分析心理學[M].北京: 東方出版社,1993.
[2]榮格.榮格自傳[M].北京: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5.
[3]榮格.現代靈魂的自我拯救[M].北京: 工人出版社,1987.
[4]卡爾·S·霍爾.榮格心理學綱要[M].鄭州: 黃河文藝出版社,1987.
[5]路格·阿伯罕.人生黑暗面[M].伊犁: 伊犁人民出版社,1998.
[6]胡道靜,陳耀庭,段文桂,等.藏外道書·第10冊[M].成都: 巴蜀書社,1990.
[7]馬丹陽.真仙直指語錄·丹陽語錄[C]//道藏·正一部.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8]柳華陽.慧命經·正道修煉直論[C]//徐兆仁.東方修道文庫·伍柳法脈.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9]戴維·羅森.榮格之道: 整合之路[M].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10]白玉蟾.謝張紫陽書·雜著指玄篇·修真十書[C]//道藏要籍選刊·第三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