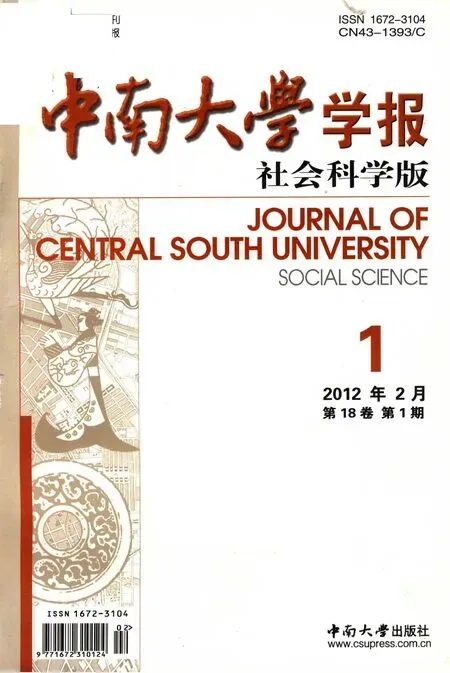基于“抗戰”“文學”視點的“抗戰文學”論析
劉江
(柳州鐵道職業技術學院科研處,廣西柳州,545007)
一
以“抗戰”眼光來看,學術界此前對于“抗戰文學”的認識并不明晰。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里,“抗戰文學”至今尚未具有特指的意義。有的人以時間為界,研究“抗日戰爭時期的文學”[1](1?204),這當然包括非抗戰內容的文學作品在內,實際上并非專門研究抗戰文學;有的人則從作品的內容出發,把五四之后至抗日戰爭結束期間與抗戰相關的作品統稱為“現代救亡文學”[2](337?387),時限上并不與“抗戰”相吻合;有的人又把目光對準“七·七”之后至新中國建國之前,稱之為“抗戰的民主的文學運動”,[3](129?200)這不但把許多非抗戰內容的作品,還把許多非抗戰時期產生的作品歸納其中;有的人卻又把“七·七”之前的作品,歸為“抗日救亡”作品,而把“七·七”事變之后的作品,稱為“為民族解放而歌的抗戰文藝”,和“在‘為工農兵服務’方向下的解放區作品”,以及“皖南事變以后的國統區文藝”,[4](437?649)這表現出并未確立真正的“抗戰文學”的概念。此外,網上又有人把建國后馮德英的《苦菜花》等,甚而當今以抗戰為題材的電影和小說,統歸為“抗戰文學”,這顯然是把具有特定寫作時限的“抗戰文學”,同歷史文學混淆起來;當然,還有人以八年抗戰為時限,收集此間抗戰題材的作品,稱之為“戰時文學”。[5]這最后一種似乎準確些,只是,這又忽略了“八年”之前的相關作品,把它們排斥在抗戰文學之外,又造成了對此間文學“抗戰”意義的輕視與忽視。
這些事實表明,在此前的研究中,學術界并未從“抗戰”的角度來審視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抗戰作品。同時也表現出,學界對于“抗戰文學”還缺乏明晰的認識。
當代美國批評家科林·馬加比 1999年在埃克塞特大學所作的題為《為批評辯護——為紀念加拉斯·羅伯茨及托尼·坦納而作》的講演中說過:“建立一種研究,一般說來首先是要在對特殊的用詞的構成的分析之中,找到它最基本的合理性。”[6]筆者認為這種認識是科學的。因此,抗戰文學應當具有以下“質”的規定性才能體現出“最基本的合理性”:一是“抗戰”的內容;二是“抗戰”的時限;三是寫作和發表的時間。從內容上看,“抗戰”的內容應該包括前方、后方,部隊、民間,正面和側面對日寇的斗爭,不論以何種方式,只要指向抗日就可歸屬。從時限上看,作為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是從“七·七”開始的,但民間的反抗卻是在“九·一八”前后就出現了。蕭紅于 1935年出版的小說《生死場》敘述的就是“九·一八”事變前夕東北淪陷后“這片荒蕪的土地上淪于奴隸地位的被剝削、被壓迫、被輾軋,……的人民,每年、每月、每日,每時、每刻……在生與死兩條界限上輾轉著,掙扎著,……或者悄然地死去,或者是浴血斗爭著……的現實和故事”[7]。從寫作、發表時間看,應該是從“九·一八”到1945年抗戰結束期間所創作、發表的作品。如為之后所寫,那就只能算作歷史題材的作品了。所以,以“抗戰”眼光看來,所謂“抗戰文學”,就應該是指稱上世紀“九·一八”前后至 1945年抗戰結束期間創作的,直接反映各界民眾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所作的斗爭,或者描寫與抗戰相關的生活,以抗日為思想指向的一切文學作品。“抗戰文學”有特定的寫作背景(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后,對中國人民的血腥屠殺和肆意欺凌),有特定的創作思維(文藝服務于抗日救亡),有特定的作品題材(包括各種方式和各個側面的對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斗爭),有特定的思想情感(對侵略者和漢奸的仇恨,對有礙于抗戰的一切行為的憤慨和反對,以及對積極抗戰者的贊頌)。正因這樣的作品具有特定的含義,所以它在文學史上具有特定的意義,占有特殊的地位。
二
以“抗戰文學”的眼光來看,“與抗戰無關”和“服務于抗戰”,都是對“抗戰”和“文學”的割裂,實際上兩者完全可以統一起來。在抗戰文學的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武漢失陷后開展的文學“與抗戰無關”還是“為抗戰服務”的論爭。梁實秋首先在重慶自己主編的《中央日報》“平民”副刊上發表《編者的話》,批評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他們的作品是“空洞的‘抗戰八股’”[8](9)。此后的1931年1月,沈從文又連續發表文章,稱文學只有“遠離了‘宣傳空氣”,“遠離了那些戰爭的浪漫情緒”,“才是社會真正的進步”[8](9)。而侍桁則在1940年的《文藝月刊》上,稱作家們“對于他們的過度的抗戰服務的熱情有加以深刻檢討的必要”[8](10)。他們的說法立刻遭到了羅蓀、陳白塵、宋之的、張天翼等人的反駁。而后來的文學史家也都一致譴責和批判梁實秋、沈從文們。當然,這一譴責自有其道理,在國難當頭的時刻,高喊“與抗戰無關”完全是錯誤的,是文人們喪失社會責任感和愛國心的表現。但是當我們站在今天的觀察點上回眸這一歷史事件時,便又會發現,這次論爭其實質并非不同政治立場的搏擊,而是不同眼光對文學的不同要求的交鋒。羅蓀等人是站在政治的即抗戰的立場說話,而梁實秋們則是站在文學的立場要求文學。前者強調文學的政治意識形態性,強調宣傳教育功能;而后者則主要著眼于文學的藝術質量,著眼于文學的主體性,他們“與抗戰無關”的主張,主要是面對當時為抗戰服務的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狀況而發的。現在看來,兩者都有片面性:強調要服務于抗戰的人,忽視了文學的主體性,這一主張發展到40年代,形成了文學的“工具論”和“武器論”;強調“與抗戰無關”的人,則忽視了或者說不承認文學的政治意識形態性,拋棄了文學應有的思想正義的靈魂,也無視政治所具有的文化性。實際上,無論是“服務論”者還是“無關論”者,都是把“抗戰”(政治)和“文學”割裂開來。
而我們完全可以把兩者統一在一起。這是因為:一方面,“抗戰”的思想內容和“文學”的主體性,都是“抗戰文學”所應該具備的品質,兩者的結合才是它的應有之義。而所謂“抗戰的思想內容”是廣泛的,應該包括前方與后方、軍隊與民間的正面與側面的斗爭。其感情,也應該包括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對漢奸的忿憤,對國民黨不抵抗的政策和行為的譴責,對積極抗戰者的贊頌,對一些軟弱、忍耐的民眾的怨艾和嗟嘆……等等。這樣,就能給“文學”以許多選擇的空間和發揮的余地,以致不與文學的主體性、多樣性發生矛盾。而所謂“文學的主體性”,也就應該體現在作家對于上述不同內容的選擇上,同時也體現在對創作方法、表現手法,以及語言、體式和作家個人風格等方面的選擇上。這樣,就不但能解決怎樣為抗戰服務的問題,而且也能實現文學的多樣化。事實證明,這種要求是能夠做到的。另一方面,“抗戰”也并非一般的階級、民族之間的斗爭,而是人道與反人道、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抗戰的“政治”本身就蘊涵著文化的內涵。反映抗戰,完全可以由政治走向文化,從而體現出豐厚的文化意蘊。西方許多描寫戰爭的作品,例如俄羅斯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不就是既是政治的同時也是文化的文學嗎?
三
以“文學”的眼光看: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什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前的作品表現的多為悲憤之情,而慷慨激昂、振奮人心的作品多問世于《講話》之后?為什么許多作品總是把抗日和揭露國民黨的丑惡結合起來?為什么典型形象都是反面人物?
我國的抗戰文學是豐富多彩的。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在1942年毛澤東發表《講話》之前,正面描寫抗日斗爭的作品并不多,而且,表達的多為悲憤之情。
先看“九·一八”至“七·七”之前的作品。小說方面,蕭紅的《生死場》“以纖細而又帶有幾分粗獷的筆觸,在描寫了‘九·一八’事變前東北鄉間生活的沉滯和閉塞”的同時,“又寫出了這些‘愚夫愚婦’們的民族和階級意識的最初覺醒”[2](364),魯迅稱其寫出了“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9],作品的感情是悲憤的。與此同時,舒群的短篇《沒有祖國的孩子》、中篇《老兵》,黑丁的短篇《回家》,端木蕻良的短篇集《憎恨》,羅烽的中篇《歸來》、短篇集《呼蘭河邊》,白朗的短篇《輪下》,“這些作品真實地記錄了東北人民的苦痛和抗爭,也滲透了作者自己的悲憤的感情”[1](368)。此外還有夏衍寫于1936年的報告文學《包身工》,真實地反映了上海日本紗廠女工的非人遭遇,憤怒控訴了日本資本家和中國封建勢力互相勾結、共同壓榨中國人民的血腥罪行。戲劇方面,1931年由陳鯉庭執筆、集體創作的獨幕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敘述了“九·一八”之后,一對流離失所以賣唱為生的父女,從東北淪陷區逃亡來到內地,演出時因饑餓難忍,女兒暈倒在地,后來父女敘說了東北淪陷后他們的悲慘境遇,激起觀眾對侵略者的無比憤慨。此外,還有田漢的短劇《戰友》和《回春之曲》,它們寫的是1932年上海“‘一·二八’停戰、反動政府簽訂賣國條約后愛國青年們的悲憤心情和抗戰要求”[1](383)。此外,還有夏衍創作于1936年冬的多幕歷史劇《秋瑾傳》,在贊揚民主革命者秋瑾的同時,無情地鞭撻了媚外殘內的漢奸走狗。詩歌方面,田間寫于“七·七”之前的詩集《中國牧歌》和《中國農村的故事》,表現的是“侵略戰爭給祖國農村、尤其是東北大地帶來了苦難”[8](43)。這些作品都呈現出民間生活的情狀,內中既有我國人民遭受的種種苦難,也有他們的掙扎和反抗,所以都突出地表達了悲憤的情懷。總的說來,上述作品所寫的都是情緒上、心理上的“抗戰”,也可以說是作品從側面表現了抗戰的主題。
期間,正面描寫抗日斗爭而且較為引人注意的只有一部作品,即蕭軍的《八月的鄉村》(1934),記敘的是一支東北抗日游擊隊,在和日偽激烈的斗爭中,經受了各種困難和挫折不斷成長壯大的過程。“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10],其情調,依然是悲憤交加的。
再看看“七·七”之后的作品。就戲劇而論,夏衍寫于1940年的四幕劇《心防》,表現的是上海淪陷后,進步的文化工作者為堅守這個城市‘五百萬’中國人心里的防線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斗爭。其情感是深沉而悲憤的。其寫于1942年的五幕劇《法西斯細菌》,“主要通過細菌學家俞實夫由不問政治到‘再出發’的曲折的覺醒過程,嚴正批評了超階級、超政治的科學至上主義,揭露了法西斯主義與人類一切進步事物為敵的反動本質和國民黨統治的黑暗腐敗”[8](84?85),其感情同樣是憤慨而又悲酸的。丁西林寫于 1939年的四幕劇《等太太回來的時候》,寫的是留學回來的梁治和高中學生梁玉斷然與做漢奸的父親決裂,而年事已高的母親,也知道一個人“最要緊的是要有氣節”,于是毅然和子女一起離開上海前往內地,其感情當然也是憤慨而悲壯的。沈浮的三幕劇《重慶二十四小時》,描寫的是一個從東北流浪到重慶的女青年,識破了邪惡勢力的圈套,毅然投入抗日的戲劇工作,作品在對邪惡勢力表達憎恨的同時,依然流露出悲傷的情懷。此外,郭沫若自1941年起,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寫出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六部歷史劇,“反對侵略、反對賣國投降、反對專制暴政、反對屈從變節,主張愛國、愛民,主張團結御侮,主張堅持節操,是這些劇本從不同角度所表現的共同主題”[8](96)。歐陽予倩自1937年始,先后改編成多個劇種的《桃花扇》,阿英也先后寫出了南明史劇《碧血花》《海國英雄》《楊娥傳》等,這些作品都大力宣傳民族氣節,而內中又都流露出悲憤的情調。
小說方面,丘東平在抗戰初年所寫的短篇《暴風雨的一天》,“用側面烘托的手法,塑造了狂風暴雨中堅守崗位的少年游擊隊員形象”,反映出“戰爭初期人民奮起抗戰、慷慨悲歌的感人情景”[8](110?111)。吳組緗的長篇小說《鴨嘴嶗》(《山洪》),表現的是抗戰初期皖南農民堅持中國人要“爭口氣”的想法,投入民族解放斗爭的歷程。丁玲1940年底寫成1941年6月發表的短篇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敘述的是抗日根據地農村姑娘被日寇侮辱后堅持送情報的故事。還有姚雪垠的短篇《差半車麥秸》,講的是一個綽號叫“差半車麥秸”的農民的故事:他抱著“鬼子不打走,莊稼做不成”的思想參加了游擊隊,在一次戰斗中身負重傷,卻仍然掙扎著說要“留下來”,不愿退下火線。這些作品盡管內容不同,人物的精神各異,但作品的情調或多或少帶有“悲”的成分。
相反,1942年《講話》之后的作品情況卻大不相同。邵子南的小說《地雷陣》,敘述晉察冀民兵開展地雷戰把日本侵略者打得焦頭爛額的故事。楊朔的短篇小說《月黑夜》,敘述一位革命老人自愿冒著生命危險,前去接送八路軍小分隊執行任務,途中被敵人抓住殺害的故事。華山的《雞毛信》,敘述兒童團長海娃,在一次反‘掃蕩’中,為了送一封雞毛信(表示十萬火急),一路上和敵人巧妙周旋,終于克服困難和險阻,把情報送到八路軍手里的故事。管樺的《雨來沒有死》,敘述一次日寇的突襲中,一個活潑的小孩獨自一人機智地掩護區交通員,在敵人的誘騙和威逼下逃走的故事。這些作品雖然寫了犧牲,寫了艱難困苦,但是因為革命的亢奮情懷壓倒了悲傷,所以作品表達的不再是悲憤,而代之以激憤之情。還有孫犁的短篇小說集《蘆花蕩》《荷花淀》等,“具體生動地描寫了抗日根據地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艱苦的抗日戰爭。”[8](333)它們更是洋溢著樂觀的情調,散發出浪漫主義的氣息。
于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擺在了我們的面前:為什么《講話》之前抗戰文學表達的是悲憤,而之后表現的卻是激憤、奮發和樂觀呢?
在筆者看來,其原因不外乎三個方面:一是在“七·七”全民抗戰之前,抗戰的形勢嚴峻,作家們往往對侵略者的行徑雖然憤慨但卻無力;二是“七·七”后的抗戰初期,作家們對抗日的前途信心不足,因而悲憤難免;三是到了《講話》發表之時,抗日戰爭已經從防守階段到了相持階段,抗戰的形勢比以前推進了一步,這給我國人民包括文藝工作者樹立了抗戰勝利的信心。而在《講話》中,毛澤東強調文藝工作者“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11](53)。怎么變化,怎么改造呢?毛澤東提出: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11](79)。與此同時,他還一再特別要求文藝工作者“要站在黨的立場上”[11](49),而作品的感情、情緒就是立場的重要表現。在這種情勢下,作品表達激奮、向上的情懷是很自然的。從這一意義上說,毛澤東的《講話》無疑對我國的抗戰文學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說,《講話》是抗戰文學思想情感發展的一個轉折點。當然,這轉變主要表現在抗日根據地的創作上,因為表達激憤、樂觀情懷的作品,主要就是產生于抗日根據地的作品。
以上是第一種情況。第二種情況是:這些反映抗日斗爭的作品,許多都是把描寫抗日斗爭和揭露國民黨官僚、土豪劣紳的丑惡行徑結合起來,甚至是以抗戰為背景,主要寫國民黨的反革命活動。其中最有名的是張天翼寫于1938年的《華威先生》和沙汀發表于1940年的《在其香居茶館里》。前者揭露國民黨官僚對抗日戰爭包而不辦、表面積極實際壓制的消極態度;后者則展現抗戰時期,國民黨鄉紳借抓壯丁之名徇私舞弊、敲詐勒索的惡行。此外,艾蕪的長篇小說《故鄉》寫抗戰初期畢業于上海某大學的青年知識分子余峻廷回到家鄉,本想大干一番抗日的宣傳事業,可是當他接觸了當地的許多官紳之后,便感到無可奈何,感嘆“我們的家鄉,真是黑暗,黑暗,第三個黑暗”。沙汀的長篇小說《淘金記》,寫地主劣紳們因為爭發國難財而起了內訌。宋之的寫于1940年的五幕劇《霧重慶》,同樣是“揭露和抨擊國民黨腐敗政治”的[8](88)。陳白塵寫于1939年的多幕劇《亂世男女》,也“描寫了抗戰乍起由南京逃到‘大后方’的一群都市‘沉渣’的形形色色丑態”[8](90),這“沉渣”就是指國民黨的官僚和黨棍。而茅盾寫于1941年孟夏的長篇小說《腐蝕》,以皖南事變前后‘陪都’重慶為背景,暴露了國民黨法西斯特務統治的罪惡和他們反共反人民、投降賣國的本質,被稱為“抗戰期間以現實為題材暴露國民黨統治區政治黑暗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2](381)。即使是寫于“七·七”之前,正面描寫抗日斗爭的蕭軍的《八月的鄉村》,也是一方面寫出“東北人民反抗日寇侵略的堅強意志和斗爭精神”,而另一方面,也同時“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不抵抗政策”[3](216)。
為什么會如此?
一是出于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期間突出的惡劣表現,即使是在“七·七”之后,蔣介石、國民黨雖然和共產黨簽訂了抗戰協議,卻又從1939年起,連續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這使許許多多的進步文藝工作者看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反革命本性,認清了這些人對于抗戰事業的嚴重危害,從而決心揭露他們。沙汀說過:“我們的抗戰,在其本質上,無疑的是一個民族自身的改造運動,它的最終目的,是在創立一個適合人民居住的國家,若是本身不求進步,那不僅將失掉戰爭的最根本的意義,便單就把敵人從我們的國土上趕出去一事來說,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將一切“新的舊的痼疾,一切阻礙抗戰,阻礙改革的不良現象指明出來”[8](133)。二是出于共產黨的號召,毛澤東在《講話》之前的1941年5月就說:國民黨“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這些事實,也在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證明了。極端地復雜的中國政治,要求我們的同志深刻地給以注意。”[12]正是這一號召,鼓動著進步的文藝工作者注意觀察和表現國民黨官僚的真面目。三是國統區的作家對于國民黨的內幕有足夠的了解,比如茅盾,就有論者指出,他“所選的題材(指《腐蝕》——筆者)……是十分熟悉的”。[13](177)這又表明,他們具有揭露國民黨官紳丑行的條件。
當我們檢視抗戰文學時,還會發現一種情況,就是在這些為數眾多的抗戰作品中,所刻畫的具有時代特色的豐滿的人物形象不多,真正能夠站立在文學史上的人物形象,大概只有華威先生(張天翼《華威先生》)和邢么吵吵(沙汀《在其香居茶館里》)。湊巧,兩者都是國民黨身份的人物形象,學術界評論前者是“抗戰初期一個文化官僚的典型形象”[2](425)。筆者認為,后者是一個不顧國難、借公行私,橫行霸道,痞氣十足的國民黨土豪的典型。前者具有官場的文化氣息,后者則具有鄉間的污濁味。這兩個人物形象,不同于文學史上包括《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儒林外史》《老殘游記》《官場現形記》等古典文學中所有的官紳形象,也不同于魯迅筆下的魯四老爺,他們是具有抗戰時代特點的、具有高度概括力的類型性人物。
為什么典型形象都是反面形象?一是因為作家們囿于生活。不說《講話》之前,就是《講話》之后的作家,到抗戰前線的人也不多,所以對于正面的抗日人物還不夠熟悉,很難寫出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形象,特別是英雄形象。二是因為他們對于國民黨包括上下層人物都特別地注意審察,對于這些人的行為、心理,都有比較深入的了解,這為他們塑造反面典型提供了可能,張天翼和沙汀都是如此。如沙汀說: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為了抗戰,而在實質上,它們的作用卻不過是一種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人們你爭我奪的飯碗,所以人們自然也就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獰笑著,呻吟著,制造著悲劇”。[2](427)因而,遵從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家,也就自然地把他們描繪出來。三是因為他們厭惡這些人物,應該說,抗戰時期的文藝工作者,并不都是持有無產階級立場的,但是進步作家都具有愛國之心,他們是有意把國民黨官紳塑造成反面形象,借以鞭笞國民黨的。正如有的學者評論《在其香居茶館里》時所說:“作品的鋒芒”是“指向兵役問題上弊政產生的根源——國民黨政府。”[8](135)
四
再以“文學”的眼光來看我國“抗戰文學”的特色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發生在上世紀30、40年代的我國抗日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 分,而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則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戰爭。遺憾的是,由于資料所限,我們難得讀到國外戰時所寫的反映這次大戰的作品。我們容易看到的,只是為數不多的前蘇聯作品如法捷耶夫的小說《青年近衛軍》(1945)等,其他都是戰后多年創作的,應視為歷史文學的小說和電影,如前蘇聯的《莫斯科保衛戰》《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南斯拉夫的《橋》,以及美國的兩部曲小說《戰爭風云》和《戰爭與回憶》等。但是可以肯定,我們有值得驕傲的地方,那就是:我們的抗日戰爭,既是全民的軍事抗戰,也是全民的文化(文學)抗戰。據統計,1939年以前,僅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所創作和演出的比較成功的戲劇,就有 30種以上,包括獨幕劇、活報劇、小歌劇等多種形式[8](22),同時,“抗戰初期,人們紛紛以寫詩來表達自己的感情,服務于抗日斗爭,其中大量的是青年作者,也有長期未寫詩或從未寫過詩的作家”。[8](23?24)更有民間的快板、民歌、說唱和短劇,可謂形式多樣,色彩紛呈。無論數量還是質量,就戰時創作而言,在世界范圍內都可以說是名列前茅。
再認真體味一下,我們還可以發現,這些作品具有一些鮮明的特點。
首先是突出的文化性。從文學史收錄的作品看,都是一方面極力展示侵略者非人道的殘暴行為,展示我國人民所受的沉重災難;另一方面極力展示我國人民反抗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從“尋求正義”的角度,把抗日戰爭表現為正義對邪惡的斗爭,做到了政治性與文化性的統一,也就是從政治走向了文化,是政治與文學的結合。同時,許多作品,如沙汀、孫犁、蕭紅、田間、老舍、張天翼等人的小說和詩,都滲入了濃烈的地域意識和歷史內涵。從中,我們完全可以體味到沙汀作品的“天府味”,孫犁作品的“荷花淀味”,田間作品的“燕趙味”,蕭紅作品的“黑土味”,老舍作品的“北京味”,張天翼作品中國式的“官僚味”……。這些,既表現出我國抗戰文學的藝術品位,更表現出它的文化精神。學者楊義先生說:“抗戰文學的文化精神史的價值高于它的文化藝術史的價值”,[14]這話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其次是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這些作品都遵從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去表現生活,無論是侵略者的囂張和兇殘,我國人民所受的苦難,還是我國民眾的反抗行為,特別是作品所表現的我國人民先是悲憤后是激昂的情感,都體現出現實主義的特色。而理想化的色彩,只有在《講話》發表之后創作的某些工農兵文學作品中才有所體現,如《呂梁英雄傳》和《新兒女英雄傳》)以及孫犁的《荷花淀》等。當然,即使它們也只是在生活的基礎上,表現得更理想一些,或者注重意境的營造,散發出某些浪漫的氣息而已。因此所有這些作品都給人以真實感和親切感。在這些作品中,現實主義既是一種創作方法,又是一種創作精神。
最后是色澤分明的人物描寫。我國的文學傳統是,在人物描寫方面表現為所采用的主要是以《水滸傳》《三國演義》《紅樓夢》所代表的色調模糊的手法,比如李逵、林沖、宋江,曹操、劉備、諸葛亮,還有林黛玉、賈寶玉等人物,都不是單純的“好”或“壞”的角色,而是優缺相雜的復合型人物。然而自清末《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譴責小說出現之后,創作界便慢慢風行另一種人物描寫的色彩分明的手法,即對人物思想品行的描寫,進行好、壞的鮮明對比。這種手法,在五四新文學之后、抗戰文學之前,革命文學就廣泛采用了。抗戰文學繼承了這一手法。這些作品中所寫的人物,如《雨來沒有死》中的雨來,《雞毛信》中的海娃,還有《等太太回來的時候》中那同漢奸父親決裂的兩位青年,甚至《差半車麥秸》中那位綽號叫“差半車麥秸”的農民……,都只是寫出了他們的正面的思想品質(只有《四世同堂》例外),即使是那些愚昧的人們,當他們覺醒之后,他們的表現也都完全是正面的。相反,那些國民黨官僚、黨棍和鄉紳、土豪,無論是華威先生,還是邢么吵吵,還有那聯保主任方治國,或者是艾蕪《故鄉》中的“反動腐朽的社會勢力”《等太太回家的時候》中的漢奸,都完完全全是壞人。正因如此,抗戰文學的人物顯現出色澤分明的面貌。
站在今天的觀察點上,看看幾十年前我國的抗戰文學,我們感到自豪,就其總體而言而不是就某些作品而言,它多了這之前文學中少有的濃烈的民族正氣,少了這之后工農兵文學強烈的工具性,給人以更多的親切感和文學味(大概只有郭沫若的歷史劇的文學氣息少些,《呂梁英雄傳》等政治功利性強些)。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這一時期出現了大批有才華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呈現出鮮明的特點和風格,諸如田間的激越情懷,艾青的深沉情調,蕭紅的散漫渾濁之風,張天翼的尖酸刻薄之氣,孫犁的浪漫主義氣息,艾蕪的凝重風韻,沙汀的辛辣格調,老舍的古樸京味……
抗戰文學是我國重要的文學類別。即使不從政治角度看,而單從“文學”著眼,它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是重要的。就它的波及面和影響力來說,遠遠超過了我國歷史上任何一種反映“抗戰”的文學(如南宋和清末的抗戰作品)。如果說抗日戰爭是我國歷史上取得最大勝利的反侵略戰爭,那么抗戰文學就是我國文學史上最輝煌的反侵略文學。筆者認為孟繁華教授說的“我們現在還沒有一種能夠稱得上經典的反映抗日戰爭的小說”[13]這話不夠準確。這是因為他把側面反映抗日戰爭的《華威先生》和《在其香居茶館里》排除在“反映抗日戰爭的小說”之外,其立論的根據只是戰后創作的正面描寫抗日戰爭的《烈火金剛》《鐵道游擊隊》和《平原槍聲》等作品,與本文所主張的“抗戰文學”的含義不符。其實這兩篇小說完全稱得上是抗戰文學的經典作品。
[1]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下)[M].北京: 作家出版社,1956.
[2]馮光廉, 劉增人.中國新文學發展史[M].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4.
[3]馮光廉, 等.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程(上)[M].濟南: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4.
[4]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M].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
[5]張燕.山西抗戰文學優秀作品首次結集出版[EB/OL].山西新聞網, 2010-09-27.
[6][美]科林·馬加比.為批評辯護——為紀念加拉斯·羅伯茨及托尼.坦納而作[C]// 王逢振.2002年度西方文論選.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3: 156.
[7]肖軍.〈生死場〉重版前記[C]// 蕭紅.生死場.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0: 1.
[8]唐弢, 嚴家炎.中國現代文學史(三)[M].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0.
[9]魯迅.蕭紅作〈生死場〉序[C]// 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422
[10]魯迅.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C]// 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296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藝論集[M].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2.
[1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7:740
[13]孫中田.論茅盾的生活與創作[M].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
[14]作者不詳.抗戰文學作品: 對人性的挖掘還欠深度[N].中國讀書報, 2005-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