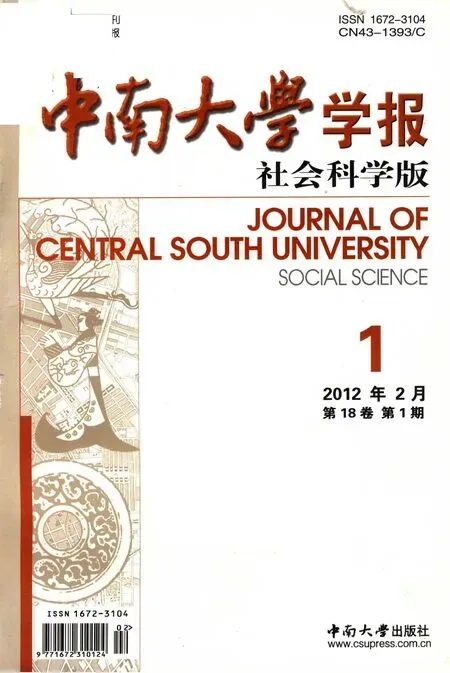英國漢學家杜德橋與《西游記》研究
許浩然
(南京大學文學院,江蘇南京,210093)
杜德橋(Glen Dudbridge, 1938?),英國劍橋大學博士,曾任劍橋大學、牛津大學講座教授,兼任牛津大學中國學術研究所所長,入選英國學術院(British Academy)院士,當代著名漢學家,現已榮休。《西游記》研究是杜德橋重要的學術方向之一。1964年他在《新亞學報》上用中文發表《<西游記>祖本考的再商榷》;1967年以論文《<西游記>前身考及其早期版本》(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dents and Early versions)取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1969年在《泰東》(Asia Major)上發表《百回本<西游記>及其早期版本》(The Hundred-chapter Hsi-yu Chi and Its Early Versions),該文為其博士論文的一部分,被臺灣學界翻譯;1970年其專著《十六世紀中國小說<西游記>前身考》(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被列入“劍橋中華文史 叢 刊 ”(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出自其博士論文的另一部分;1988年杜氏又有論文《<西游記>的猴子與最近十年的成果》(The Hsi-yu Chi Monkey and the Fruits of the Last Ten Years)發表于《漢學研究》(Chinese Studies)。杜德橋對《西游記》的版本演變、章回分合、形成源流、人物原型均有深入探討,這些探討并非封閉自足的體系,而是充滿了對研究同行觀點的反思、商榷與借鑒,同時他的觀點也被同行反饋和討論,這種互動促進了《西游記》學術的進程,值得國內學界重視,今特撰文述評如下。
一、《西游記》版本考證及明刻陽本的發現
學界對《西游記》版本的考證,一直都在爭論百回本、陽本、朱本的相互關系。百回本《西游記》現存最早者是明代金陵唐氏世德堂本。陽本(亦稱楊本)原名《三藏出生全傳》,題“齊云陽志和(亦作楊致和)編”,四十則,不稱回,后被收入《四游記》,稱《西游記傳》,一直翻刻不綴。朱本原名《唐三藏西游釋厄傳》,題“羊城沖懷朱鼎臣編輯”,十卷,分則不稱回,朱本最早存本為明萬歷初年本,曾在日本村口書店出售,后此本被北平圖書館收購,后又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制有縮影微卷。陽本與朱本相似,可以視為同一系統的本子,這兩個本子較之百回本明顯簡略。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者已對以上三種本子的關系作出討論。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認為陽本為百回本的一種祖本。胡適《跋<四游記>本的<西游記傳>》予以反駁,認為陽本是妄人割裂百回本而成。孫楷第于村口書店、鄭振鐸于北平圖書館親見朱本最早存本,分別在《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西游記的演化》中作出分析,在觀點上都傾向于胡適之說,鄭振鐸更是列出版本源流圖示,明示了朱、陽二本從百回本刪削而來。魯迅后來也依鄭著訂正了己說。[1](166?173)
時至60年代,陽本、朱本與百回本的關系問題又起爭議。澳大利亞籍華裔學者柳存仁獲睹美國國會圖書館朱本縮影微卷,于1963年、1964年在《新亞學報》和《通報》(T’oung Pao)上分別用中、英文發表論文《<四游記>的明刻本》[2](323-375)、《<西游記>的祖本》(The Prototypes of “Monkey(Hsi Yu Chi)”)[3](55?71)試圖推翻前說,論證朱本、陽本為早,百回本后出,對以上兩本都有承襲。在這一背景下,杜德橋撰成《<西游記>祖本考的再商榷》[4](497?519)、《百回本<西游記>及其早期版本》[5](337?400)兩文與之商榷。杜氏同意孫楷第、鄭振鐸的觀點,并用更為嚴謹的論證來鞏固它。他提出:“省略之處不足為證,可能是裝訂疏忽造成的漏洞更不能用做證據。”這是說文本間單純的詳略比較對于考證版本前后沒有作用,既可以說版本源流是由繁刪簡,又可以說是由簡增繁。他認為“表面上流暢、完整的散文敘述中極不通的地方才能用為檢驗的有效標準”。[5](352)其意是要由文本內在的文義矛盾來考索刪削的痕跡。在這一標準之下,他用很長的篇幅詳舉數例論證陽、朱二本的刪削之處。可以說杜、柳二氏的商榷文章將《西游記》版本考證推向了更為精密的層次。
杜德橋在版本研究中更有一個突出的貢獻,就是他和漢學前輩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于60年代在牛津大學圖書館發現了明刻陽本,該本原是一位英國爵士在1679年以前捐贈給牛津的。此前中外學者考證《西游記》版本,所據陽本最早者是胡適所藏的嘉慶坊本,接觸不到該本的學者只能利用近現代的排印本。[6](702)牛津本的發現無疑使學界能夠更為清晰地了解陽本的原貌。杜氏將這一發現的成果公布在《百回本<西游記>及其早期版本》中,他這樣描述:“新鍥三藏出身全傳,共四卷,正文分為四十則,不稱‘回’。半頁十行,行十九字。上圖下文,圖兩邊有題詞;首頁插圖旁題:‘彭氏’。首卷前題‘齊云陽至和編,天水趙毓真校’,緊接前題有一題記:‘芝潭朱蒼嶺梓行’。”[5](348)他考證芝潭是建寧府建陽縣,認為朱蒼嶺極有可能是當地從事專業出版的朱氏家族的一分子。[5](385?386)而就“其版式看來,乃彼時典型之閩刻。”
1988年柳存仁新撰《<西游記>簡本陽本、朱本之先后及簡繁本之先后》發表于《漢學研究》,根據以上牛津本對《西游記》版本又作了重新考證,雖然具體觀點仍與杜氏不同,但是他極其稱道兩位牛津學者的發現,說:“牛津大學龍彼得和杜德橋兩位先生發現在牛津收藏的明刻本,是研究中國小說史的一件大事,特別是研究《西游記》的早期版本的里程碑。他們的發現的功績是應該大書特書的。在他們沒有發現這一部重要的刻本之前,從中國老輩的學者們數起直到現在的我們,幾十年間,大家不免走了不少冤枉路。”[6](702)
二、從版本考證到文學批評:《西游記》第九回問題
杜德橋《西游記》的版本研究還涉及“第九回問題”:通行本《西游記》第九回“陳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兒復仇報本”(簡稱“陳光蕊故事”),明代所有百回本皆不載,而最早載于明刻朱本,它是否為小說內容原有,一直是學界爭論的話題。杜德橋考證朱本后于百回本,故傾向于認為“陳光蕊故事”并非小說原有,是后人所加。該問題原屬版本考證范疇,然而杜氏的研究另多出一段評述文字:“‘陳光蕊故事’無論就結構及戲劇性來講,與整部小說風格并不諧洽。組成前十二回的各節故事中,只有此‘陳光蕊故事’對整個故事情節的推展沒有貢獻。此節故事自成一體,強調倫理孝道。性喜詼諧,落拓不羈的百回本西游記作者,若寫了這節故事來寓托這么嚴肅的主題,實在令人難以想象。”[5](374?375)該段評述的性質超出了版本考證而涉及到文學的評論。這一點被他敏銳的歐美同行們發覺,使他們受到啟發,反向思考,撰寫文章與其商榷,從敘事結構、母題意義、改編技巧等文學的角度挖掘“陳光蕊故事”對于整部《西游記》的重要性。于是在歐美漢學界里,《西游記》第九回的去取由版本問題一變而成為文學批評的話題。
1975年,芝加哥大學《西游記》研究名家余國藩在《亞洲研究學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發表《<西游記>的敘事結構與第九回問題》(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Problem of Chapter Nine in The“Hsi-Yu Chi”)首先與杜氏商榷。余文對“陳光蕊故事”中兩個情節的論述特別值得注意。其一是玄奘剛一出生就被棄置江上,蒙金山寺長老救養,皈依佛門的情節。他認為小說至六十七回有一詩句“幸遇金山脫本骸”是對該情節回應,暗示著玄奘以出家作為救贖,即“脫本骸”的象征。至九十八回師徒即將功德圓滿之時,又出現了“脫本骸”情節:玄奘以無底船過凌云渡時,真正捐棄了本骸,得到了救贖。從江流出家到凌云渡修成正果,余氏指出《西游記》里有一個貫穿全篇的河流母題:“河流不但是毀滅的象征,也是再生的征兆。毋庸置疑,玄奘心里的河流經驗乃包括生前的災難、出世后的遺棄,以及最后的獲救等等。”[7](227)其二是:玄奘母親拋繡球選婿的情節,小說敘至天竺國故事時,玄奘觀覽國風,追念此事,且更被繡球打中,被逼與公主成親,余氏認為這正是“陳光蕊故事的回應與嘲諷”。[7](228)基于以上論述,余氏認為杜氏所下的“‘陳光蕊故事’對整個故事情節的推展沒有貢獻”的判斷是不能成立的。
1979年,威斯康辛大學學者阿爾薩斯·嚴(Alsace Yen)在《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Reviews)上發表《中國小說的技巧:<西游記>里的改編——以第九回為中心》(A Technique of Chinese Fiction: Adaptation in the “Hsi-yu chi” with Focus on Chapter Nine)作了進一步的探討。嚴分析了“陳光蕊故事”的模式:“事業有成的父親/兒子——惡人試圖謀殺父親——父親復生:惡人受懲:家庭團聚”。嚴認為這種模式在中國小說戲劇中十分流行,他例舉元代張國賓《相國寺公孫合汗衫雜劇》也有極其相似的模式。[8](206-212)嚴發現《西游記》中,這種模式其實出現了多次,以后章回里的烏雞國故事與天竺國故事也呈現了相同的模式:“烏雞國國王/王子:惡人試圖謀殺國王:國王復生:惡人受懲:家庭團聚”以及“天竺國王/公主:邪惡妖精試圖謀殺公主(妖精用風將公主運走):公主歸來:妖精受懲:家庭團聚”。嚴認為這種模式的重復“似乎暗示著《西游記》作者在寫作技法上有意識地接受了流行傳統中一種固定的形式”。而運用這種固定的形式來寫不同的故事正可以體現《西游記》作者一種文學改編的技巧。[8](201)
三、《西游記》前身考與“帕里—洛德口頭理論”
杜德橋著作《十六世紀中國小說<西游記>前身考》以相當篇幅梳理了業已被發現的十六世紀小說《西游記》形成以前的“西游記”文本、圖像材料:《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劉克莊《釋老六言十首(其四)》、泉州開元寺南宋西塔猴形神將圖及“龍太子”圖、永樂大典本“魏征夢斬涇河龍”平話殘文、朝鮮崔士珍《樸通事諺解》以及一些“西游記”戲劇和寶卷等。[9](25?100)這些材料已為學界知悉,無需詳述。值得注意的是他對于材料的態度。杜氏在其書導論中引述到西方口頭文學研究領域著名的“帕里—洛德口頭理論”(the Parry-Lord Oral Theory),其為美國學者米爾曼·帕里(Milman Parry)與其學生阿爾伯特·貝茨·洛德(Albert B.Lord)共同提出,反映在洛德1960年出版的著作《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之中。該理論通過對南斯拉夫史詩歌手的田野考察研究了口頭文學傳統:口頭傳統遠離書寫傳統,歌手吸取同行優點、根據聽眾需要、或是即興發揮,在表演中隨時對作品進行再創造,史詩在他們口里的傳承具有流動性和靈活性。[10](17?39)如果歌手利用固定文本來識記歌詞,被書寫傳統限定的形式和措辭所束縛,就意味著口頭文學的消亡。[10](197?198)根據這個理論,杜氏認為中國白話文學的發展亦包括口頭傳統和書寫傳統,只是后來隨著印刷業的繁榮,固定劃一的文本抹去了口頭傳承的特色,逐漸使其消失,例如固定的話本就抹去了口頭文學傳統中說話藝術的多變性。杜氏指出,在某些白話故事形成的源流中,有許許多多的人物曾通過書面或口頭方式發揮了作用,但當我們追溯這個源流的時候,“采用書寫和印刷方式之人輕易地在我們心中占據不公平的優勢:他們有力地壟斷了我們使用的材料。”[9](10?11)而源流中那些口頭傳承者則大多湮滅不聞。杜氏認為《西游記》的形成過程就有這樣的情況,研究者在考察其書前身源流的時候,資料的獲取只能依靠手寫或印刷的書面材料,但必須認識到口頭文學對于《西游記》的重要,承認書面文獻的局限。[9](11)
這種態度使得杜德橋對學界有關孫悟空原型的種種推測深表懷疑。20世紀70年代以前中國、日本、歐美學界對孫悟空原型作出種種推測:有《補江總白猿記》中的白猿、雜劇《二郎神鎖齊天大圣》《龍濟山野猿聽經》的猴精、神話中水怪無支奇、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的哈奴曼。[9](114?164)杜氏認為這些推測僅在書面文獻之間作平行的對比,闡述一些所謂的相似性來作出推論,難令人信服。這些推測缺乏口頭材料來描述從原型演變到現狀的過程,書面文獻較之口頭文學的多樣性遠為簡省,很可能會忽略、歪曲人物原型的演變過程中某些重要的元素。杜氏說:“口頭媒介有其自身的規律。有了足夠的第一手材料,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下,我們或許就能追蹤不同口頭故事之間主題的傳承;在一個更廣的范圍,我們或許還能追蹤某些神話從一個文明到另一個文明的傳播。但是我們只能使用與口頭材料截然不同的書面小說……特定故事基本要素的形式就會顯得簡單概括得多,這在更后的書面版本中還可能常顯出意義的扭曲失衡。所有這些就是說,僅有書面劇本和小說文本構成我們現在的《西游記》以及與之類似傳說的材料體,我們可能不能指望開展一項有效的人物原型研究,如孫悟空原型研究。”[9](154)
杜德橋以上觀點在歐美學界引起過質疑,1971年8 月、1972 年 8 月,夏志清[11](887?888)、余國藩[12](90?94)有該書書評發表,認為“帕里—洛德理論”產生的背景與中國口頭文學環境之間的差異實在太大,該理論是基于對許多徹底與文本世界隔離的南斯拉夫歌手所作的調查而提出的,這些歌手很多不認字,但是中國口頭文學藝人普遍識字斷文,而且與書面文獻緊密相連。兩篇書評發表間隔的1972年2月,杜氏在《亞洲研究學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發表過一封公開信,承認中國口頭文學藝人的文化程度,他解釋說:“我并非如書評宣稱將‘與書寫傳統的脫離’歸于‘口頭藝人’,而是歸于‘口頭傳播’。” 他認為“帕里—洛德理論”可以為中國口頭文學研究者帶來如此一種“中肯的警示”,即強調口頭、書寫文學是兩種彼此脫離的傳承,而“真正的職業口頭藝人,不管識字與否,即使有著名的書面版本存在,也會保持有自己的藝術獨立以及超越文本束縛的自由。”[13](351)平心而論,在“帕里—洛德理論”提出剛剛十年之后,杜德橋就將它引入中國文學研究,揭示口頭文學在考察故事源流時的重要性,指出傳統學術在依靠實物、書面文獻方面的局限性,此一作用是積極的。不過如何恰切使用該西方理論去處理中國文化的問題,尚需仔細琢磨,杜氏書中使用“帕里—洛德理論”有過于機械之處,如果沒有后來的解釋,確實會讓人產生如夏、余二先生的感覺。
四、孫悟空原型研究的反思與新解
上文述及杜德橋《前身考》質疑當時孫悟空原型的推測,他后來的文章《<西游記>的猴子與最近十年的成果》(以下簡稱《成果》)又繼續質疑了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后期學界對此問題作出的新推測,主要是日本學者磯部彰及其贊同者提出的孫悟空形象源于福建神猴信仰的說法。[14](264?265)與《前身考》不同的是,在《成果》中,杜氏不再將質疑統歸為口頭材料的缺乏,而是作出了更為縝密的思考,他思考這些推測基于證據所運用的學術方法。他認為《西游記》原型研究里存在兩種證據:本證(primary evidence)和旁證(circumstantial evidence)。“本證緩慢并少量地積累;旁證迅速并大量地積累。本證安上了一條不靈活、不舒坦、不自在的規則;旁證則創造出熱情、朦朧而愉快的光輝。本證牢牢并永久地保持在討論的中心;旁證隨著個人觀點和偏好的閃現而來去自由。最終,對于我們問題的解答只能依靠本證;而直到那時,我們還將十年又十年繼續用我們頭腦里新生出來的旁證去填充新的著作。”[14](255)他指出唐僧原型研究依據的是本證:玄奘前去印度學習取經的史實,所有研究者都是圍繞它展開論述,這就是所謂的“規則”,這樣的研究雖然單調,但最終有明確的定論。孫悟空的原型研究則不同,因為缺乏一個公認的證據,學者各自提出自己的旁證:從《西游記》以外文獻中找出一個或幾個猴子形象,利用外證與孫悟空對比,發揮聯想,論證原型,這樣的研究方法雖然興致勃勃,新見迭出,但難得定論。
杜德橋試圖以新方法對孫悟空原型問題作出解釋。在《前身考》里,他曾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在《西游記》里“為什么一個民間流行的宗教偶像(指玄奘)要有奇怪的動物隨從,并且為什么猴子在中間特別杰出。”當時他自己對這一問題并不能深入解答,只是籠統地歸為“喜劇元素”。[9](166)在《成果》里,他參考了有關臺灣、香港、新加坡及其他東南亞地方傳統社區里宗教風俗的實地考察材料,發現在這些社區里的葬禮儀式中,當靈柩被抬去墓地時,人們往往扮作各種動物為其開道,此俗自古就有。人們相信逝者的脆弱的靈魂在西去極樂世界的道路上是兇險多難的,途中需要動物神保護驅魔——這是以上儀式的主題。而《西游記》里易被傷害的玄奘西去求取正果的路上正是由動物隨從相伴,與以上儀式主題完美對應,杜氏認為這一主題很可能就是小說的隱喻意義。那么為什么猴子在其中特別杰出?他的解釋是《西游記》中有孫悟空偷盜仙桃的情節,仙桃在中國文化中是長生的象征,它也是逝者前往極樂世界的護身符,逝者如想通過一個動物神得到它,那么猴子無疑是最有用的。這就是杜德橋給出的孫悟空原型分析,當然這也非定論,杜氏亦承認自己也運用了旁證:宗教風俗現象的考察。但與以前研究者思路不同,他已不再尋找《西游記》以外文獻中的猴子形象來與孫悟空作類比,而是挖掘故事內部所隱寓的意義,并論述猴子對于此意義的重要性,按他自己話就是“故事內部的鑒定”。[14](271?274)
杜德橋有關孫悟空原型研究的反思與新解具有學術史眼光,我們不妨將之與余英時名文《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所論的大觀園原型研究相比較。余氏認為紅學考據派在“自傳說”典范的影響下,利用小說以外文獻材料考證大觀園在現實中的地點問題,但是始終難以避免“南北混雜的嚴重矛盾現象”,這是該派學術上的危機。要超越這一危機,必須建立新典范,其方法是將“研究的重心放在《紅樓夢》這部小說的創造意圖和內在結構的有機關系上”,從文學的構思考慮大觀園的產生。[15](150?153)這種新典范的方法與杜氏的觀點相通,杜氏同樣認為從外證的考據永遠無法獲得孫悟空最終確鑿的原型,應該另謀出路,試圖通過分析文本內容結構探索小說隱寓意義,進而再證明猴子對這一意義的重要性。從歐美學界來看,他們的研究成果與杜德橋的此種主張有一定相契之處。例如余國藩致力于探討《西游記》宗教哲學寓意,認為小說中蘊含著儒釋道三教的“修心”觀念,而孫悟空形象的設定和中國習語“心猿”一詞有相當的關聯。[7](272?274)余氏的具體觀點雖和杜德橋相差頗大,但他們二人從小說內部的寓意來探索人物原型的研究思路卻是相同的。
[1]竺洪波.四百年〈西游記〉學術史[M].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6.
[2]柳存仁.〈四游記〉的明刻本[J].新亞學報, 1963, (2): 323?375.
[3]LIU Ts’un-yan.The prototypes of “Monkey (Hsi Yu Chi)” [J].T’oung Pao, 1964, (51): 55?71.
[4]杜德橋.〈西游記〉祖本考的再商榷[J].新亞學報, 1964(2):497?519.
[5]杜德橋, 蘇正隆, 譯.百回本〈西游記〉及其早期版本[C]//中國文學論著譯叢.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1985.
[6]柳存仁.〈西游記〉簡本陽本, 朱本之先后及簡繁本之先后[C]//和風堂新文集.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7.
[7]余國藩.李奭學譯.〈西游記〉的敘事結構與第九回問題[C]//〈紅樓夢〉, 〈西游記〉與其他: 余國藩論學文選.北京: 三聯書店, 2006.
[8]ALSACE Y.A technique of Chinese fiction: Adaptation in the“Hsi-yu chi” with focus on Chapter Nine [J].Chinese Literature: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79, (1): 206?212.
[9]GLEN D.The Hsi-yu chi: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10]阿爾伯特·貝茨·洛得.尹虎彬, 譯.故事的歌手[M].北京: 中華書局, 2004.
[11]HSIA C T.Book review: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71, (30): 887?888.
[12]ANTHONY C Y.Hsi-yu Chi and the tradition [J].History of Religious, 1972, (12): 90?94.
[13]GLEN D.Communications [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72, (31): 351.
[14]GLEN D.The Hsi-yu Chi Monkey and the Fruits of the Last Ten Years [C]// Books, Tales and Vernacular Culture: Selected Papers on China.Leiden·Boston: Brill, 2005.
[15]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C]//余英時文集·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下)[M].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