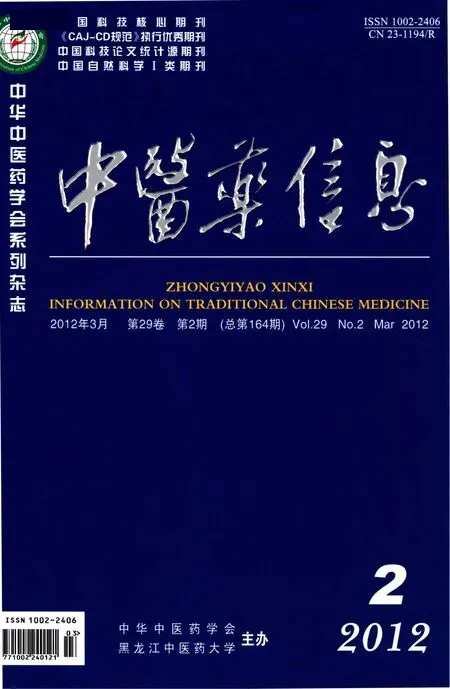易水學派薛己從體質靈活論治內科咳嗽
劉桂榮,李成文
(1.山東中醫藥大學,山東 濟南 250355;2.河南中醫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8)
咳嗽是一種常見病、多發病,是由外感或內傷因素導致的肺失宣肅,肺氣上逆,沖擊氣道,發出咳聲或伴咯痰為臨床特征的一種病證。中醫論治咳嗽有較大優勢,但至今仍多仁智之見,實則源于對其病因病機的認識不同。易水學派著名醫家薛己治療咳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其發病有深刻而透徹的研究,其發病觀及對內科咳嗽的論治經驗對臨床有重要意義。
1 論咳嗽首重體質
患者體質的不同,往往決定其對某些邪氣的易感性及產生病癥類型的傾向性。因此,認清患者的體質特點有助于分析其發病規律,為診斷和治療疾病提供依據。
薛氏論治咳嗽,首重患者的體質,并以此作為選擇治法和方藥的依據。《內經》云“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薛氏對此頗有體會,咳嗽患者多有正氣虛弱這一基礎,或偏于陰虛,或偏于陽虛,或偏于氣虛,或偏于血虛,影響臟腑功能,致臟腑失調,尤其脾胃升降失調,內而產生痰濕,外而招致邪氣,影響肺氣的宣肅,發為咳嗽,并有偏熱偏寒之殊,正如《素問·宣明五氣》所說:“五氣所病……肺為咳,”以及《素問·咳論》所說:“五臟六腑皆令人咳,非獨肺也。”因此臨證治病必須結合患者平素體質而定。
薛氏經過長期研究認為,素稟虛弱,或因飲食起居不調,房事不節,或長期病困,均可導致患者體質虛弱,表現出或偏于陰虛,或偏于陽虛;或偏于脾虛,或偏于腎虛,或偏于脾肺兩虛,或足三陰虛;或偏于痰濕等常見的咳嗽病癥特點。這也正是薛氏辨治的重要依據。
2 辨機體陰陽之偏施治
2.1 足三陰虛
2.1.1 陰虛轉為陽虛之體
原案:太守錢東墟,先患肩疽。屬足三陰虛火不歸源,用壯水之主以制陽光而愈。余曰:瘡疾雖愈,當屏去侍女,恐相火一動,其精暗流,金水復竭,必致變癥。后果喘嗽痰出如涌,面目赤色,小便淋瀝。又誤認為外感風寒,用麻黃湯表散,汗出不止。迎余視之,其脈已脫,惟太沖未絕。余謂脾虛不能攝涎,腎虛不能生水,肺虛不能攝氣,水泛為痰,虛寒之癥也。辭以難治,勉以益火之源以消陰翳而愈。繼后勞傷神思,外邪乘之,仍汗出亡陽以致不起[1]。(《薛立齋醫學全書·薛案辨疏》)
分析:該患者以房事過多,形成足三陰虛,火不歸源之體,后發為肩疽,故薛氏用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的方法治之而愈,并給患者提出警告:應屏去侍女以節欲,以防生變。不過,病人未聽勸告,致精氣虛衰,而發為喘、嗽、痰癥,卻誤認為外感風寒而用辛溫發表,汗出不止,以致陽隨津脫,變為“脾虛不能攝涎,腎虛不能生水,肺虛不能攝氣,水泛為痰”之虛寒癥,由于病重,薛氏勉強以“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之法治療,當然,由于病機分析絲絲入扣,藥對病證,幸而獲愈。然而,患者仍不慎加調養,復受外邪,終至亡陽而歿。
2.1.2 足三陰虛寒之體
原案:州守王用之先因肚腹膨脹,飲食少思,服二陳、枳實之類,小便不利,大便不實,咳痰腹脹;用淡滲破氣之劑,手足俱冷。此足三陰虛寒之癥也。用金匱腎氣丸,不月而康(《內科摘要·卷下》)。
分析:從本患者腹脹、納呆,服用二陳、枳實之類,出現小便不利,大便不實,咳嗽吐痰,腹脹;又服用淡滲破氣之劑,手足俱冷諸癥,可知,患者原屬肺、脾、腎氣俱虛之體,誤用破氣淡滲之品,致使足三陰氣虛加重而為虛寒,故治以金匱腎氣丸而康。
由上述兩例患者之體質狀況可知,薛氏所重視的“足三陰虛”,并非單純“陰虛”證,還包括相當一部分“陽虛”之虛寒證。我們從薛氏的辨證分析可以領悟到,準確把握病機是施治的關鍵,而且,病人的體質是可變的,治療方法就不可一成不變。
2.2 素體陰虛
2.2.1 陰虛咳嗽誤治傷陽
原案:司廳陳國華素陰虛,患咳嗽,以自知醫,用發表化痰之劑,不應,用清熱化痰等藥,其癥愈甚。余曰:此脾肺虛也,不信,用牛黃清心丸,更加胸腹作脹,飲食少思,足三陰虛癥悉見。朝用六君、桔梗、升麻、麥門、五味,補脾土以生肺金;八味丸,補命門火以生脾土,諸癥漸愈。經云:不能治其虛,安問其余?此脾土虛不能生肺金而金病,復用前藥而反瀉其火,吾不得而知也(《內科摘要·卷上》)。
分析:患者素體陰虛,發為咳嗽,誤用發表化痰之劑損傷脾氣,又用清熱化痰等藥戕伐肺氣,致使病情加重。薛氏做出脾肺虛弱的診斷,患者不信,反用牛黃清心丸,致使病情進一步加重,病變復雜。薛氏診為足三陰陽氣虛,采用朝夕補法,即朝用補脾土以生肺金,夕用補命門火以生脾土之法,當然,病人畢竟本屬陰虛之體,故而用藥亦兼顧肺陰以免有偏,終獲痊愈。
2.2.2 陰虛咳嗽誤治傷陰
原案:中書鮑希伏素陰虛,患咳嗽,服清氣化痰丸及二陳、芩、連之類,痰益甚,用四物、黃柏、知母、玄參之類,腹脹咽啞,右關脈浮弦,左尺脈洪大。余曰:脾土既不能生肺金,陰火又從而克之,當滋化源。朝用補中益氣加山茱萸、麥門冬、五味子,夕用六味地黃加五味子,三月余,喜其慎疾得愈(《內科摘要·卷上》)。
分析:清氣化痰丸及二陳、芩、連之類主治痰熱內結之證,以之治療陰虛咳嗽,則徒損脾氣、傷肺陰;又用四物、知、柏、玄參,養陰不足而重傷脾氣,是以陰火上克,而見諸脈癥。因此,薛氏朝用補中益氣加山茱、麥門、五味,夕用六味地黃加五味子,益脾氣、滋肺陰,經三月余而愈。
上兩例患者均是陰虛體質,但因咳嗽誤治用藥不同,致使病癥變化結果不一,薛氏辨證準確,既重體質,又能據證用藥,故而皆能取得滿意療效。由此可見薛氏具有靈活的辨證思想。
3 辨臟腑之盛衰施治
3.1 脾腎虧損誤治致咳
原案:一儒者失于調養,飲食難化,胸膈不利。或用行氣消導藥,咳嗽喘促,服行氣化痰藥,肚腹漸脹;服行氣分利藥,睡臥不能,兩足浮腫,小便不利,大便不實,脈浮大按之微細,兩寸皆短。此脾腎虧損,朝用補中益氣加姜、附;夕用金匱腎氣加骨脂、肉果,各數劑,諸癥漸愈;再佐以八味丸,兩月乃能步履;卻服補中(指補中益氣湯)、八味,半載而康(《內科摘要·卷下》)。
分析:本患者由于日常失于調養,造成脾腎虛弱之體,以致于飲食難化,胸膈不利。醫者不審病機,誤以為飲食積滯,而用行氣消導藥,反致氣虛之咳嗽喘促;醫者不察,給服行氣化痰藥,重傷脾氣而無以運化,出現肚腹漸脹;可惜,醫者執迷不悟,反予行氣分利藥,不僅無益于運行氣機,反由脾虛導致腎虧,水濕留滯,出現諸脈癥。薛氏明確辨證為脾腎虧損,于是朝用補中益氣加姜、附,夕用金匱腎氣加骨脂、肉果,各數劑,諸癥漸愈。為徹底糾正患者已造成的脾腎虧損體質,薛氏繼續給予八味丸,服藥兩月乃能步履;再以補中益氣湯、八味丸配合治療,經半載而康復。
3.2 脾肺虧損
3.2.1 脾氣虛弱遇勞咳嗽
原案:地官李北川每勞咳嗽,余用補中益氣湯即愈。一日復作,自用參蘇飲益甚,更服人參敗毒散,項強口噤,腰背反張。余曰:此誤汗亡津液而變痓矣。仍以前湯加附子一錢,四劑而痊(《內科摘要·卷上》)。
分析:本例患者素體脾虛,故而勞累即咳,薛氏用補中益氣湯就可治愈。然而,又有一次遇勞復發,病人自作主張服用參蘇飲,致使病情加重,以為發散力不夠,繼用人參敗毒散發散,損傷津液,而見項強口噤,腰背反張諸癥。故而薛氏辨為誤汗亡津液之痓癥,然患者究竟屬于脾虛之體,于是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一錢,使陽旺而陰生,僅四劑而痊。
3.2.2 脾肺虛而兼外邪
原案:金憲阮君聘咳嗽面白,鼻流清涕,此脾肺虛而兼外邪,用補中益氣加茯苓、半夏、五味治之而愈,又用六君、芍、歸之類而安(《內科摘要·卷上》)。
分析:此例患者面白,知其肺氣虛寒,脾為肺之母,故有脾虛;鼻流清涕,知其外感寒邪。是以薛氏診為脾肺虛而兼外邪,本宜用健脾補肺,散寒祛邪之法,然薛氏只用補虛之法,處以補中益氣湯補益脾胃,加茯苓、半夏健脾化痰,加五味子斂肺止咳,咳嗽諸癥消失。但因患者脾虛,氣血不足,故又投六君子湯益氣健脾,加川芎、當歸之類調養氣血。可見,薛氏治病,更重視“治人”。
3.2.3 脾肺俱傷,痰郁于中
原案:一婦人不得于姑,患咳,胸膈不利,飲食無味,此脾肺俱傷,痰郁于中,先用歸脾湯加梔子、川芎、貝母、桔梗,諸癥漸愈,后以六君加芍、歸、桔梗,間服痊愈(《內科摘要·卷上》)。
分析:本案患者雖然病因情志不遂而發,但由于遷延日久,脾肺俱傷,氣化失職,致使痰郁于中為主要病機,故以健脾益氣為主要治法,兼顧養血疏肝,先用歸脾湯加梔子、川芎、貝母、桔梗,咳嗽諸癥消失;患者究屬脾虛肝郁之體,故以六君加芍、歸、桔梗,間服痊愈。
3.2.4 脾肺陽虛寒痰咳嗽
原案:侍御譚希曾咳嗽吐痰,手足時冷。余以為脾肺虛寒,用補中益氣加炮姜而愈(《內科摘要·卷上》)。
分析:譚姓患者素體脾肺陽虛,不能達于四末,故手足時冷;陽虛不化水濕,侵襲于肺,則咳嗽吐痰。因脾為肺之母,故薛氏以補中益氣加炮姜治之而獲愈。
3.2.5 脾肺熱邪上逆而咳
原案:職坊王用之喘嗽作渴,面赤鼻干,余以為脾肺有熱,用二陳加芩、連、梔子、桔梗、麥門而愈(《內科摘要·卷上》)。
分析:王姓患者當屬脾虛有痰、肺虛有熱之體,故為病可見喘嗽作渴,面赤鼻干,此與外感熱邪、或寒邪化熱所致咳嗽不同,故以二陳加芩、連、山梔、桔梗、麥門冬治之而愈。可見薛氏為善于辨析病人體質而靈活遣藥者。
3.3 脾虛
3.3.1 脾虛失運痰嗽氣喘
原案:儒者張克明咳嗽,用二陳、芩、連、枳殼,胸滿氣喘,侵晨吐痰;加蘇子,杏仁,口出痰涎,口干作渴。余曰:侵晨吐痰,脾虛不能消化飲食;胸滿氣喘,脾虛不能生肺金;涎沫自出,脾虛不能收攝;口干作渴,脾虛不能生津液。遂用六君加炮姜、肉果溫補脾胃,更用八味丸以補土母而愈(《內科摘要·卷上》)。
分析:本里病案,薛氏已做了詳細分析,患者之吐痰、氣喘、口渴,悉由脾虛所致,而痰濕之成,津液之不化,則是脾虛不能溫運所致,故應本著“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之法,用六君加炮姜、肉果溫補脾胃;薛氏更追究病人脾虛之源,從調整病人體質入手,用八味丸以補土母,終獲痊愈。
3.3.2 脾虛生痰肺虛陰火而咳
原案:一婦人咳嗽,早間吐痰甚多,夜間喘急不寐,余謂早間多痰,乃脾虛飲食所化;夜間喘急,乃肺虛陰火上沖。遂用補中益氣加麥門冬、五味子而愈(《內科摘要·卷上》)。
分析:從薛氏對此例患者病情及治療思路的剖析可知,病人當屬脾虛痰濕、肺虛陰火之體質,故用補中益氣加麥門冬、五味子而治愈。
3.4 火不生土
原案:表弟婦咳嗽發熱,嘔吐痰涎,日夜約五六碗,喘咳不寧,胸躁渴,飲食不進,崩血如涌,此命門火衰,脾土虛寒,用八味丸及附子理中湯加減治之而愈(《內科摘要·卷上》)。
分析:此例患者之表現:發熱、胸躁渴、崩血如涌,頗似熱證;然而,由嘔吐痰涎,日夜約五六碗之多,飲食不進,知是脾虛已重,運化無力;進而推知類似熱證的表現,確是陽虛外浮之象,其根本在于命門火衰,無以燠土,故而用八味丸及附子理中湯加減治之而愈。由此可知,薛氏不愧為行家里手。
3.5 肝火血虛
原案:一婦人患咳嗽,脅痛發熱,日晡益甚,用加味逍遙散、熟地治之而愈。年余,因怒氣勞役,前癥仍作,又太陽痛或寒熱往來,或咳嗽遺尿,皆屬肝火血虛,陰挺痿痹,用前散及地黃丸,月余而瘥(《內科摘要·卷上》)。
分析:從本案的治療經過可知,患者屬肝火血虛之體,故初發病時用加味逍遙散、熟地治之而愈。一年多以后,又因怒氣勞役,導致前癥復發,由于患者固有之體質,容易造成腎精不足,故又見遺尿,陰挺痿痹等癥,因而,薛氏在前述治療方藥基礎上,配合應用六味地黃丸,治療月余而愈。由此可知,薛氏診療疾病之靈巧,絕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輩所能望其項背的。
[1] 盛維忠.薛立齋醫學全[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9: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