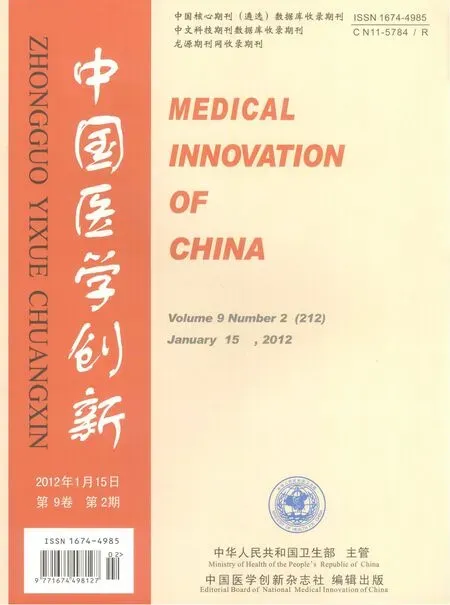功能性三尖瓣反流研究進展
梁麗明 陳同
功能性三尖瓣反流研究進展
梁麗明 陳同
三尖瓣反流(tricuspid regurgitation,TR)按發生機制分為器質性三尖瓣反流(organic tricuspid regurgitation,OTR)和功能性三尖瓣反流(functional tricuspid regurgitation,FTR)。FTR發生的原因、FTR與左心瓣膜病的關系、外科手術指征、手術方式的選擇及手術效果評價都還存在不同的觀點。本文就FTR的發病機理、診斷進展、外科手術時機及方案選擇的新觀念做一綜述。
三尖瓣反流; 功能性三尖瓣反流; 三尖瓣成形
FTR是造成TR最常見的原因,多數FTR繼發于左心瓣膜疾病,有研究表明30%的FTR與左心疾病有關,左心瓣膜手術同時對FTR的干預與術后遠期生存率和死亡率直接相關。近年來FTR越來越受到外科醫生的重視,成為外科領域研究的焦點。
1 功能性三尖瓣反流形成的原因
1.1 風濕活動的進展 左心瓣膜置換或成形術只糾正了瓣膜的病理改變,并沒有阻止風濕活動的進展。Dreyfus等[1]報道風濕性病變在二尖瓣置換術后遠期出現TR的患者中占11%,國內一組報道顯示風濕病進展約占遠期三尖瓣反流患者的25%。Antunes等[2]指出三尖瓣風濕性受累后圍繞三尖瓣瓣環的心肌結構發生收縮性改變是導致三尖瓣反流的病理基礎。反復風濕活動累及心肌,使心肌發生纖維化改變,致右室功能不全加重而引起TR。梅舉等研究認為,風濕性病變可累及心肌,使心肌呈纖維化改變,導致右心室功能不全加重引起TR。
1.2 心房纖維性顫動 二尖瓣或雙瓣病變患者常合并心房纖顫,房顫時心房機械活動紊亂,失去主動、規律的收縮和舒張功能,血液動力學改變,在心房內形成渦流,出現血流淤滯造成心房擴大,最終可導致三尖瓣瓣環擴大而繼發FTR。Kim等[3]研究發現,術前為竇性心律和術后恢復竇性心律的患者,術后遠期FTR加劇比例遠低于房顫者,證實房顫是FTR的獨立危險因素。
1.3 肺動脈高壓 肺動脈高壓是引起FTR的傳統觀念,長期持續的肺循環高壓,造成右室負荷增加,進一步使右心室幾何構型由原近橢球形向近球形改變,并引起三尖瓣瓣環擴大進而發生FTR。但近年一些作者對傳統觀念提出疑問。Skudicky等[4]使用超聲心動圖測量肺動脈壓,發現肺動脈壓與FTR程度并非線性關系。Matsuyama等[5]研究發現,在接受二尖瓣置換術的患者中,術前有肺動脈高壓組患者術后遠期僅有13%出現FTR,而無肺動脈高壓組患者術后反而17%出現FTR,故認為術前肺動脈高壓并不是術后遠期FTR的危險因素。Colombo等[6]研究發現二尖瓣病變繼發FTR或二尖瓣術后出現的FTR,肺動脈高壓并不是FTR的預測因子,FTR嚴重程度與肺動脈壓力高低無直接關系。
1.4 右心功能不全 Kaul等[7]對86例進行二尖瓣置換術后遠期出現TR的患者進行研究后認為,術前右心室擴大及右心室功能不全是術后TR復發和進展的危險因素。Kim等[3]應用超聲心動圖研究75例FTR患者的右心室偏心指數及球形指數,提出右心室幾何形態的改變及三尖瓣環徑與FTR密切相關。持續的肺動脈高壓可導致右心功能不全和右室心肌重構,進而使三尖瓣環擴大,乳頭肌移位三尖瓣瓣葉受到牽拉,最終構成TR。而TR又進一步加劇右室擴張,加重右心室功能不全,使三尖瓣環受到牽拉而擴張形成惡性循環。Porter等[8]研究認為,肺動脈高壓使右心室容量負荷增加,幾何構型改變,從而妨礙右心室游離壁朝向室間隔的風箱樣運動,導致右心室功能下降,進而逐漸出現TR。隨著TR的逐漸增加,右心室逐漸擴大,右心功能也越來越差,造成右心室舒張壓增加、室間隔移向左室,使左室受壓,從而限制了左室充盈,導致左室舒張壓和肺動脈壓增高,形成惡性循環,Antunes等[9]把上述現象叫做“限制擴張綜合征”。Kaul等[7]報道了86例風濕性心臟二尖瓣置換術后伴中度TR的患者。在隨訪中發現重度肺動脈高壓[(78±14)mm Hg]患者與非重度肺動脈高壓[肺動脈收縮壓(41±6)mm Hg]患者相比反而有更好的心功能,更高的存活率。出現這種現象可能的原因是非重度肺動脈高壓的患者可能心功能更差,FTR是右心功能不全的一種表現,因此FTR是提示患者預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1.5 左室功能不全 Matsunaga等[10]研究認為,左室功能不全會影響FTR治療的遠期效果。左心室功能不全患者常伴左室幾何構型的改變,這種改變通過室間隔、心室間交錯的肌纖維及心包直接引起右心室構型及功能改變,也可通過影響肺動脈壓而間接影響右心功能。weber等[11]在實驗中證實,左心室幾何構型變化與右心室壓力相關,左心室形態改變時右心室也受其影響發生構型改變,并最終導致右心室功能不全,并且心包完整時心室間的相互影響無論在舒張期或收縮期都更加明顯。左右心通過肺循環、體循環相互聯系起來形成循環回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左心功能不全可以影響右心功能,從而導致FTR。同樣左心室功能不全可致左心室舒張末壓增高并引起肺動脈高壓進而影響右心室結構和功能變化的導致FTR進展。所以左心功能不全是造成FTR的重要因素之一。
1.6 人工瓣膜對FTR的影響 研究表明,左心機械瓣置換術后人工瓣跨瓣壓差明顯高于自然瓣膜,持續的影響誘發病變,左房壓力升高及房顫與術后三尖瓣反流加重或繼發相關[12]。雖然歷經第一二代瓣膜后,第三代中心血流的雙葉機械瓣與過去的機械瓣相比,血流動力學更好,而且降低了與瓣膜相關的并發癥,但各種人工瓣膜均沒有達到完全符合生理的程度。近年來出現了機械三葉瓣,其跨瓣壓差遠小于雙葉瓣,而且血流動力學表現優于雙葉瓣,可能成為未來機械瓣的發展方向。更小的跨瓣壓差,更好的血流動力學,可能更有利于改善心功能,從而阻止或延緩FTR的進展。此外硬質的機械瓣環對心室的收縮及舒張也可能有一定的影響,但目前還缺乏相關臨床研究,有待進一步證實。
2 FTR的診斷學進展
二維超聲是目前最常用的診斷方法,但常規的二維超聲技術很難準確評估右心室的容量和功能。脈沖式多普勒超聲心動圖從血流動力學角度評價右心功能,可避免對右心室形態幾何假設引起的誤差。組織多普勒是近年發展起來的評價右心室功能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在傳統的多普勒技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無創、定量分析室壁運動的新技術。心肌功能指數[13](Tei指數)是近年由日本學者提出的評價心功能的新方法。右室Tei指數的測量:右室Tei指數=(右室等容收縮時間IRT+等容舒張時間ICT)/右室射血時間ET。它可用脈沖多普勒頻譜和組織多普勒頻譜兩種方法測得,且兩者間存在良好的相關性。研究表明Tei指數越大三尖瓣反流越嚴重,Tei指數越大右室功能損傷也越嚴重。實時三維超聲心動圖測定心室容積不受心室幾何形態限制,主要優點是容量分析不再基于假設的幾何形態,從心室整體采集數據,在定量心腔容積和評價心功能上較二維超聲心動圖更具優勢。心臟多層螺旋CT掃描及心臟核磁共振成像(CMRI)對右心衰竭的診斷較準確,其可提供右心室的形態、功能及組織特點等參數,且重復性較超聲心動圖更佳,尤其是其能反映右心室復雜的幾何結構。
3 手術適應證及手術方案的選擇
臨床上許多重度TR患者被推薦外科手術時已經發生右心衰,心功能差,失去了最佳手術時機,這是TR手術治療死亡率高的重要原因。傳統的三尖瓣成形術如Kay成形、De-Vega及改良DeVega成形近年已有大量臨床研究表明其遠期效果并不理想,已經逐漸被淘汰。
TR手術指征的問題,以往認為左心瓣膜術后TR會逐漸好轉并不需要處理的觀念已經過時,目前大多數學者認同2006版ACC/AHA和ESC指南,指南中均把二尖瓣病變伴重度TR的患者二尖瓣手術同時行三尖瓣環成形作為I類推薦。ESC把三尖瓣環直徑≥40 mm的中度TR作為IIa類推薦,左心瓣膜置換術后出現TR臨床癥狀但沒有嚴重的左心衰、右心衰、重度肺動脈高壓的患者也作為三尖瓣環成形IIa類推薦的對象。而ACC/AHA把二尖瓣置換術后伴有肺動脈高壓和三尖瓣環擴張的輕-中度TR作為IIb類推薦。目前美國心臟病協會(ACC/AHA)和歐洲心臟病協會(ESC)更多推薦的是人工瓣環成形術。尤其是嚴重的三尖瓣反流伴有肺動脈高壓和肺血管阻力增高的患者,研究表明三尖瓣環成形遠期效果良好。目前常用的是Cosgrove-Edwards成形環,是一種C形的三維彈性軟環,其優點是三維空間設計能最大限度貼合患者的解剖形態,減少縫線的張力,能更準確地瓣膜重塑,植入后有效保存了三尖瓣環的生理形態和活動,又可消除因縫合隔瓣環所引起的傳導組織損傷[14]。在大多數病例中,人工瓣環成形是目前最好的治療FTR的方法,這種方法有利于提高生存率、阻止遠期TR和心衰的發生。研究發現,輕度FTR保守治療可以獲得良好的效果,中-重度三尖瓣反流積極行人工瓣環成形術遠期效果良好。對于瓣膜損傷、瓣葉脫垂以及擴張性心肌病瓣膜損害較復雜的患者可行“Edge-to-Edge或Clover”結合人工瓣環成形進行功能矯正也可獲得一定的臨床效果。
對于瓣膜本身病變比較嚴重,成形效果不佳的患者可行三尖瓣置換(TVR),此類患者多存在嚴重的右心功能不全,往往合并肝、腎功能不全,病情復雜,圍手術期處理難度大,手術死亡率較高。國外文獻報道三尖瓣置換住院病死率高達10% ~54%[15]。因此,對三尖瓣置換的手術適應證應采取慎重態度。在TVR中人工瓣種類的選擇一直存在爭議,有的推薦生物瓣,有的推薦機械瓣,也有分析認為兩者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16]。目前國內多數學者認為生物瓣優于機械瓣。Rizzoli等[17]對1160例三尖瓣置換的病例研究,其中生物瓣646例,機械瓣514例,發現生物瓣和機械瓣的近、遠期生存率以及需要再次手術的病例并沒有統計學差異。正因為兩者相比沒有一種比另一種具有更大的優越性,所以臨床上可以依據具體情況適當選擇瓣膜的種類。已經左心機械瓣置換的患者一般認為三尖瓣宜植入機械瓣;相對年齡輕的患者考慮到生物瓣的使用壽命也宜植入機械瓣。由于機械瓣有潛在的抗凝相關的出血風險及機械瓣跨瓣壓差問題,除上述情況以外一般臨床上多傾向于使用生物瓣。左心瓣膜置換術后再次手術存在較大困難和風險,因此對左心瓣膜置換術后再發嚴重FTR的患者要嚴格掌握手術指征。
筆者認為,FTR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形成的,可稱之為“功能性三閉綜合征”。現有的研究尚不能全面地說明其原因,尤其是神經內分泌機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尚未被充分揭示。忽視FTR的本質原因認為左心瓣膜術后FTR會逐漸好轉的觀念已經被取代,同樣忽視FTR發生的本質原因一味追求外科手術顯然也是不科學的。目前臨床上對FTR的處理還缺乏成熟的經驗,只要充分理解了FTR的病理變化及臨床特點,針對不同時期的病理生理特點給予合理的內科治療或合理外科干預,FTR就可能獲得較滿意的預后。
[1]Dreyfus GD,Corbi PJ,Chan KMJ,et al.Secondary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or dilatation:which should be the criteria for surgical repair[J].Ann Thorac Surgery,2005,79:127 -132.
[2]Antunes MJ,Barlow JB.Management of tricuspid valve regurgitation[J].Heart,2007,93:271 - 276.
[3]Kim HK,Kim YJ,Kim KI,et al.Impact of the maze operation combined with left-sided valve surgery on the change in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over time[J].Circulation,2005,112(9 Suppl):I14 - I19.
[4]Skudicky D,Essop MR,Sareli P.Efficacy of mitral balloon valvotomy in reducing the severity of associated tricuspid valve regurgitation[J].Am J Cardiol,1994,73(2):209 -211.
[5]Matsuyama K,Matsumoto M,Sugita T,et al.Predictors of residual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after mitral valve surgery[J].Ann Thorac Surg,2003,75(6):1826 -1828.
[6]Colombo T,Russo C,Ciliberto GR,et al.Tricuspid regurgitation secondary to mitral valve disease:tricuspid annulus function as guide to tricuspid valve repair[J].Cardiovasc Surg,2001,9(4):369 -377.
[7]Kaul TK,Ramsdale DR,Mercer JL.Functional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following replacement of the mitral valve[J].Int J Cardiol,1991,33(2):305-313.
[8]Porter A,Shapira Y,Wurzel M,et al.Tricuspid regurgitation late after mitral valve replacement:clinical and echocardiographic evaluation[J].J Heart Valve Dis,1999,8(1):57 -62.
[9]Avinoam S MD,Alex S MD.Tricuspid Regurgitation in Mitral Valve Disease Incidence,Prognostic mplications,Mechanism,and Management[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2009,53(5):587-589.
[10]Matsunaga A,Duran CM.Progression of tricuspid regurgitation after repaired functional ischemic mitral regurgitation[J].Circulation,2005,suppl(112):1453 -I457.
[11]Weber KT,Janicki JS,Shroff S,et al.Contractile mechanics and interaction of the right and left ventricles[J].Am J Cardiol,1981,47(3):686-695.
[12]朱曉東,張寶仁.心臟外科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314-319.
[13]Harada K,Tamura M,Toyono M,et al.Comparison of the right ventricular Tei index by tissue Doppler imaging to that obtained by pulsed Doppler in children without heart disease[J].Am J Cardiology,2002,90(5):566 -569.
[14]Matsuyama K.DeVega Annuloplasty and Carpentier-Edwards Ring Annloplasty for Secondary tricuspid regurgitation[J].Heart Velve Disease,2001,10:520 -521.
[15]Shahzad GR,Gilled DD.Surgery for functional tricuspid regurgitation:current techniques,outcomes and emerging concepts[J].Cardiovasc,2009,7(1):73 -84.
[16]Chang BC,Lim SH,Yi G,et al.Long term clinical results of tricuspid valve replacement[J].Ann Thorac Surg,2006,81(4):1317-1323.
[17]Rizzoli G,Vendramin I,Nesseris G,et al.Biological or mechanical prostheses in tricuspid position?A meta-analysis of intra-institutional results[J].Ann Thorac Surg,2004,77(5):1607 -1614.
10.3969/j.issn.1674-4985.2012.02.106
350001福建醫科大學省立臨床醫學院(梁麗明);福建省立醫院(梁麗明,陳同)
陳同
2011-11-01)
(本文編輯:陳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