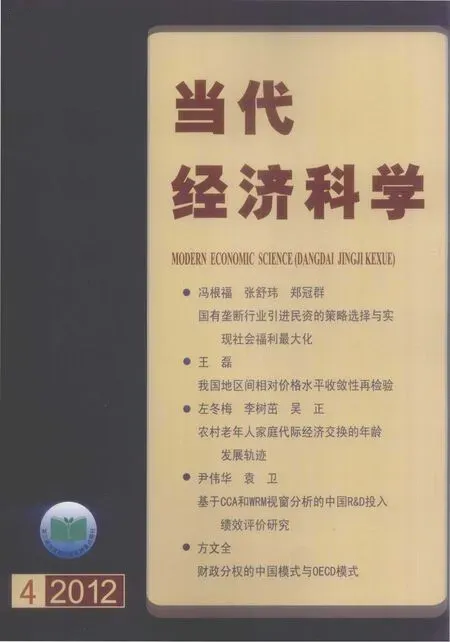財政分權(quán)的中國模式與OECD模式:分稅制是財政集權(quán)嗎
方文全
(上海理工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上海200093)
一、引 言
1994年以來,分稅制確立的財政分權(quán)制度成為促使各地區(qū)競爭性經(jīng)濟增長的重要制度動力。進入“十二五”時期,中國經(jīng)濟進入新一輪的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和增長模式轉(zhuǎn)變階段,政府行為調(diào)整成為其中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政府間財政關(guān)系及其經(jīng)濟效應(yīng)問題再次成為理論焦點。延續(xù)以往的理論路徑和關(guān)注熱情,新近的研究尤為注重深入揭示財政分權(quán)引致的政府間競爭行為模式,反思分權(quán)的整體福利效應(yīng),進而推論后續(xù)深化改革的方向和措施。
研究中存在脈絡(luò)分明、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關(guān)鍵的分歧是對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性質(zhì)判斷,一種觀點認為分稅制是對之前過度分權(quán)的調(diào)整,確立了中央與地方相對合理穩(wěn)定的財政分權(quán)關(guān)系[1-3];另一種觀點明確認為這是一次集權(quán)安排[4-5]。相關(guān)問題的不同結(jié)論都與分稅制的分權(quán)或集權(quán)性質(zhì)問題判斷有關(guān):中央-地方政府財政關(guān)系的分權(quán)程度處于怎樣的水平?各級政府的事權(quán)與財權(quán)匹配問題實質(zhì)何在?近年來地方政府的財政行為偏差是否應(yīng)該歸咎于分稅制?下一步的財政關(guān)系調(diào)整路徑是繼續(xù)分權(quán)還是再度集權(quán)?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權(quán),與經(jīng)濟去中央計劃化進程緊密相連,分稅制改革的現(xiàn)實動機確實是為了保證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穩(wěn)定和職能正常運轉(zhuǎn)[6],但將這種改革實驗的試錯結(jié)果斷定為集權(quán)的理由非常不充分。本來重要的是確立一個分權(quán)最優(yōu)標(biāo)準(zhǔn)并據(jù)此判斷分稅制的分權(quán)水平,但在無法確定存在一個最優(yōu)分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理論支持的情況下,這些問題都只能轉(zhuǎn)而通過比較現(xiàn)實、由經(jīng)驗結(jié)論來解答更為可靠。
進一步地,對中國分權(quán)水平的判斷,將涉及對參照對象的考察和判斷,也將觸及財政分權(quán)理論與現(xiàn)實是否脫節(jié)的問題。這其實是一個始終鮮有人深入研究的疑惑,即兩代財政分權(quán)理論的經(jīng)驗基礎(chǔ)究竟有何差異?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轉(zhuǎn)軌國家的財政分權(quán)程度分別處于什么水平?針對這一問題,本文將比較分析中國與OECD國家的財政分權(quán)及相應(yīng)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結(jié)構(gòu),在厘清事實的基礎(chǔ)上探討財政分權(quán)制度及其經(jīng)濟效應(yīng)的差異,為理解中國體制改革進程中政府行為提供經(jīng)驗證據(jù)。
二、文獻綜述
關(guān)于政府財政分權(quán)及其經(jīng)濟福利效應(yīng),兩代分權(quán)理論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研究。第一代財政分權(quán)理論從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的現(xiàn)實出發(fā),在假定治理結(jié)構(gòu)穩(wěn)定完善的前提下,從稅收征收與公共品供給匹配的角度闡述了財政分權(quán)有利于地方政府公共職能的正常運行[7];第二代財政分權(quán)理論著眼于轉(zhuǎn)軌和發(fā)展中經(jīng)濟的去中央計劃化過程,更為關(guān)心地方政府的經(jīng)濟增長角色和財政行為規(guī)范化[8]。需要明確的是,兩代理論對財政分權(quán)的界定包含著側(cè)重點不同的三個層次,一是財權(quán)權(quán)力和財政資源向地方政府轉(zhuǎn)移,以及地方政府有效地向本地居民提供合意的公共服務(wù);二是制度化的轉(zhuǎn)移支付,即存在有效的中央對地方垂直約束;三是政府職能明確和預(yù)算硬約束。只有這三個層面的內(nèi)涵是確定的,政府間橫向和縱向的競爭均衡分析才有意義。以中國的實際應(yīng)用視角,兩代分權(quán)理論通常被總結(jié)為收入的稅收競爭[9]和支出的 GDP 增長競爭[10]觀點的區(qū)別。因此,在分權(quán)指標(biāo)構(gòu)造和經(jīng)濟績效測度上也就存在差異。
在分權(quán)指標(biāo)問題上,理論觀點和實證方法并不統(tǒng)一、進展有限[11]。如上所述,完整的財政分權(quán)應(yīng)該綜合考察收入分權(quán)指標(biāo)、支出分權(quán)指標(biāo)和預(yù)算約束指標(biāo),單純分析其中一種指標(biāo)如廣泛采用的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權(quán)”是不夠全面的。度量指標(biāo)的多樣化實際上意味著衡量分權(quán)程度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存在困難,即是否存在一個最優(yōu)的分權(quán)結(jié)構(gòu)[12-13]并沒有理論結(jié)論①Gordon模型[12]的假定條件包括政府公共職能明確和稅收預(yù)算硬約束,其最優(yōu)分權(quán)結(jié)構(gòu)下的政府規(guī)模顯示解對于不具備這些條件的經(jīng)濟僅具參考意義;中國式分權(quán)模型[13]的最優(yōu)結(jié)構(gòu)完全取決于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的縱橫交錯博弈結(jié)果,更難獲得穩(wěn)定的唯一均衡解。。在財政分權(quán)效果評估問題上,也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迄今為止的跨國實證文獻還不能證實財政分權(quán)與經(jīng)濟增長、公共服務(wù)供給存在確切的關(guān)系,財政分權(quán)與宏觀經(jīng)濟不穩(wěn)定性、政府腐敗和地區(qū)差異等間接效應(yīng)的關(guān)系也莫衷一是。
衡量指標(biāo)與績效評估的不確定性與世界各地財政分權(quán)改革的現(xiàn)實基礎(chǔ)和進程有關(guān),即分權(quán)程度、財政資源轉(zhuǎn)移與治理結(jié)構(gòu)的匹配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衡量指標(biāo)建構(gòu)和績效評價結(jié)果;轉(zhuǎn)軌國家正在經(jīng)歷制度變遷,分權(quán)進程及其效應(yīng)的差異尤其明顯。這樣,由于不同國家的制度架構(gòu)使得分權(quán)結(jié)構(gòu)及其效果呈現(xiàn)不同的動態(tài)特點,大樣本跨國研究更需謹慎對待(參見文獻[11]的文獻綜述)。從計量技術(shù)的角度講,不同經(jīng)濟體的分權(quán)水平和政府行為存在顯著差異,意味著作為研究對象的數(shù)據(jù)存在聚類和異方差等異質(zhì)特征,以此估計的結(jié)果和判斷結(jié)論是有偏的。因此如果忽視第一代理論將治理結(jié)構(gòu)完善作為假定前提條件、第二代理論則將其作為制度改進目標(biāo),脫離現(xiàn)實背景抽象地談?wù)摲謾?quán)優(yōu)劣,我們將一無所獲。
1990年代后期以來,研究中國財政分權(quán)的國內(nèi)文獻異常豐富,對財政分權(quán)的公共品供給和增長效應(yīng)及其地區(qū)差異收斂前景都做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分析,主要從第二代理論的支出競爭角度證實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分稅制形成的制度化財權(quán)分權(quán)有效地促進了地區(qū)經(jīng)濟增長[2-4],同時也帶來一系列附加效應(yīng),如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jié)構(gòu)出現(xiàn)“重基本建設(shè)、輕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服務(wù)”的扭曲[10]。經(jīng)過十多年分稅制改革實踐,近期的研究文獻更加重視揭示財政分權(quán)的競爭博弈機制和地方政府行為模式,反思其在公共品供給和地區(qū)差距效應(yīng)方面的缺陷。沈坤榮和付文林[9]在第二代理論基礎(chǔ)上,重新強調(diào)第一代理論的稅收減免-公共品供給匹配的地區(qū)間收入競爭機制。后續(xù)研究將這種收入競爭推廣到第二代理論框架中,進一步分析“中國式分權(quán)”的中央-地方、地方-地方“縱橫交錯”、“收支互動”的復(fù)雜效應(yīng)和地方政府策略[13]。由此對財政分權(quán)在加劇地區(qū)差異、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造成整體福利損失等方面有了更清醒的認識[14]。
這些反思明顯地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過度分權(quán)論,認為財政分權(quán)過度因而不利于經(jīng)濟穩(wěn)定平衡增長,主要體現(xiàn)為轉(zhuǎn)移支付結(jié)構(gòu)和力度存在缺陷、中央對地方的約束不足[15],以及地方政府自身的財政預(yù)算軟約束,支出的GDP增長競爭導(dǎo)致擴張性支出政策取向[16];并且,地方政府的競爭手段從稅收優(yōu)惠發(fā)展到財政支出總量和結(jié)構(gòu)政策,過度投資生產(chǎn)性物質(zhì)資本、忽視內(nèi)生要素和制度建設(shè)投資,收入-支出競爭導(dǎo)致財政結(jié)構(gòu)扭曲[13]。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的內(nèi)部與縱橫約束嚴(yán)重不足,分稅制的性質(zhì)不言自明。另一種是集權(quán)論,認為分稅制中央集權(quán)導(dǎo)致地方自主性財源萎縮、財權(quán)與事權(quán)不匹配,地方政府只能加大本地稅收征收力度和拓展預(yù)算外、體制外收入,呈現(xiàn)出“攫取之手”的性質(zhì)[4];并扭曲支出結(jié)構(gòu)、惡化公共服務(wù)水平[5]。解決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進一步分散下放財政權(quán)力和資源,才能矯正地方政府行為、實現(xiàn)經(jīng)濟平穩(wěn)增長。這樣,解決中央和地方財政關(guān)系的“事權(quán)與財權(quán)匹配”問題就指向再分權(quán)和再集權(quán)兩個方向。
由于理論背景存在“代際”差異,從完整的財政分權(quán)涵義來看,關(guān)于中國的研究文獻存在局限,有幾個問題還需要澄清。首先,如前所述,財政分權(quán)含有多方面的內(nèi)容、側(cè)重點不一致,單純考察某一類指標(biāo)總是有偏頗的,需要多個角度相對完整地分析政府間財政關(guān)系。其次,分權(quán)是縱橫博弈的結(jié)果,分稅制是否偏離最優(yōu)水平、分權(quán)程度和合理性除了以經(jīng)濟績效來自我證明之外,應(yīng)該可以從國際間橫向比較獲得證據(jù)。再次,即使分稅制并非最優(yōu),但收支結(jié)構(gòu)扭曲是地方政府應(yīng)激策略的正反饋效應(yīng),將這種財政失范歸咎于分稅制邏輯上不成立,那么以再分權(quán)或再集權(quán)來糾正還是無濟于事,還可能導(dǎo)致新的無法預(yù)測的策略反應(yīng)。最后,需要指出的計量技術(shù)問題,多數(shù)經(jīng)驗研究結(jié)論其實并沒有令人信服地控制住財政預(yù)算約束軟硬程度的影響,因此兩類觀點甚至無法相互證偽,地方公共收支扭曲的原因到底歸咎于分權(quán)、集權(quán)還是地方政府自身依然不明確,未來改革方向也就不清楚了。
在缺乏嚴(yán)格理論標(biāo)準(zhǔn)的情況下,將這一問題置于國際背景中進行比較,有利于我們更清楚地厘清分稅制的性質(zhì)。以O(shè)ECD為代表的發(fā)達國家的財政分權(quán)制度比較成熟,是可能的轉(zhuǎn)軌目標(biāo),也是第一代財政分權(quán)理論的經(jīng)驗基礎(chǔ),因而是一個合適的比較對象。
三、中國與OECD財政分權(quán)結(jié)構(gòu)比較
為了避免概括性地使用財政分權(quán)概念和指標(biāo)而實際上并沒有明確界定其內(nèi)涵,本文主要關(guān)心以下幾個與分權(quán)有關(guān)的財政收支結(jié)構(gòu):收入與支出結(jié)構(gòu);收入結(jié)構(gòu);功能性支出結(jié)構(gòu)。
本文將中國各地區(qū)和OECD國家作為兩個對照組進行比較分析。1994年為中國實施分稅制的事件窗口,本文將比較1995-2009年的數(shù)據(jù)。中國的數(shù)據(jù)根據(jù)歷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相關(guān)數(shù)據(jù)計算整理;OECD國家數(shù)據(jù)來自“OECD Fiscal Decentralisation Database”和“OECD Revenue Statistics”。
需要先予以說明的是,第一,以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計算的宏觀稅負水平,1995年以來OECD國家平均為31%;中國為15%,加上預(yù)算外收入為19%,仍然遠遠低于發(fā)達國家。不過OECD基本保持穩(wěn)定,而中國則呈平緩上升趨勢,從1995年的14.5%上升到2009年的22%。盡管經(jīng)濟發(fā)展階段的邊際稅率是有上升趨勢的,但這一比較結(jié)果可以說明分稅制以來的政府財政行為并未全面惡化宏觀稅負狀況,是否稅收競爭機制的結(jié)果則有待深入研究。第二,OECD國家中并不存在預(yù)算外收入和支出,而中國各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預(yù)算外收支都占據(jù)相當(dāng)重要的比例,這可以說明預(yù)算軟約束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無需借助構(gòu)建各種分權(quán)指標(biāo)而直接比較中央和地方收入支出結(jié)構(gòu)就可以得到直觀的證據(jù)。
本文分別計算了1995-2009年的中國和OECD的中央財政收入支出比重、地方財政收入構(gòu)成和功能性支出構(gòu)成比重,具體結(jié)果見圖1至圖6;其中圖1和圖2的數(shù)據(jù)均為調(diào)整的中央財政收入和支出,已經(jīng)減去政府間轉(zhuǎn)移支付。
從收入分權(quán)角度比較可見,從1995年到2009年,OECD國家的平均中央財政收入都高于80%。同期的中國中央財政收入比重平均為52.4%;結(jié)合1978-1994年平均為31.0%、且波動較大的情況,可見中國的財政分權(quán)始于改革開放之后的經(jīng)濟去中央計劃化,試錯過程確實可能導(dǎo)致分權(quán)過度影響中央履行職能和約束下級,分稅制只是制度化安排的開端,提高了中央財政比重,保證了中央財政基本權(quán)力穩(wěn)定。相比之下,中國財政收入分權(quán)結(jié)構(gòu)變化有其獨特性,因此被認定為集權(quán)卻并不合理。
從支出的角度看,OECD中央財政支出比重超過70%,而中國中央財政支出比重低于30%。即在收入分權(quán)、中央集中部分地方財政收入的同時,以轉(zhuǎn)移支付的形式返還給了地方,其中相當(dāng)部分用于補助財政困難地區(qū)。結(jié)合分稅制前后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劃分沒有發(fā)生顯著變化的情況,可以說分稅制似乎沒有根本改變中央和地方的事權(quán)劃分格局。但需要追問的關(guān)鍵問題是,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中有多大比重是職責(zé)明確合理和受預(yù)算約束的?
因此,判斷分稅制改革的實質(zhì),不能僅僅根據(jù)財政收入比重的變化和地方需要部分依靠中央的轉(zhuǎn)移支付履行公共職責(zé)而斷定為中央集權(quán)。須知“財政聯(lián)邦主義”的含義本來就包括收入權(quán)力劃分和適當(dāng)?shù)霓D(zhuǎn)移支付。追求完全的地方“財政自主權(quán)”,那就不叫聯(lián)邦主義,而是無中央政府主義。






在地方政府的收入結(jié)構(gòu)方面,以O(shè)ECD 2006年和中國2007年①2007年中國實施政府收支分類改革,財政統(tǒng)計體系基本與發(fā)達國家接軌,統(tǒng)計口徑更具可比性。為例,28個OECD國家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中本地稅收比重為40.9%,中央政府的轉(zhuǎn)移支付比重為43.3%。而中國各省級地區(qū)地方財政總收入中本地稅收收入占40.0%,來自中央轉(zhuǎn)移支付占34.1%,非稅收入占9.7%,預(yù)算外收入比重達到16.2%,成為重要的收入來源。以收入結(jié)構(gòu)衡量,不管是中央-地方的財政收入比重,還是中央對地方轉(zhuǎn)移支付確定的垂直約束力度,中國的財政分權(quán)程度都超過發(fā)達國家。這樣,財政分權(quán)和預(yù)算軟約束背景下地方財政失控的可能性才值得擔(dān)憂。
財政收入支出結(jié)構(gòu)必須與功能性支出結(jié)構(gòu)對照才能更加清楚地說明問題所在。在OECD國家,地方財政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務(wù)支出占21.0%,經(jīng)濟事務(wù)占25.5%,健康和文化教育等占38.0%,社會保護為15.5%。中國地方財政一般公共服務(wù)支出占24.4%,經(jīng)濟事務(wù)占35.4%,健康和文化教育等占26.4%,社會保護13.8%。這一結(jié)構(gòu)在1994年分稅制之后出現(xiàn)了顯著的趨勢性變化:在能夠給地方政府帶來GDP增加值和財政收入增長的經(jīng)濟事務(wù)財政支出一直呈上升趨勢,而科教文衛(wèi)和社會保障支出的比重基本穩(wěn)定甚至略有下降。中國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最大的為經(jīng)濟事務(wù),預(yù)算內(nèi)結(jié)構(gòu)偏向的經(jīng)濟性支出有明顯的GDP增長效應(yīng)①財政分權(quán)與政府規(guī)模關(guān)系的Leviathan假說沒有得到證實,說明并非完全不存在縱橫約束和內(nèi)部約束。。
通過對中國和OECD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guān)系的比較分析,本文明確認定,1994年分稅制改革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分權(quán)關(guān)系調(diào)整進程的一次制度化安排,是中央與地方政府動態(tài)博弈的階段性結(jié)果,反映了轉(zhuǎn)軌發(fā)展中經(jīng)濟的治理權(quán)力分散化進程。中國的完整意義上的經(jīng)濟財政分權(quán)基本框架由此奠定,但相應(yīng)的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公共職能明確和預(yù)算約束硬化進展不大。僅僅根據(jù)事件前后財政收入比重變化認為這是一次集權(quán)改革,甚至將地方政府應(yīng)激策略的正反饋效應(yīng)也歸咎于財政“集權(quán)”事件,明顯偏離事實,嚴(yán)重誤判現(xiàn)階段財政關(guān)系和地方政府行為后果的性質(zhì)。
中國的財政分權(quán)引致經(jīng)濟分權(quán)即經(jīng)濟聯(lián)邦主義[8]或曰諸侯經(jīng)濟[14],從聯(lián)邦主義的規(guī)范性分析,地方政府的財政機會主義(Fiscal Opportunism[17])才是特質(zhì)。當(dāng)然政治集權(quán)的中央政府對此有時并不排斥,如在實施相機抉擇的財政刺激措施時,需要地方政府以自有財源及時配合。
四、財政分權(quán)的經(jīng)濟績效檢驗
那么迥異的財政分權(quán)格局在經(jīng)濟運行的哪一個層面上發(fā)揮關(guān)鍵性影響并構(gòu)成差異呢?本文利用上述中國數(shù)據(jù)回歸檢驗財政分權(quán)的GDP增長和公共品供給效應(yīng),并將OECD國家作為對照組。為了直觀地刻畫財政分權(quán)與經(jīng)濟增長和公共品供給的基本關(guān)系,在單變量回歸方程中檢驗:

其中,被解釋變量Yit,依次取1990年不變價格的對數(shù)人均GDP增長率(GDPit)和以財政均等化指標(biāo)(FEEit)衡量的公共品供給水平。
公共品供給測度是一個重要而有爭議的難題。關(guān)于財政均等化(Fiscal Equalization[18]),財政聯(lián)邦主義理論明確指出公共品供給政均等化是再分配政策目標(biāo),人均財政支出可以用于衡量分權(quán)制度下的公共品供給水平及差異;并應(yīng)該考慮地區(qū)人口規(guī)模、經(jīng)濟發(fā)展和城市化水平造成的公共品需求和供給差異,發(fā)展了基于需求的財政均等化指標(biāo)。考慮到中國的具體情況,本文采用各地區(qū)人均財政支出的平均值(FEAit),并以各地人均GDP增長(φit)和城市人口占總?cè)丝诒戎刈儎?μit)兩個環(huán)比指數(shù)予以調(diào)整,即FEEit=FEAitφμ為基本財政均等化指標(biāo);則均等化差異即各地區(qū)偏離均等水平的超額公共品供給為實際人均財政支出(FERit)減去均等化水平(FEEit)。這樣得到一個財政均等化指數(shù):FEIit=FERit/FEEit;本文主要檢驗財政均等化指數(shù)FEIit。限于本文目標(biāo)和篇幅,公共品供給類型不做細分測度,這是后續(xù)研究應(yīng)該細致考察的。
解釋變量FDit為財政分權(quán)指標(biāo),本文主要分別檢驗收入分權(quán)(FDRit)和支出分權(quán)指標(biāo)(FDEit);對轉(zhuǎn)移支付(CTLit)和預(yù)算外支出(SBEit)也進行分析。收入分權(quán)指標(biāo)為地方財政收入與中央財政收入的比值代表;支出分權(quán)指標(biāo)以地方財政支出與中央財政支出的比值代表;財政收入和支出都為扣除政府間轉(zhuǎn)移支付的調(diào)整數(shù)據(jù)。轉(zhuǎn)移支付和預(yù)算外支出指標(biāo)分別為轉(zhuǎn)移支付在總收入、預(yù)算外支出在總支出中的比重。
面板數(shù)據(jù)模型。在全國34個省市自治區(qū)中,重慶與四川合并計算,西藏、香港、澳門和臺灣不包括在內(nèi),這樣得到了包含29個省市自治區(qū)的截面數(shù)據(jù);時間序列方面,考慮到數(shù)據(jù)的統(tǒng)計口徑一致性和可得性,選取經(jīng)過普查調(diào)整的1995-2008年為樣本期,這樣構(gòu)成平衡面板數(shù)據(jù)。經(jīng)檢驗選擇,估計過程中采用截面固定效應(yīng)技術(shù);同時還分別檢驗分地區(qū)數(shù)據(jù)。面板水平數(shù)據(jù)估計中采用AR(1)方法以確保其平穩(wěn)性。為了厘清基本事實,所以將全國和分地區(qū)檢驗結(jié)果詳細列出,主要結(jié)果見表1至表6。OECD的部分結(jié)果見圖7和圖8的散點圖。
表1列示了財政收入分權(quán)指標(biāo)與人均GDP增長的檢驗結(jié)果。在收入分權(quán)與人均GDP增長率的關(guān)系上,如將全國所有地區(qū)作為一個整體似乎存在反向關(guān)系。但分地區(qū)檢驗可見,這種反向關(guān)系僅在西部地區(qū)才是顯著的,在東部和中部都不存在。財權(quán)集中對占有主要貢獻的較發(fā)達地區(qū)的經(jīng)濟增速影響并不大,整體上應(yīng)該沒有負面作用。表2的支出分權(quán)與人均GDP增長的檢驗結(jié)果可見,支出分權(quán)與經(jīng)濟增長有顯著的正向關(guān)系,并且各地區(qū)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從這兩個常用分權(quán)指標(biāo)的增長效應(yīng)上看,收入分權(quán)與支出分權(quán)的效果是明顯不對稱的,還有一些重要的需要識別的地區(qū)差異,因此分析政府間財政關(guān)系及其經(jīng)濟效果,相關(guān)結(jié)論和政策引申需要非常小心。

表1 人均GDP增長與收入分權(quán)FDR檢驗結(jié)果

表2 人均GDP增長與支出分權(quán)FDE檢驗結(jié)果

表3 財政均等化指數(shù)FEI與收入分權(quán)FDR檢驗結(jié)果

表4 財政均等化指數(shù)FEI與支出分權(quán)FDE檢驗結(jié)果

表5 財政均等化指數(shù)FEI與轉(zhuǎn)移支付CTL檢驗結(jié)果

表6 財政均等化指數(shù)FEI與預(yù)算外支出SBE檢驗結(jié)果
表3顯示收入分權(quán)與財政均等化實際上僅在東部地區(qū)具有非常明顯的正向關(guān)系;表4說明支出分權(quán)對財政均等化指數(shù)有顯著的正向關(guān)系,并且地區(qū)間差異不明顯。表5顯示,轉(zhuǎn)移支付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wù)均等化,尤其是在西部地區(qū)。表6可見,預(yù)算外支出總體上顯著不利于均等化公共服務(wù),地方政府軟約束具有明確的忽視公共服務(wù)均等化傾向。提供財政公共品服務(wù)是地方政府法定義務(wù),公共服務(wù)均等化則應(yīng)當(dāng)是中央政府的追求目標(biāo),在經(jīng)濟不發(fā)達地區(qū)尤其是西部地區(qū)預(yù)算內(nèi)收入無法保證提供均等化公共品服務(wù)的情況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中央政府以轉(zhuǎn)移支付保證經(jīng)濟落后地區(qū)的財政普遍服務(wù)本來就是財政分權(quán)的題中之義。
以上的回歸結(jié)果可見,中國分稅制背景下的收入分權(quán)與支出分權(quán)的作用并不對稱,這實際上正是來自兩代分權(quán)理論的經(jīng)驗基礎(chǔ)的差異,即由于地方政府行為偏倚導(dǎo)致的政策目標(biāo)動態(tài)不一致性。由于預(yù)算法的約束,預(yù)算內(nèi)支出結(jié)構(gòu)的有限調(diào)節(jié)不能帶來穩(wěn)定的預(yù)算內(nèi)收入增長,地方政府有強烈的動機突破預(yù)算約束,通過增加自主性的預(yù)算外支出,進一步強化生產(chǎn)性公共資本,帶來額外的GDP增長和財政邊際收入①詳細的檢驗結(jié)果可向作者本人索取。。長期擴張的財政支出最終將不利于經(jīng)濟穩(wěn)定增長,卻能帶來本地稅收、財政總收入尤其是預(yù)算外收入增加。稅收競爭機制不僅有本地征收減免的形式,還有結(jié)構(gòu)性偏向支出擴張的形式。如此清晰的經(jīng)驗事實說明,預(yù)算約束才是理解分權(quán)效果的關(guān)鍵之關(guān)鍵。直言之,地方軟約束才是其行為偏倚的根源,分稅制做了替罪羊,還背了集權(quán)的壞名聲。更坦率地說,考慮到中國經(jīng)濟的地區(qū)差異及其收斂前景已經(jīng)導(dǎo)致了難以容忍的福利損失,在中國討論財政分權(quán),將分稅制“集權(quán)”性質(zhì)作為經(jīng)驗基礎(chǔ),以此來推論計量結(jié)果的政策含義,得出需要更進一步下放財政權(quán)力的結(jié)論,是完全搞錯了方向。
圖7和圖8的結(jié)果顯示,OECD國家的財政支出分權(quán)指標(biāo),與人均GDP增長和均等化公共品供給不存在顯著的反向關(guān)系。程度如此之高的財政集權(quán),至少并沒有損害經(jīng)濟增長和公共服務(wù)。


中國的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guān)系不僅仍然屬于聯(lián)邦主義的范疇,而且處于高度分散狀態(tài),進一步調(diào)整需要強化對地方政府的垂直約束和自身預(yù)算約束,以適應(yīng)治理結(jié)構(gòu)和經(jīng)濟模式變化的要求。需要強調(diào)的是,由于中國與OECD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處于不同的階段,地區(qū)差異巨大,政府財政提供的公共服務(wù)均等化水平仍屬于起步階段,因此,效仿發(fā)達國家實施高度中央集權(quán)的財政體制也不合乎邏輯。
直觀的經(jīng)驗分析結(jié)果比較也許還可以得到直接的邏輯引申猜想。眾所周知,存在政治-財政關(guān)系的“中國式分權(quán)”與“俄羅斯式分權(quán)”的區(qū)別[19],本文的分析結(jié)果顯示,還可能存在政治分權(quán)與財政集權(quán)的“OECD式分權(quán)”,真正需要比較的是“中國模式”和“OECD模式”更加有趣的對比式組合。在中國,存在以各地區(qū)主要官員任命、晉升和異地調(diào)動等方式形成精英網(wǎng)絡(luò)式的政治集權(quán)②張軍和周黎安[10]關(guān)于官員晉升機制和GDP增長競爭的系列研究成果中包含一個至關(guān)重要但未充分闡釋的政治精英網(wǎng)絡(luò)化和政策趨同圖景(Elite Networking,Policy Convergence[20])。;在典型的聯(lián)邦制國家中,這種精英網(wǎng)絡(luò)與政治分權(quán)是相容的[20]。至此,可以明確地提出,“中國式分權(quán)”和“OECD式分權(quán)”也許正是聯(lián)邦主義治理結(jié)構(gòu)中政治-經(jīng)濟權(quán)力的不同組合模式。即在政治權(quán)力自下而上形成的國家,各地區(qū)分散決策的政治權(quán)力需要用相對集中的財政權(quán)力加以約束;而自上而下的政治授權(quán),則必須用相對分散的財政-經(jīng)濟權(quán)力予以激勵。這樣才能共同維護穩(wěn)定而有活力的政治-經(jīng)濟秩序,避免劇烈波動以至于崩潰。治理結(jié)構(gòu)的“中國模式”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Buchanan、Tiebout提出財政分權(quán)理論迄今已經(jīng)過去半個世紀(jì),如果發(fā)達國家確實根據(jù)理論指導(dǎo)實施財政分權(quán)政策,則取得的成果僅僅是中央財政的收入比重仍然高達80%、支出比重超過70%;即使嚴(yán)格實行財政聯(lián)邦制的美國,目前各州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比重平均占43.2%、支出比重為50.0%;單純的財政分權(quán)程度還遠不如中國。如此分權(quán)進程也太緩慢了,連漸進式改革都稱不上。鑒于某些官方觀點對轉(zhuǎn)軌國家的財政分權(quán)進程態(tài)度鮮明的負面評價,也許我們還需要追問甚至警惕理論與現(xiàn)實脫節(jié)背后是否存在華盛頓動機。
五、簡要結(jié)論
通過以上的實證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結(jié)論:第一,與OECD國家相比,中國的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quán)程度高得多,呈現(xiàn)了財政收入分權(quán)與支出分權(quán)不對稱的經(jīng)濟聯(lián)邦主義或曰諸侯經(jīng)濟模式。這種模式與典型的財政分權(quán)理論存在實質(zhì)性的差異,因此應(yīng)用主流理論框架討論中國的財政分權(quán)問題必須注意現(xiàn)實層面的顯著差異。
第二,在聯(lián)邦主義治理結(jié)構(gòu)中,可能存在對比式的中國式分權(quán)和OECD式分權(quán)模式,政治-經(jīng)濟權(quán)力的優(yōu)化組合是維持經(jīng)濟政治社會秩序穩(wěn)定而有活力的制度保證。在政治分權(quán)的OECD國家中,財政分權(quán)程度及其結(jié)構(gòu)具有極其明顯的中央集權(quán)特征;而在政治集權(quán)的中國,各地區(qū)的財政分權(quán)程度遠遠超過OECD國家,與此相連的政府支出結(jié)構(gòu)的分權(quán)差異更為明顯。
第三,與收入分權(quán)相對應(yīng)的支出分權(quán)是理解中國政府間財政-經(jīng)濟關(guān)系的關(guān)鍵。所謂中國的政府財權(quán)與事權(quán)的匹配問題,并不意味著分權(quán)程度不足,恰恰相反,由于財政分權(quán)和政府公共職責(zé)界定不清,導(dǎo)致地方政府超越公共職責(zé)和預(yù)算約束,財政機會主義傾向過于明顯。在此背景下,中央-地方財政關(guān)系的主要問題體現(xiàn)為中央財政權(quán)力過小和對地方政府的約束不足,這才是地方政府策略性行為的正反饋機制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
第四,分稅制改革不構(gòu)成財政集權(quán)事件,分稅制下的政府間財政關(guān)系依然處于高度分權(quán)狀態(tài)。從完整的財政分權(quán)內(nèi)涵上看,體現(xiàn)為中央集中的財政收入和對地方的垂直約束仍然有限,地方政府職能不明確、財政機會主義行為普遍和預(yù)算約束異常軟化;并且與發(fā)達國家成熟的財政聯(lián)邦主義相比,中國的財政分權(quán)程度更高。
第五,不管是以財政分權(quán)理論的稅收競爭觀點還是GDP增長競爭觀點解釋中國經(jīng)濟增長的地區(qū)競爭機制,分稅制都是基礎(chǔ)性的制度安排。如果存在一個分權(quán)的目標(biāo)模式,以經(jīng)濟增長速度優(yōu)化和地區(qū)均衡發(fā)展為今后的發(fā)展目標(biāo),財政分權(quán)理論應(yīng)用于中國中央與省級地方政府財政關(guān)系上的政策指向非常清楚:在明確規(guī)范化政府公共職責(zé)和硬化預(yù)算約束的基礎(chǔ)上適度財政集權(quán)化。
[1]Zhang Tao,Zou Hengfu.Fiscal decentralization,public spending,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8,67:221 -240.
[2]林毅夫,劉志強.中國的財政分權(quán)與經(jīng)濟增長[J].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科版),2000(4):4-17.
[3]張晏,龔六堂.分稅制改革、財政分權(quán)與中國經(jīng)濟增長[J].經(jīng)濟學(xué)(季刊),2005,5(1):75-109.
[4]陳抗,Hillman A,顧清揚.財政集權(quán)與地方政府行為變化:從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J].經(jīng)濟學(xué)(季刊),2002,2(1):111-130.
[5]陳碩.分稅制改革、地方財政自主權(quán)與公共品供給[J].經(jīng)濟學(xué)(季刊),2010,9(4):1427-1446.
[6]項懷誠,馬國川.改革是共和國財政六十年的主線(上)[J].讀書,2009(9):3-15.
[7]Tiebout C.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5):416-424.
[8]Qian Yingyi,Roland G.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5):1143-1162.
[9]沈坤榮,付文林.稅收競爭、地區(qū)博弈及其增長績效[J].經(jīng)濟研究,2006(6):16-26.
[10]張軍,周黎安.為增長而競爭:中國增長的政治經(jīng)濟學(xu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Boex J.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intergovernmental finance reform as an international strategy[R].IDG Working Paper,No.2009 -06,2009.
[12]Gordon R.An optimal taxation approach to fiscal federalism[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3,98(4):567-586.
[13]王美今,林建浩,余壯雄.中國地方政府財政競爭行為特性識別:“兄弟競爭”與“父子爭議”是否并存?[J].管理世界,2010(3):22-31.
[14]鄭毓盛,李崇高.中國地方分割的效率損失[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3(1):64-72.
[15]方紅生,張軍.中國地方政府競爭、預(yù)算軟約束與擴張偏向的財政行為[J].經(jīng)濟研究,2009(12):4-16.
[16]馬拴友,于紅霞.轉(zhuǎn)移支付與地區(qū)經(jīng)濟收斂[J].經(jīng)濟研究,2003(3):26 -33.
[17]Polackova H.Contingent government liabilities:A hidden risk for fiscal stability[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1989,1998.
[18]Blanchard O,Shleifer A.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R].NBER Working Paper,No.7616,2000.
[19]Buchanan M.Federalism and fiscal equ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0,40(4):583-599.
[20]Bennett C.What is policy convergence and what causes it?[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1,21(2):215-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