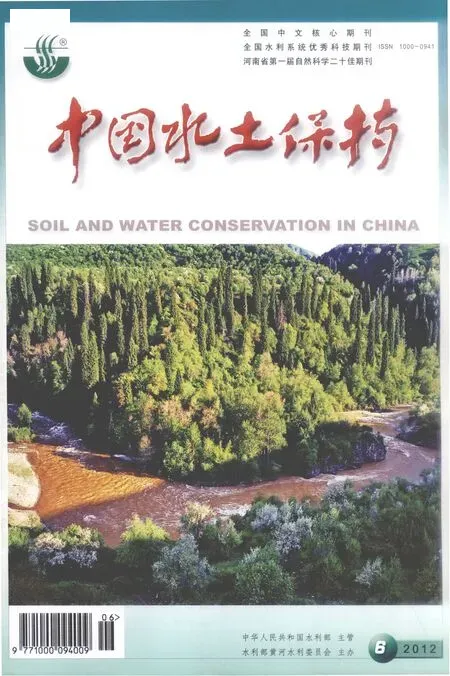生態清潔小流域建設現狀與研究展望
李建華,袁 利,于興修,劉前進
(1.山東師范大學人口資源與環境學院,山東濟南250014;2.臨沂大學資源環境學院山東省水土保持與環境保育重點實驗室,山東臨沂276005;3.淮河水利委員會淮河流域水土保持監測中心站,安徽蚌埠233000)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以水土資源治理為核心的小流域綜合治理已難以適應人們對生態環境的新要求,同時,為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水利部于2006年提出建設生態清潔小流域的新思路,生態清潔小流域的研究與實踐空前活躍。本文簡要回顧了生態清潔小流域研究的進展,分析了不同地區生態清潔小流域構建的特點,探討了生態清潔小流域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進一步加強研究與實踐的相關建議。
1 中國生態清潔小流域建設的背景
1.1 小流域綜合治理的發展歷程
自然與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使學者對小流域的概念以及功能有著不同的認識,其治理措施也有差別,國內對小流域綜合治理的研究與實踐主要分為4 個階段[1-2]。
1.1.1 萌芽與探索階段(1950—1979年)
這一階段探索了許多有效的小流域治理方法。20 世紀50年代初,在黃土高原地區,以支毛溝為單元,利用工程與生物措施相結合的方法對小流域進行整治,形成了小流域綜合治理的雛形。1956年黃河水利委員會肯定并推廣了“以支毛溝為單元綜合治理”模式。20 世紀60年代,水土保持工作以基本農田建設為主要內容,把水、壩、灘地和梯田確定為治理目標,但治理措施的配置比較分散。到20 世紀70年代中期,通過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逐步認識到應以小流域為單元進行綜合整治。
1.1.2 以小流域為單元的綜合治理階段(1980—1990年)
20 世紀80年代初,水利部把“小流域綜合治理”作為一條重要經驗進行推廣,并制定了《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辦法(草案)》,我國的水土保持工作從此進入到以小流域為單元的綜合治理新階段。與此同時,國家確定在黃河、長江等六大流域及水土流失嚴重的8 片區域開展小流域綜合治理試點工作。到80年代末,小流域綜合治理已經成為我國治理水土流失與發展農村生產的主要形式。
1.1.3 預防為主,依法綜合治理階段(1991—2005年)
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水土保持工作進入法制化階段。1993年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強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強調水土保持是一項基本國策。1997年4月國務院召開全國水土保持第六次會議,對跨世紀水土保持工作進行了部署。這一時期水土保持工作進一步深化,在以戶承包治理小流域的基礎上,先后提出了以經濟效益為中心、治理與開發相結合、小流域治理同區域經濟發展相結合的思路,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治理開發模式。
1.1.4 生態清潔小流域治理新階段(2006年至今)
2006年1月,水利部在北京召開生態清潔型小流域治理工作座談會,提出了新時期生態清潔型小流域治理的新要求:從經濟快速發展與人們對改善生態環境的迫切要求出發,在指導思想上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把水生態環境、人居環境、景觀建設、產業結構等內容引入到小流域綜合治理當中。2006年下半年,全國30 個省(市、區)的81 個縣實施了生態清潔小流域試點工程,推動了生態清潔小流域建設進一步發展。
1.2 生態清潔小流域的概念
生態清潔小流域是指以流域為單元,統一規劃,綜合治理,治理措施與當地景觀相協調,遵循自然規律和生態法則,基本實現流域內資源的合理利用和優化配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3]及生態系統良性循環。
生態清潔小流域作為小流域綜合治理的新發展,是小流域綜合治理在內涵上的深化與提升。它以流域內的水、土地、生物等資源的承載力為基礎,以調整人為活動為重點,抓住“生態”和“清潔”兩個核心要素,建立政府主導、公眾參與的互動機制,強調統一規劃、因地制宜、分步實施、穩步推進的原則[4]。生態清潔小流域作為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共同組成的三維復合系統,其研究涉及到系統論、生態經濟學、景觀生態學、可持續發展理論、水土保持學理論[5]以及生態系統控制論[6]等理論。
2 中國生態清潔小流域建設現狀
2.1 建設模式
自然、經濟與技術等條件的不同使不同地區生態清潔小流域建設模式各異,其中典型的建設模式有如下幾種。
2.1.1 “三道防線”治理模式
這種模式源于北京地區。為解決水資源缺乏與用水量大、水污染嚴重之間的矛盾,北京市確定了以“保護水源”為核心的小流域綜合治理理念,通過建立小流域試點工程,構筑了“生態修復區、生態治理區、生態保護區”的“三道防線”治理模式[7]。
2.1.2 “三層次、四防區”治理模式
這種模式源于黑龍江省延壽縣國家生態清潔型小流域試點工程。該模式的基本特點是,按照“山坡、村莊、河道”三個層次進行整體規劃,確定“生態修復、綜合治理、生態農業、生態保護”四片防治區域,有針對性地配置生態林草地建設、坡耕地治理、禽畜舍改造、清潔能源建設以及溝道工程等措施[8-9]。
2.1.3 以水源保護為核心、面源污染控制為重點治理模式
此種模式源于距南水北調核心水源區丹江口水庫直線距離僅6 km 的湖北省丹江口市胡家山小流域。為切實保護好丹江口水庫水質,提出了“生態修復、生態治理、生態緩沖”的治理思路,堅持分區防治,確定生態農業、村落面源污染控制和科技示范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在面源污染控制上突出“荒坡地徑流控制、農田徑流控制、村莊面源污染控制、傳輸途中控制、流域出口控制”的五級防護模式[10]。
2.1.4 以安全為重點的小流域綜合整治治理模式
此種模式在生態安全問題嚴重的南方山區以及黃土高原地區最為典型。該模式針對山區山洪與地質災害頻繁、水土流失與面源污染嚴重,人民的生命與財產受到威脅的實際,確立了“安全、生態、發展、和諧”的治理目標,把山洪與地質災害防治納入小流域治理范疇。
2.2 建設措施與技術體系
生態清潔小流域的治理措施與技術,歸納起來主要有工程、耕作、生物等方面的措施及相應的技術[7-10]。
各地建設生態清潔小流域的措施與技術有著明顯的不同,重要水源地,例如北京市等重要城市的周邊山區,在措施布局上多形成以水源地保護為核心,以污水治理為重點,溯源治污,村莊配套,農業、工業綜合整治的技術路線;在農業比重大、地形平緩的東北平原地區,措施布局上多形成以農業面源污染控制、河流水質保護為核心,在保護原有生態環境的基礎上,改變農業結構與耕作方式的技術路線;在地形復雜、溝谷眾多,侵蝕嚴重的西南以及黃土高原地區,措施布局上多形成以流域防災減災、保護土地資源為核心,以災害預警,河、溝、坡面綜合整治,面源污染控制為重點的技術路線。
2.3 研究方法
新技術與新方法的應用,為定量研究生態清潔小流域及其科學治理提供了保障。
在信息提取方面,目前多利用RS 獲取小流域自然要素指標,借用RS 與GIS 軟件模塊分析小流域特征。祁生林[5]利用RS 與GIS 分析密云縣的降雨因子、植被因子、地形因子、土地利用狀況與地貌部位,提取植被蓋度、坡度、土地利用類型與地形地貌信息,為“三道防線”的劃分提供了科學依據。胡曉靜等[11]也結合GIS 工具,快速劃分小流域地塊,提高了基礎圖件的準確性和工作效率。
在小流域演化規律與預測研究方面,主要是建立模型與模擬。數學模型既可以分析流域內各要素間的相互關系從而優化治理方案,也可以定量反映小流域治理效果。在方案優化方面,陳建剛等[12]采用多目標規劃方法,建立數學模型,優化土地利用結構,合理配置水土保持措施,治理與開發相結合,探索出了小流域綜合治理最佳模式的建立方法。葉芝菡等[13]把WMS流域模擬系統引用到生態清潔小流域的規劃設計當中,為流域水源保護工程建設提供了科學依據。在治理效果評價方面,馬騫等[14]通過建立多目標決策灰色關聯投影模型,評價了沂蒙山區平邑縣國家水土保持生態修復試點工程生態環境的變化,提高了小流域生態效益評價的精度。
建立流域決策與管理系統,是提高生態清潔小流域建設與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徑。饒良懿等[15]將專家系統與地理信息系統、決策支持系統等技術相互集成,研發了包括6 個功能模塊的小流域綜合治理智能決策信息管理系統,為北京山區小流域的綜合治理以及可持續發展評價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工具;劉高煥等[16]立足黃土高原小流域的治理,開發了小流域管理與決策支持系統,有力地服務于水土保持的現代化管理和小流域綜合治理。
2.4 效益監測與評價
作為社會、經濟與環境組成的三維復合系統,需要從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三方面建立生態清潔小流域效益監測與評價指標體系,以進行綜合性與動態性的監測與評價。
2.4.1 針對建設目標的監測與評價指標體系
為便于生態清潔小流域建設的考核與完善,許多地區根據建設目標建立監測與評價指標體系。如北京市根據小流域建設的總體目標[17],建立了小流域出口地表水環境質量、土壤侵蝕強度、林草面積占宜林宜草的面積比、化肥施用強度、農藥施用量、溝道形態特征及水質、村莊生活污水處理率、工業污水達標排放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規模養殖污水處理率、防洪達標率等11 項指標。
2.4.2 水生態環境監測與評價指標
吳敬東等[18-19]在吸收傳統小流域水土保持監測與水環境、水生態技術發展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生態清潔小流域水生態環境監測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分為水土流失與面源污染狀況、河流健康狀況和點源污染狀況3 個層次、17 個監測指標。
2.4.3 工程建設監測與評價指標
馬豐豐等[20]根據小流域治理、生態修復、河道整治、人居環境整治、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水土流失和水環境監測等7 項工程要求,采用專家咨詢、理論分析、頻度分析與層次分析等方法,從生態修復、生態治理和生態保護方面構建了生態清潔小流域評價指標體系,共涉及植被覆蓋率、樹種結構、林種結構、徑流系數等20 個指標。
3 生態清潔小流域建設與研究展望
3.1 加強生態清潔小流域的理論體系與構建技術研究
生態清潔小流域建設與研究起步較晚,目前沒有明確的建設標準、統一的管理與技術規范;治理模式的地域特色不突出,多采取工程、耕作、生物等宏觀水土保持措施,構建技術單一,需進一步研究。
3.2 完善監測與評價指標體系
現有的監測與評價指標體系,多采用土壤侵蝕、面源污染、植被覆蓋、水環境監測、生物多樣性等生態環境指標,較少涉及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指標,缺乏對生態清潔小流域整體性的評價。因此,生態清潔小流域監測與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需要進一步加強。
3.3 健全生態清潔小流域構建的投入與產出機制
生態清潔小流域的建設大多由政府與水利部門投入資金,如何引入社會資本,使投入主體多元化是重要的探索領域;如何發揮試點小流域的示范與帶動作用,提高治理的效益等,是未來生態清潔小流域研究與實踐的重點之一。
4 結 語
與資源環境研究領域其他問題一樣,生態清潔小流域研究與實踐的最大挑戰來自于流域系統本身的復雜性。生態清潔小流域作為“社會-經濟-環境”三維復合系統,其構建涉及內部眾多要素及其相互關系,而流域本身是一個不斷與外部進行信息和能量交流的開放系統,這就增加了生態清潔小流域構建的難度,但這種復雜性也是學術研究的突破點所在。中國河流眾多,水系發達,山地丘陵區小流域的數量多、類型全,應在借鑒國外成功的小流域治理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建立完整的理論體系,系統開展生態清潔小流域監測,加強生態清潔小流域構建技術、投入與產出機制研究;選擇重要城市水源地、水土流失潛在風險高等問題突出的地區,例如北方土石山區等,進行重點研究,建設一批科技含量高、示范作用強的典型小流域,使我國生態清潔小流域研究向著更加綜合、更加完善的方向發展。
[1]劉震.我國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回顧與展望[J].中國水利,2005(22):17-20.
[2]王雪.京郊山區農村環境綜合整治模式研究[D].北京:北京林業大學,2008.
[3]畢小剛,楊進懷,李永貴,等.北京市建設生態清潔型小流域的思路與實踐[J].中國水土保持,2005(1):18-20.
[4]周萍,文安邦,賀秀斌,等.三峽庫區生態清潔小流域綜合治理模式探討[J].人民長江,2010,41(21):85-88.
[5]祁生林.生態清潔小流域建設理論及實踐[D].北京:北京林業大學,2006.
[6]陳新軍,田里,張望林.基于“生態系統控制論”原理的小流域綜合治理對策研究[J].中國水土保持,2010(5):58-60.
[7]韓富貴,卜振軍,王娟,等.密云縣建設生態清潔小流域的實踐[J].水土保持應用技術,2007(2):37-38.
[8]趙艷娥,趙春佳,趙再新.黑龍江省生態清潔型小流域水環境建設探索[J].黑龍江水利科技,2009,37(6):90.
[9]劉陪封,鞏徳武,段景洪.生態清潔型小流域治理模式在水土流失治理中的應用[J].黑龍江水利科技,2010,38(3):226.
[10]賈鎏,王永濤.丹江口庫區胡家山生態清潔小流域治理的探索和實踐[J].中國水土保持,2010(4):4-5.
[11]胡曉靜,葉芝菡,常國梁,等.基于ArcGIS 的生態清潔小流域地塊劃分及應用[J].北京水務,2009(z2):37-39.
[12]陳建剛,侯旭峰,吳敬東.北京北部山區石匣小流域綜合治理模式研究[J].北京水利,2002(6):18-20.
[13]葉芝菡,段淑懷,吳敬東,等.流域水文模型在生態清潔小流域規劃中的應用[J].中國水土保持,2007(9):12-13.
[14]馬騫,于興修,楊子峰,等.基于多目標決策灰色關聯投影法的水土保持生態修復生態效益動態評價[J].水土保持研究,2009,16(4):100-103.
[15]饒良懿,謝寶元,余新曉,等.北京山區小流域綜合治理智能決策信息管理系統的研制和開發[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2003,25(1):43-47.
[16]劉高煥,朱會議,蔡強國,等.小流域綜合管理信息系統集成研究[J].地理研究,2002,21(1):25-33.
[17]劉大根,段淑懷,李永貴,等.北京《生態清潔小流域技術規范》的編制[J].中國水土保持,2008(7):24-26.
[18]吳敬東,葉芝菡,梁延麗,等.生態清潔小流域水生態環境監測指標體系初探[J].中國水土保持,2007(9):8-9.
[19]吳敬東,段淑懷,葉芝菡,等.蛇魚川生態清潔小流域水生態環境監測布設研究[J].水土保持通報,2009,29(2):70-72.
[20]馬豐豐,田育新,羅佳,等.生態清潔小流域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J].湖南林業科技,2010,37(3):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