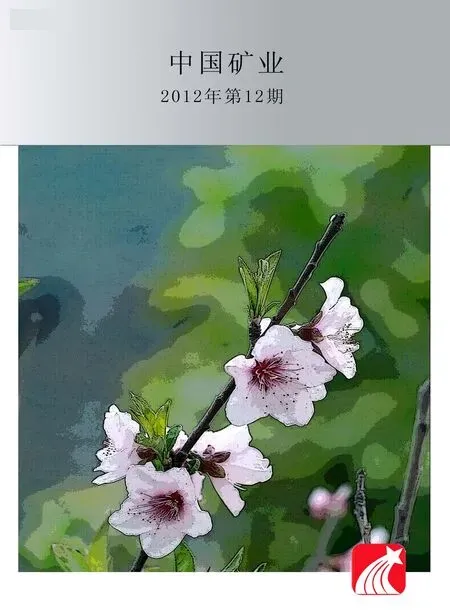可持續(xù)發(fā)展視野下我國礦業(yè)權(quán)之重構(gòu)研究
袁 俊
(成都理工大學(xué)文法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0059)
目前,我國尚未形成一個有利于促進礦產(chǎn)資源合理開發(fā)的系統(tǒng)完善的的法律體系,現(xiàn)有的法律法規(guī)之間也存在明顯沖突,這不但使得礦業(yè)權(quán)流轉(zhuǎn)出現(xiàn)了諸多問題,更使得礦業(yè)權(quán)人基于制度的考慮,追求短期利益,無心或無法更多關(guān)注資源的合理開發(fā)及礦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而對礦業(yè)權(quán)概念界定模糊及科學(xué)嚴(yán)謹(jǐn)?shù)那啡保彩切纬梢陨蠁栴}的重要誘因之一。
1 概念的厘清
對于礦業(yè)權(quán)的概念,我國法律并未明確界定,目前它僅止于學(xué)術(shù)概念。多年來,學(xué)術(shù)界對于該概念的爭論非常激烈,《物權(quán)法》的頒布也未能定紛止?fàn)帯F鹣龋瑢W(xué)者們多從礦業(yè)權(quán)的性質(zhì)入手對其進行界定,比如有學(xué)者將礦業(yè)權(quán)定義為“我國用益物權(quán)中的一個獨立類型”,有人將礦業(yè)權(quán)界定為包括礦產(chǎn)資源所有權(quán)的權(quán)利[1],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礦產(chǎn)資源權(quán)與礦業(yè)權(quán)組成礦權(quán),而礦業(yè)權(quán)則由探礦權(quán)和采礦權(quán)組成[2]。之后,學(xué)者們的定義多體現(xiàn)了礦業(yè)權(quán)的復(fù)合性——礦業(yè)權(quán)為“依法取得”(行政許可之公權(quán)性質(zhì))“進行勘察或開采”并獲得“礦產(chǎn)品”或者“地質(zhì)資料、礦物及其伴生礦”的權(quán)利(物權(quán)之私權(quán)性質(zhì))。甚至有學(xué)者明確指出礦業(yè)權(quán)是一個復(fù)雜概念,是一個權(quán)利束,是由一系列相關(guān)權(quán)利組合而成的[3]。《物權(quán)法》頒布之后,對礦業(yè)權(quán)的研究出現(xiàn)分流。一些學(xué)者們在肯定礦業(yè)權(quán)前提下著重對“復(fù)合性”進行研究,而另一些學(xué)者則公開質(zhì)疑我國礦業(yè)權(quán)概念,認(rèn)為以礦業(yè)權(quán)作為一個整體來確定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探礦權(quán)和采礦權(quán)的法律屬性缺乏科學(xué)性[4]。還有學(xué)者主張以礦產(chǎn)權(quán)、特許權(quán)和開發(fā)權(quán)替代傳統(tǒng)的探礦權(quán)、采礦權(quán),礦業(yè)權(quán)則應(yīng)當(dāng)撤銷[5]。
伴隨著礦業(yè)權(quán)概念之爭的是礦業(yè)權(quán)的法律屬性之爭。在《物權(quán)法》頒布之前,學(xué)界關(guān)于礦業(yè)權(quán)性質(zhì)的觀點主要有:債權(quán)說(江平,1991)、準(zhǔn)物權(quán)說(崔建遠,2003、張振凱,2003、李顯冬,2006)、用益物權(quán)說(屈茂輝,1999、房紹坤,2003、潘婉雯等,2003、余振國,2004、劉權(quán)衡,2006)、特許物權(quán)(王利明,2001、楊立新,2004)、特別物權(quán)(陳華彬,2004)以及物權(quán)取得說(張俊浩,2000)、探礦權(quán)知識產(chǎn)權(quán)說(李顯冬,2006)、采礦權(quán)自物權(quán)說(肖國興等,2003、王世軍,2005)等。雖然之后《物權(quán)法》將礦業(yè)權(quán)相關(guān)規(guī)定放在用益物權(quán)部分,但對礦業(yè)權(quán)法律屬性的質(zhì)疑與探討并未因此而停止。有學(xué)者指出礦業(yè)權(quán)屬準(zhǔn)用益物權(quán)[6],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探礦權(quán)系物權(quán)化的債權(quán);而采礦權(quán)系債權(quán)與所有權(quán)的組合體[4]。
對礦業(yè)權(quán)概念及其法律屬性的爭論多年來之所以未能消減,主要是因為礦業(yè)權(quán) “行政許可”之公權(quán)性質(zhì)與“物權(quán)”之私權(quán)性質(zhì)的捆綁導(dǎo)致內(nèi)在沖突,而“用益物權(quán)”的法律屬性界定也因無法有效解釋探礦權(quán)、采礦權(quán)的許多特性而顯得疑點重重,如此模糊而欠嚴(yán)謹(jǐn)?shù)闹贫仍O(shè)計自然備受學(xué)者們質(zhì)疑。
2 現(xiàn)行礦業(yè)權(quán)制度相關(guān)問題解析
2.1 公權(quán)與私權(quán)相捆綁導(dǎo)致的沖突與問題
依據(jù)我國現(xiàn)行規(guī)定,礦業(yè)權(quán)的取得、勘查和開發(fā)、轉(zhuǎn)讓、作價出資、抵押、合作開發(fā)等諸多環(huán)節(jié)都要受到不同程度行政強制規(guī)定的限制。而礦業(yè)權(quán)的“物權(quán)”性質(zhì)又決定了其對正常順利流通的需求。由此形成了沖突格局,并引發(fā)了一系列問題。
2.1.1 國家的“雙重身份”所帶來的問題
在礦業(yè)權(quán)出讓過程中,國家擁有礦產(chǎn)資源所有權(quán)權(quán)利人和國家行政事務(wù)管理者雙重身份,這使其很有可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標(biāo)驅(qū)動下,背離市場配置規(guī)律而專注于短期經(jīng)濟利益,最終偏離資源合理利用的既定目標(biāo)。另外,國家作為礦產(chǎn)資源所有者的權(quán)益由國務(wù)院代為行使,但諸多管理責(zé)任、礦產(chǎn)資源開發(fā)中環(huán)境污染治理、生態(tài)環(huán)境恢復(fù)等成本卻基本由地方政府來承擔(dān),由此造成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利益沖突。這使得地方政府或怠于管理,或?qū)Y源的實際控制權(quán)進行條塊分割、變管理為占有,甚至巧立名目、向礦業(yè)企業(yè)收取各種費用等種種怪象。而由此形成的利益關(guān)系則嚴(yán)重影響了政府對礦山企業(yè)的違規(guī)行為處理的執(zhí)法公正性,亂采濫采、浪費行為無法得到及時遏制,進而影響了礦產(chǎn)資源合理開發(fā),造成了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
2.1.2 采礦權(quán)人“物權(quán)”利益保障問題
“行政許可”之公權(quán)性質(zhì)與“物權(quán)”之私權(quán)性質(zhì)相捆綁,使得采礦權(quán)人在取得了開采該礦產(chǎn)資源的資格的同時,也取得礦產(chǎn)資源的財產(chǎn)權(quán)利。但法律并未規(guī)定礦產(chǎn)資源之物權(quán)從國家讓渡給企業(yè)的轉(zhuǎn)讓過戶程序,企業(yè)物權(quán)并無物權(quán)效力及排他性支配權(quán),并造成現(xiàn)實中采礦權(quán)人權(quán)益不穩(wěn)定并無法自保的現(xiàn)實問題。一旦礦山企業(yè)被吊銷采礦許可證,由于企業(yè)財產(chǎn)暗含在采礦許可證中,因此被處罰者只能空手退出市場,企業(yè)的剩余礦產(chǎn)資源以及資本投入都只能留在市場里。同樣在我國為根治礦山企業(yè)散、亂、多現(xiàn)象的全國礦產(chǎn)資源整合中,被整合企業(yè)亦遭遇了采礦許可證由政府強制吊銷、企業(yè)的礦產(chǎn)資源物權(quán)和其他合法財產(chǎn)被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強行收繳的境遇。而對于擬接受礦業(yè)權(quán)抵押的債權(quán)人及金融機構(gòu)而言,以上風(fēng)險已是其接受礦山企業(yè)擔(dān)保的重大障礙[7]。如此制度設(shè)計,必然造成采礦權(quán)人對所享物權(quán)的安全性和穩(wěn)定性產(chǎn)生疑慮,對開采對象預(yù)期利益的取得缺乏安全感,無心對礦山安全和環(huán)境保護進行成本投入,更無心技術(shù)創(chuàng)新,而急功近利、挑肥揀瘦,置礦產(chǎn)資源的合理利用、礦山的環(huán)境保護于不顧的行為也必將層出不窮。
2.2 《物權(quán)法》“用益物權(quán)”法律屬性界定帶來的問題
2.2.1 理論上缺乏解釋力
僅占有、使用、收益而不能處分,權(quán)利消滅后標(biāo)的物應(yīng)返還所有人,這是用益物權(quán)的本質(zhì)特征。就探礦權(quán)而言,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探礦權(quán)的客體是什么,它是否屬物權(quán),有學(xué)者認(rèn)為礦產(chǎn)資源是礦業(yè)權(quán)的唯一客體,但在勘探后無礦的情況下如何界定其物權(quán),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特定礦區(qū)或者工作區(qū)的地下土壤和其中所賦存的礦產(chǎn)資源是礦業(yè)權(quán)的客體[8]。但礦區(qū)例行縮減與懲罰性縮減制度使得“特定的礦區(qū)或者工作區(qū)”出現(xiàn)不確定性,勘探成功與否使得探礦權(quán)之客體出現(xiàn)變數(shù),這必然會違反物權(quán)法“客體特定”及“一物一權(quán)”原則[4]。其次,勘探行為是否可以界定為“使用”,顯然不是,那么探礦權(quán)人是否有“收益”,理論上,探礦權(quán)人的利益一方面存在于自行銷售勘查中按照批準(zhǔn)的工程設(shè)計施工回收的礦產(chǎn)品,另一方面則體現(xiàn)在對該勘查作業(yè)區(qū)采礦權(quán)的優(yōu)先取得。但現(xiàn)實中以上礦產(chǎn)品非常有限,遠遠不能彌補勘探人的投入,甚至還存在勘探后無礦的情形。因此,礦業(yè)權(quán)人取得探礦權(quán)的最為實質(zhì)的目的并非用益權(quán)所側(cè)重的“使用”和“收益”,而是優(yōu)先取得采礦權(quán),因此探礦權(quán)是否為用益物權(quán)是值得商榷的。而采礦權(quán)的行使本身就是一個對礦產(chǎn)資源消耗的過程,采礦權(quán)人的本質(zhì)利益是獲得礦產(chǎn)品并通過交換取得收益,無法滿足用益物權(quán)消滅后標(biāo)的物以原狀返回到所有權(quán)人的條件。因此,將其界定為用益物權(quán)更是缺乏基本法理依據(jù)。
2.2.2 實踐中的消極影響
將采礦權(quán)確定為用益物權(quán),導(dǎo)致開采處分行為被異化成用益行為,這是我國礦產(chǎn)資源補償費偏低的根源之一。理論上, 我國的礦產(chǎn)資源補償費應(yīng)當(dāng)是因為資源開采過程中有實際消耗,而補償給資源所有者的。而現(xiàn)實是,一方面礦產(chǎn)資源被不斷消耗,另一方面資源補償卻按用益價格計征,而且如此低的支付額度還在銷售后收取,這嚴(yán)重?fù)p害了國家作為資源所有者的利益。用益與處分之間價格差所形成的溢價價值,也吸引眾多投機者想方設(shè)法跑馬圈地;作為理性經(jīng)濟人,采挖人很清楚與其花成本去采邊料、采礦層薄、難度較大的礦產(chǎn)追求高回采率,不如棄貧采富,吃“菜心”以追求短期經(jīng)濟利益。如此便加劇了礦產(chǎn)資源浪費、開采回采率低、環(huán)境污染和生態(tài)破壞等現(xiàn)象的發(fā)生。
3 理論重構(gòu)與制度設(shè)計
3.1 重構(gòu)礦業(yè)權(quán)
毋庸置疑,以上問題產(chǎn)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礦業(yè)權(quán)界定不清是重要誘因。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對礦業(yè)權(quán)相關(guān)理論進行重構(gòu)。首先,礦業(yè)權(quán)自身存在的問題已使其無法勝任探礦權(quán)、采礦權(quán)上位概念的角色,即便其已被立法及學(xué)界廣泛接受,也還是有必要討論將其放置一邊轉(zhuǎn)而延續(xù)《礦產(chǎn)資源法》將探礦權(quán)與采礦權(quán)分立的做法,以重點突出探礦權(quán)和采礦權(quán)。其次,應(yīng)厘清探礦權(quán)的性質(zhì)。目前,國家為轉(zhuǎn)移勘探風(fēng)險,以賦予探礦權(quán)人自行銷售勘查中按照批準(zhǔn)的工程設(shè)計施工回收的礦產(chǎn)品以及對該勘查作業(yè)區(qū)采礦權(quán)的優(yōu)先取得權(quán)條件吸引民間投資,繼而收取勘探費,實際上是將礦產(chǎn)資源轉(zhuǎn)讓行為摻雜在了勘探活動當(dāng)中,導(dǎo)致探礦權(quán)復(fù)雜化,并造成了現(xiàn)實中的諸多問題。所以,應(yīng)當(dāng)還原探礦權(quán)的本質(zhì)。國家與勘探者之間應(yīng)當(dāng)是委托、受托關(guān)系,應(yīng)是國家付費、勘探企業(yè)服務(wù)的關(guān)系。探礦中因勘探活動而產(chǎn)生的風(fēng)險應(yīng)全部由作為所有者的國家承擔(dān)。有學(xué)者主張將探礦權(quán)界定為“債權(quán)”[4]。第三,應(yīng)明確國家出讓給采礦人礦產(chǎn)資源的實際對價。國家應(yīng)與采挖人簽訂轉(zhuǎn)讓礦產(chǎn)資源所有權(quán)合同,協(xié)商形成該所有權(quán)符合市場規(guī)律的物權(quán)對價(而非現(xiàn)在所規(guī)定的在采挖之后依據(jù)銷售價格計征礦產(chǎn)資源補償費),之后采礦人采挖所獲得的礦產(chǎn)品完全由其自行處置(關(guān)乎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具有重大影響的礦物除外)。此時作為受讓人的礦主由于付出了對價取得了所有權(quán),并產(chǎn)生了避免浪費的原動力。這不但可以從實質(zhì)上改變?nèi)缃竦V產(chǎn)資源費偏低、國家所有者利益無從體現(xiàn)的現(xiàn)象,還可從很大程度上降低跑馬圈地、采富棄貧、浪費資源、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等一系列問題的產(chǎn)生。
3.2 進一步調(diào)整國家的身份定位
鑒于前述,國家在礦業(yè)市場需要強化的是所有者、管理者身份,而經(jīng)營者身份則應(yīng)淡化。所有者身份強化的主要方向便是形成合理真實的礦產(chǎn)資源出讓對價,避免國有資產(chǎn)的流失與浪費。而管理者身份的強化則應(yīng)關(guān)注整個礦業(yè)市場是否規(guī)范、安全,礦產(chǎn)資源的開發(fā)利用是否關(guān)注社會利益的實現(xiàn)、開發(fā)利用的合理性及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由此,應(yīng)充分強化以下管理。
第一,強化科學(xué)規(guī)劃。國家應(yīng)依據(jù)礦產(chǎn)資源賦存情況、地表土地使用情況等進行全局規(guī)劃,區(qū)分開采區(qū)、限制開采區(qū)和禁止開采區(qū)。并將礦產(chǎn)資源按礦種和地理位置進行劃分,國土資源部的管轄范圍確定在石油、天然氣、鈾礦等重要資源上,而其他礦種則由所在地省級國土資源管理機構(gòu)管理。地縣設(shè)置由省級國土資源管理機構(gòu)垂直管理的派出機構(gòu)實施管理,避免地方政府和地方企業(yè)的干擾與影響[9]。
第二,規(guī)范出讓行為,嚴(yán)格審查受讓條件。立法應(yīng)當(dāng)明確:地質(zhì)報告應(yīng)準(zhǔn)確地表述對地質(zhì)勘探成果的解釋以及實現(xiàn)的目標(biāo),這是礦產(chǎn)資源合理開發(fā)利用最基礎(chǔ)的信息來源,必須從制度上預(yù)先保障合理開發(fā)的科學(xué)性。在特許審批時,除對一般法定條件進行審查外,特許部門還應(yīng)著重審查環(huán)境報告、礦床地質(zhì)報告、水文地質(zhì)報告、工程地質(zhì)報告和礦床開采計劃。同時,應(yīng)實行礦業(yè)權(quán)申請專家調(diào)查制度,由專家進行實地勘測形成具體結(jié)論,而后才能作出授權(quán)與否的決定。另外,以實際價值科學(xué)界定礦產(chǎn)資源出讓價值,支付對價的權(quán)利人的節(jié)約利益與社會利益相一致,激勵開采者提高回采率,防止采富棄貧行為急功近利的浪費現(xiàn)象。
第三,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利益。礦產(chǎn)資源有償使用收益分配,應(yīng)向地方適當(dāng)傾斜。鑒于目前礦業(yè)權(quán)價款是按國家兩成,省、自治區(qū)八成比例分配,同時在國土資源部提交的調(diào)整礦產(chǎn)資源補償費費率及分配方案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成比例也是同一比例[7],故建議與國家國防和經(jīng)濟安全密切相關(guān)的重要礦種(石油、天然氣、鈾礦等),亦按此比例分配。
第四,規(guī)范和培育中介機構(gòu)。中介機構(gòu)的參與,會從一定程度上遏制公權(quán)力過多干預(yù)礦產(chǎn)資源配置所帶來的問題。鑒于我國目前的礦業(yè)權(quán)流轉(zhuǎn)中介機構(gòu)多為事業(yè)單位,民間中介機構(gòu)尚不發(fā)達,因此培育與規(guī)范中介機構(gòu)一方面要將礦業(yè)權(quán)中介機構(gòu)逐漸與政府脫鉤,同時以制度激勵民間中介機構(gòu)的設(shè)立,并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規(guī)予以規(guī)范。
4 結(jié)語
如前所述,礦業(yè)權(quán)的重構(gòu)與國家的合理定位是實現(xiàn)礦產(chǎn)資源合理開發(fā)利用的重要前提。厘清以上問題之后,使得國家公權(quán)力存在于礦產(chǎn)資源所有、基于對礦產(chǎn)資源生態(tài)價值、礦業(yè)市場的培育與規(guī)范管理及國家安全等公共利益領(lǐng)域,而探礦權(quán)、采礦權(quán)人的權(quán)益存在于基于債權(quán)及礦產(chǎn)資源受讓后的所有權(quán)等私權(quán)領(lǐng)域,兩者之間的界限得以明晰,這是實現(xiàn)礦產(chǎn)資源合理開發(fā)利用、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從而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條件。
[1]王啟富.法律辭典[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2]彭萬林.民法學(xué)[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2.
[3]戴永生.國內(nèi)外礦業(yè)權(quán)之法律屬性分析[J] .世界有色金屬,2006(2):36-38.
[4]朱曉勤,溫浩鵬.對礦業(yè)權(quán)概念的反思[J].中國地質(zhì)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 2010(1):81-86.
[5]康紀(jì)田.礦業(yè)法論 [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6]李顯冬,劉志強.論礦業(yè)權(quán)的法律屬性[J].當(dāng)代法學(xué),2009(2):73-75.
[7]蔣文軍.礦業(yè)權(quán)交易法律制度與實務(wù)操作 [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
[8]崔建遠.準(zhǔn)物權(quán)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9]鮑榮華.對我國礦業(yè)權(quán)管理制度建設(shè)的幾點建議[J].國土資源情報,2007(1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