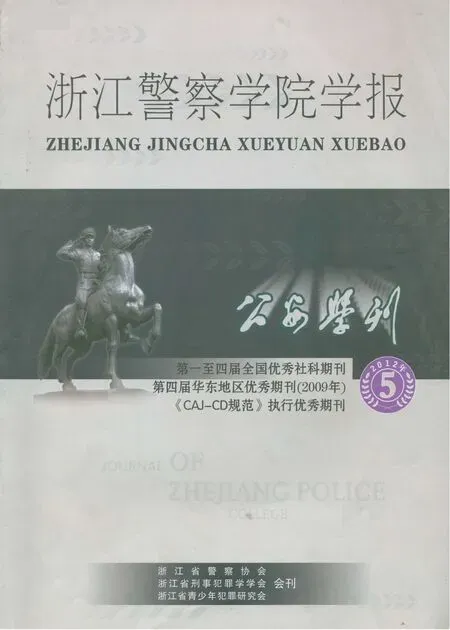犯罪統計:刑事政策定量研究的基礎(下)
——兼評美國兩大犯罪統計模式
□劉 濤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江蘇 南京 210046)
犯罪統計:刑事政策定量研究的基礎(下)
——兼評美國兩大犯罪統計模式
□劉 濤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江蘇 南京 210046)
犯罪統計;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刑事政策;UCR和NCVS兩大犯罪統計模式
(接上期)相對而言,基于被害人自陳性資料形成的NCVS等犯罪統計在避免犯罪黑數方面,是優于UCR等基于警務系統資料的統計的。從某種意義上說,NCVS等犯罪統計或犯罪報告的出現,就是因為在犯罪研究中,學者越來越意識到官方的警務犯罪統計存在巨大的犯罪黑數問題。公民在遭受犯罪侵害后,有很大一部分并沒有訴諸公共權力機構,有的學者就指出:“人口調查局做的調查給那些呼吁嚴格立法的人一劑清醒劑,調查結果顯示大量被害人并沒有訴諸法律。2004年,美國50%的暴力犯罪被害人和61%的財產犯罪被害人沒有向警方報案。設想一下有半數的人生病而不去醫院看病的情形。”(20)而上述的資料,來源于NCVS等被害人調查所公布的實證數據。其實,由官方出資進行的NCVS調查設立的初衷就是政府也意識到大量的犯罪黑數問題,而運用UCR等基于警務系統的統計是無法反映這些潛在的犯罪被害情況的。(21)雖然在當時沒有如現在這般確切的實證資料可以證實問題的嚴重性,但是正如同社會上的一般人,政府和學者對于犯罪與向警方報案存在巨大差異也有所體會,NCVS的設立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直觀的感受,而多年來的NCVS報告也逐步證實了這一點。
當然,這并不是說基于被害人報告的犯罪統計就不存在犯罪黑數問題。從定性研究來看,犯罪黑數包括應當記錄而沒有記錄的社會犯罪事件和嚴重程度沒有達到犯罪的標準而被誤認為是犯罪的記錄。學者們通常關注的是真實犯罪被害情況與警方接警與破案之間的巨大數量差異,尤其是前者的數量明顯高于后者,但有時也忽視了訪談式的數據收取可能造成的被訪者主觀夸大被害情況的可能性。(22)此外,被害統計還存在的問題有:a.由于NCVS是建立在以抽樣樣本的基礎上,相對于UCR在樣本數上是遠遠不能相比的,對于能否反映真實的全國整體犯罪情況也是值得懷疑的。b.NCVS以家庭為單位,涵蓋了許多對12歲以上的未成年人的調查,問卷的設計在某些方面沒有考慮到未成年人理解能力與成年被訪者的差異。(23)c.由于基于被害調查的犯罪統計為了求得一段時期內的犯罪變化數據,對于同一戶家庭,會進行多次的被害調查,熟悉了調查過程的被調查者基于羞愧或者隱私等心理因素,而瞞報被害情況,面談與電話詢問所造成的對于被訪談者參與意愿的影響,都會進而造成對于此類調查的可信度懷疑與犯罪黑數現象發生的可能性。(24)
總體而言,以UCR統計為代表的基于案件資料的犯罪統計在統計時間的跨度上,對于美國社會整體的犯罪趨勢描述上擁有較大的優勢;而以被害事件資料為基礎的NCVS等犯罪統計在控制統計犯罪黑數現象、提供學者更為精確的犯罪描述上具有先天的統計方法上和數據收集上的優勢。而兩種犯罪統計模式,在對于內容和所使用的犯罪分類和形式概念上,力求統一,(25)為美國學者的研究和政府部門制定犯罪對策提供最大的便利。目前為止,還沒有見到融合兩種犯罪統計方法的新的犯罪統計模式出現,(26)兩種犯罪統計方式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注定其無法完全融合。也正是由于這樣一種狀態,造成了兩種犯罪統計對于美國犯罪及其刑事司法整體狀況的描述呈現互補的特征,增強了學者和機構對于美國犯罪態勢從不同方面分析的可操作性,最終的效果是學者、政府以及普通民眾對于了解犯罪現象有了更加可靠和全面的資料予以參考。
三、刑事政策研究: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
如前所述,美國兩種犯罪統計的方法經過其自身多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筆者認為,對于犯罪統計的研究,支撐了美國犯罪學研究、社會學研究及其他的相關的社會科學的研究。精確的實證統計為這些社會科學進一步分析社會現象奠定了堅持的基礎。
作為一名刑事法學的研究者,筆者不僅關注犯罪統計在犯罪學領域和社會學領域的應用,也在思考犯罪統計對于刑事法學研究的意義,特別是在刑事政策學的研究中,犯罪統計所能發揮的作用。
(一)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定義。筆者認為,如果想要弄清楚犯罪統計對于刑事政策研究的意義,首先要弄清楚社會科學研究的路徑之別。對于社會科學研究來講,主要可以分為兩種研究路徑: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是指以統計性的社會調查獲得的數據資料為基礎,對社會現象進行量化研究,從而得出具有數量特征的信息成果或研究結論的社會現象研究方法。它也稱為量的研究、量化研究,是源自于自然科學中的一種研究方法。(27)隨著社會學的發展,定量研究也在社會科學中廣泛地開展起來,孔德、涂爾干(28)等社會學的先驅們都十分重視此種研究方法。要得到相對客觀的結論,對于研究的對象就需要進行定量的分析,這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種共識。
定性研究,是指對事物的性質、價值等方面的研究,在其直接的意義上,社會科學中的定性研究強調的是對于個別的、具體的、特殊的社會事件和社會現象的把握,其根本目的卻是在這種具體分析的基礎上掌握社會現象的內在本質、普遍性、重復性、規律性。社會的發展是有其特定的歷史規律的。定性研究的目的就是通過對社會事物的本質性內容進行研究分析,以探索社會存在和發展的規律。定性研究注重從研究者本人內在的觀點去了解他們所看到的世界。它強調在自然情境中作自然式探究,在自然的情境中收集現場發生的事件的資料,最主要的研究工具是研究者本人。因此,研究者自身所恪守的價值理念、思想觀念,構成了定性研究的出發點和立足點,也成為研究的前提假設。也可以說,在社會科學中,定性研究是學者對于社會的“應然”狀態的一種解釋與構建,是將個人所認同的某些價值體系、社會規律融入到對于研究對象的說明上去,定性研究集中體現了研究者對于研究對象的存在意義的理解。
任何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想要獲得一些成就,就不能不意識到兩種研究路徑的區別與各自的意義;任何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想要獲得認可、取得相應的社會實效,就不得不在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兩方面都有所深入。
筆者認為,刑事政策研究作為刑事學的一部分,毫無疑問是一種社會科學的研究,其研究的路徑也就可以被劃分為定性的研究與定量的研究。而犯罪統計的研究,注重的是對于犯罪在特定時空的整體狀況作出價值無涉的整理與分析。在刑事政策及其原理的研究中,犯罪統計是支撐刑事政策定量研究的重要資源,是進行刑事政策定量研究的基礎。
(二)中國刑事政策研究現狀:注重定性研究。
刑事政策,從廣義上說,一切對抗犯罪的策略,都可以稱為刑事政策。不過,作為一門學科,刑事政策應當有其在學術研究上的核心內涵,正如林東茂教授所言:“一個不知核心研究領域的人,只能泛泛地談問題,不會有深挖問題的能力。”(29)所以筆者也同意林東茂教授將刑事政策限定在 “國家運用刑法體系,有效而且合理對抗犯罪的政策”(30)這樣一種狹義的概念之下。
刑事政策研究,就是對國家各種抗制犯罪的立法、司法、行刑政策進行研究,分析其合理性。刑事政策的研究,不能離開科學的分析與判斷,“刑事政策,如果缺乏科學的基礎,則刑事政策只能成為一好事家。須知,刑事政策必須以科學的研究為基礎,始能發生實效。倘僅根據非科學的常識的觀念與判斷,則政策必將空洞無力。”(31)
然而,當前我國的刑事政策研究,注重的是定性研究,對于國家制定的各項對抗犯罪的政策研究,主要依賴于學者自身的價值判斷,對于刑事政策的走向,更多的是從政策的“應然”狀態進行剖析,構建所謂“合理”的政策。傳統中國刑事政策的研究,主要圍繞的是刑事政策的制定運行應當遵循怎樣的原理、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則(如法治原則、民主原則、人道原則等)、刑事政策的價值目標(如公平、正義、效率等)、刑事政策的模式(國家本位、社會本位)展開討論。對于具體犯罪的刑事政策,也是對于一些概念的基本闡釋和邏輯建構(如犯罪化與非犯罪化、刑罰化與非刑罰化、刑罰的輕緩化、被害人保護的意義、社會矯正的本土化等)。
不可否認,當下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法治、民主等現代國家的基本特征還未完全形成,學者在研究中注重對于這些基本價值的呼吁與提倡是有見地的,也是十分必要的。當然,我們更應當看到,對于刑事政策的制定,不僅需要在各種刑事政策的制定中內化這些價值追求,還需要用科學的方法指導刑事政策的建立與調整。刑事政策研究最顯著的體現,就是在于刑事立法的修改,而我國近幾年的刑事法律的修改,尤其是近幾次刑法的修改,雖然在廢除經濟犯罪死刑、建立輕緩化的行刑方式上多有建樹,但也可以明顯看出指導刑事立法的刑事政策是急功近利的,對于社會上反映比較強烈的侵害法益的行為,立法者似乎有著一種“立法萬能”的心態,而沒有注重對于社會犯罪整體情形的把握,也沒有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作出對于現今我國刑事法律體系合理性的判斷。可以說,我國當下刑事立法的現狀與我國當下刑事政策研究注重定性研究,研究成果主要依賴非科學的常識觀念和判斷是有一定關系的。這一情況如果不得到改觀,我國的刑事政策與刑事法律很難取得進一步的社會實效。
(三)中國刑事政策研究的走向:定量研究的深化。在此,筆者認為,中國的刑事政策想要避免林東茂教授所指出的研究空洞化和常識化的狀態,以及真正為社會對抗犯罪與懲罰犯罪提供具有實效的理論支撐,必須重視定量化的研究。
當然,筆者也意識到作為一種公共政策的研究,對于刑事政策的研究并不如同大多數犯罪學的研究是價值無涉的,而是作為政治科學研究的一部分,必然帶有研究者自身的價值判斷,價值無涉在刑事政策學的各范疇下是不存在的,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怎樣在各項研究中找到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平衡點,而在中國刑事政策研究中,更是怎樣在定性研究占絕大多數的背景下,為定量研究找尋生存的空間。
其實,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并不矛盾。指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過程的刑事政策研究,想要達到對于合理的刑事政策的追求,最終達到遏制犯罪的目的,必然要對于一個社會特定時空下的犯罪問題有精確的把握,而僅僅依靠決策者、學者的主觀評判,是不可能制定出符合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科學合理的刑事政策。這樣制定出來的政策,雖然有著美好的價值追求,在現實的實施過程中,必然也是會遇到諸多障礙的,政策的實效也不會十分顯著,進而又要作出相應的調整,浪費了國家、社會資源不說,也很有可能與法治、人權等價值目標相偏離,因為任何美好的追求如果不切合實際情況,要么會被世人所拋棄,要么就會被強加于社會民眾,而違背原初的價值追求。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正義是運用科學的方法,通過辛勤而艱苦的調查研究,在社會現實中被一點一點發現出來的東西;正義并不是僅僅通過聰慧的頭腦,就能夠被人為地、‘理性地’設計、推導或發明出來的東西。”(32)所以,刑事政策定性研究所確認的那些價值取向和論斷,也只有通過定量研究的進一步檢驗,才能真正稱得上是站得住腳的理論。
如前所述,犯罪學屬于實證科學的范疇,“犯罪學與刑事政策之關系,可比喻成醫療上的診斷與治療的關系。”(33)正如學者勞東燕所言,“沒有診斷,何談治療?沒有對相關犯罪事實的正確把握,國家不可能合理有效地組織對犯罪的反應。若無犯罪學上的知識作為決策的基礎材料,刑事政策必淪為一廂情愿的臆測和空想。”(34)筆者認為,當代犯罪學的發展以科學定量研究為內容,是刑事政策研究不可獲或缺的基礎性參考。犯罪統計作為犯罪學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運用各種統計方法,收集各種實證的數據資料,作為一種可以有效支撐起刑事政策定量研究的材料,也應當得到應有的重視。
四、制定科學的刑事政策:選取合適的犯罪統計
為了探尋合理、科學的刑事政策,筆者認為,不能忽視對于各種犯罪統計模式的分析和選取,進而為制定刑事政策及其定量研究,提供較為可靠的實證數據。通過上文筆者對于美國兩種犯罪統計模式分析與優劣比較,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筆者認為,對于刑事政策研究,犯罪統計的制定和選取,應當著重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官方的犯罪統計亟待完善。犯罪統計是把握犯罪現象的基本手段和途徑,各西方國家(包括日本)都有相應、完備、公開的官方犯罪統計,這些由官方統計匯總、公開的資料都是政府部門決策和犯罪研究的基本文獻,沒有這些資料,犯罪學和刑事政策學的研究會受到很大限制。也如筆者前述,這樣的官方統計資料缺乏,在某種程度上也使得犯罪學以及刑事政策學的研究趨于定性研究,而缺乏科學的定量研究。
在中國犯罪問題向來被當做政治問題,而不是社會問題。對犯罪以及與其相關的監獄服刑人員的統計,一直被當作“國家秘密”而不予對外公布,真正的警務部門的犯罪統計遲遲沒有出臺。轉變觀念是建立完善的犯罪統計的第一步。應當認識到,犯罪是社會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之一,只有以正確的態度對待犯罪,才能找到行之有效的解決犯罪問題的對策。犯罪統計不能被稱為是“國家秘密”,而是可以向社會公開的社會信息,也是可供學者研究的數據資料。建立公開的全國性的犯罪統計系統,不僅有利于學者的研究、刑事政策的制定,更可以讓社會公民了解國家的整體犯罪情況,減輕不必要的對于犯罪的過度的恐懼。(35)
犯罪學、刑事法學近幾年不斷涌現出各種以實證的方式研究犯罪問題、法律問題的成果,然而,作為中國官方,特別是中央政府,在對于犯罪的數據統計上卻亮點不多。作為法治發展報告藍皮書的一部分,全國性以及區域性的犯罪統計數據已相繼出爐,不過縱觀其研究成果,不僅不能與美國UCR報告同日而語,甚至在一些基本的內容歸納上也太過籠統,數據的出處也有不詳之處,對于犯罪數據的解釋也常落入傳統的定性分析的視野,而不能正視犯罪數據的實證分析。
筆者認為,全國性的犯罪統計應當學習美國的UCR報告模式,由中央政府負責,收集各地警務系統的接警數、破獲率等。由于我國的公安系統遍布全國任何一級的地方行政區域,且由于我國行政系統的上下層級劃分明確,不存在美國聯邦與州政府的兩級政府劃分,做到這一點并不是十分困難的。在建立國家犯罪統計系統中所需要解決的問題,除了如前文所述的UCR犯罪統計中出現的地方警務系統自身利益的考量外,筆者認為,在中國建立統一的犯罪統計,還應當注意對于公安機關進行基本的分類統計和相關知識的普及以及對舊有的案件處理模式進行精確的界定,分清接警數、立案數、破案數等不同的類別統計。當然,我國的刑法主要繼受于大陸法系,對于分則各罪有著明確的界定,這一點對于犯罪統計的分類歸檔也有著積極作用。筆者認為,建立統一犯罪報告的障礙有可能來自于各地方警務部門自身利益的考量,這一點在美國的UCR報告施行的這幾十年中,也一直是個問題。官方統計報告收集數據的方式決定了其缺陷存在的必然,但是如果不建立這樣一套統計系統,刑事政策的定量分析更加無從談起。如筆者下文所要論述的,可以通過其他的犯罪報告彌補官方統一犯罪報告的缺陷,而不能因為以存在缺陷為理由而不提倡官方報告的建立,因為統計系統建立本身,就是對于各警務系統工作的一種監督,總是利大于弊的。
第二,將犯罪被害的調查,作為對于犯罪案件統計的補充,降低犯罪黑數對于犯罪統計的影響。正如前文所述,受害人不報案,是產生犯罪統計黑數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現象在中國也是十分普遍的,公民基于多方面的考慮而不去報案,真正的犯罪數字要遠高于公安機關的接警數目,雖然這一點在中國還沒有通過實證的被害統計得到證實,但是,筆者認為,任何一個細心觀察中國社會和自身周遭社會情態的人,都不會對這一點產生太大的懷疑。因此,建立被害調查為資料來源的犯罪統計也是勢在必行之舉。被害統計應當依靠各地方政府、人口統計部門、各高校的社會學研究人員、刑事學研究人員共同選定方案和選定調查對象,可以以家庭為單位,也可以以一個特定的社會機構為單位(學校、單位、公司、娛樂場所等),設計適合不同調查對象的調查問卷、選擇合適的復調查時間間隔,減少謊報與夸大報告的幾率。被害調查主要是應用抽樣調查的方式,彌補官方數據的不足,刑事政策的研究者通過親身參與各種研究對象的實證統計,不僅得到了一份與官方統計不同的犯罪數據資料,還得到了與被害人或者是犯罪人的直接接觸,用訪談等方式更加深入地了解犯罪的具體情境,為做進一步的定量分析提供有血有肉的素材。
第三,刑事政策的研究者在具體研究刑事政策時要勤于做社會研究,收集第一手資料。對于大多數刑事政策的研究者,應當綜合考慮上述兩大類的犯罪調查數據,畢竟,上述兩種筆者提倡的犯罪統計在大多數刑事政策學者眼中只是第二手的資料,沒有第一手資料作為對照,刑事政策的定量研究仍舊趨于空洞和不可靠。(36)
刑事政策的定量分析注重研究成果的客觀性、可檢驗性與適用性。不管是在面向立法的刑事政策研究,還是面向司法與行刑的刑事政策研究,都應當注重不同實證數據的對比,盡量價值中立地去判斷當下的犯罪情況。同時,也要注重對個別犯罪和失序問題的刑事政策研究。筆者認為,只有在精細化地對個別問題的科學把握以后,整體的刑事政策才會趨于合理。在研究刑事政策的定量因素時,學者應當投入社會研究中,去發現問題,獲得第一手資料,并運用官方警務報告和被害報告所提供整體犯罪趨勢的較為可靠又可對比的數據,得出科學化的刑事政策研究成果。這需要學者不僅有對犯罪統計資料進行對比分析的能力,更需要學者克服自身的惰性,對刑事政策中的具體問題勤于進行社會調查研究。(37)
五、結語
犯罪統計本來只是警務活動的一種延伸,不過由于當今美國社會犯罪現象的日益嚴重以及由此帶來的犯罪學研究的繁榮,犯罪統計的效用越來越受到美國學者和政府部門的關注。由UCR以及NCVS為代表的兩大種類的犯罪統計,反映了美國在研究犯罪統計方面的豐碩成果和相應的缺憾。從美國犯罪統計的發展可以看出,作為一種實證統計,犯罪統計的作用不僅僅限于支持犯罪學對于犯罪現象的解釋、對于預防犯罪策略的運用,犯罪統計也可以為刑事政策的定量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我國應當在官方層面推進警務犯罪統計與被害犯罪統計,為科學制定刑事政策提供可靠的實證描述,為刑事政策學的定量研究提供堅實基礎。
注釋:
①參見許章潤:《犯罪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
②有的學者就認為,要運用科學的方法,一個重要的原則是實證主義(empiricism),實證主義要求科學家盡量依靠直接的觀察發展,測試理論和假設,雖然研究者不能完全避免自己的主觀傾向,但是,科學主義指導下的研究都是通過不斷的觀察來求證假設和理論的。科學主義的另外一個原則是客觀性,客觀性是指科學家必須努力使自己的測量量具更加精確、更加有效。同時,還要確定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時建構在觀察(或資料)以及精確的測量方式上,而不是建構在個人喜歡或個人推論之上的。另外,科學的方法還意味著對于研究的結果,必須始終持一種懷疑的態度,不斷進行驗證而且運用科學所得出結論的過程應當深入淺出、言簡意賅。參見曹立群、周愫嫻:《犯罪學理論與實證》,群眾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頁。
③參見曹立群:《法學和犯罪學在美國的不了情》,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12年第1期第23頁。
④⑥參見曹立群,周愫嫻:《犯罪學理論與實證》,群眾出版社2007版,第5、23、24頁。
⑤所謂量度,就是指根據情況,按照數學規律結合分析單位編碼的過程。參見Blalock,Hubert M.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1982.Print。
⑦Lynch,J.P.,and J.P.Jarvis.“Missing Data and Imputation in the Uniform Crime Reports and the Effects on National Estimat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24.1(2008): 69-85.Print.
⑧所謂仇恨犯罪,又稱為偏見犯罪(bias crimes),系指個人對種族、宗教身體障礙、性傾向、族群、國籍等具有偏見而侵害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社會的行為,是根據1990年美國頒布的《仇恨犯罪統計案》(Hate Crime Statistics Act)列入UCR的。具體參見曹立群,周愫嫻:《犯罪學理論與實證》,群眾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頁。
⑨Lynch,J.P.,and J.P.Jarvis.“Missing Data and Imputation in the Uniform Crime Reports and the Effects on National Estimat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24.1(2008): 69-85.Print.
⑩參見[美]弗雷達·阿德勒等:《遏制犯罪——當代美國的犯罪問題及犯罪學研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頁。
(11)Maxfield,M.G.“The National Incident-Based Reporting System: Research and Policy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15.2(1999):119-49.Print.
(12)關于美國多種犯罪統計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所反映的美國總體的犯罪情況的詳細描述,可參見Siegel,Larry J. Criminology.11th Ed.ed.Belmont,CA:Cengage Learning/ Wadsworth,2011.Print Lab,Steven P.Crime Prevention:Approaches,Practices and Evaluations.7th ed.Albany,N.Y.: LexisNexis/Anderson Pub.,2010.Print.Wilson,James Q.,and Joan Petersilia.Crime and Public Policy.2nd ed.Oxford;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rint。
(13)Coleman,Clive.Understanding Crime Data:Haunted by the Dark Figure/Clive Coleman,Jenny Moynihan.Crime and Justice(Buckingham,England).Ed.Moynihan,Jenny.Buckingham;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1996.Print.
(14)自陳性報告又可分為被害人的被害自陳和犯罪人的行為自陳,下文主要關注前一種報告類型。
(15)當然,不可否認,也是由于長時間的施行,制作UCR報告的團隊也形成了固定的思維定式,也造成了其報告中的一些基本的缺陷始終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著名的犯罪學家Wolfgang在上世紀60年代便指出了這些缺陷,而時至今日,似乎問題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相應的改善。具體參見:Wolfgang,Marvin E.“Uniform Crime Reports:A Critical Appraisa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11.6 (1963): 708-38.Print。
(16)Tonry,Michael H.Thinking About Crime:Sense and Sensibility in American Penal Culture.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rint.
(17)參見[美]史蒂文·拉布:《美國犯罪預防的理論實踐與評價》,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頁。
(18)Lynch,J.P.,and J.P.Jarvis.“Missing Data and Imputation in the Uniform Crime Reports and the Effects on National Estimates.”JournalofContemporary CriminalJustice 24.1 (2008):69-85.Print.
(19)Coleman,Clive.Understanding Crime Data:Haunted by the Dark Figure/Clive Coleman,Jenny Moynihan.Crime and Justice(Buckingham,England).Ed.Moynihan,Jenny.Buckingham;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1996.Print.
(20)參見[加]歐文·沃勒:《有效的犯罪預防——公共安全戰略的科學設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
(21)Siegel,Larry J.Criminology.11th Ed.ed.Belmont,CA: Cengage Learning/Wadsworth,2011.Print.
(22)Wells,L.E.,and J.H.Rankin.“Juvenile Victimization -Convergent Validation of Alternative Measurements.”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2.3(1995):287-307. Print.
(23)Wells,L.E.,and J.H.Rankin.“Juvenile Victimization -Convergent Validation of Alternative Measurements.”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2.3(1995):287-307. Print.
(24)Hart,Timothy C.,Callie Marie Rennison,and Chris Gibson.“Revisiting Respondent”Fatigue Bias“in the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1.3 (2005):345-63.Print.
(25)UCR報告對于犯罪種類的劃分也為以后的犯罪統計樹立了標準,但是,其對于各罪劃分過于簡單,對于同一類型的犯罪,其嚴重程度沒有進行細致的劃分,這一點早在UCR報告設立初期,就遭到了包括Wolfgang在內的犯罪學家的批判。參見Wolfgang,M.E.,and R.A.Silverman.Crime and Justice at the Millennium: Essays by and in Honor of Marvin E. Wolfgang.Kluwer Academic,2002.Print。之后的犯罪統計逐步改進和細化了犯罪的分類,但是基本還是基于UCR所確立的標準。
(26)有學者認為,在美國,全國案件報告系統(NationalIncident -Based Reporting System,以下簡稱NIBRS)是為犯罪統計研究注入了第三股重要的力量,其將UCR和NCVS統計中的缺失進行了彌補,創造了更為細致的犯罪統計。具體參見:Maxfield,M.G.“The National Incident-Based Reporting System: Research and Policy Applications.”Journalof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15.2(1999):119-49.Print.以及Addington,Lynn A.“The Effect of Nibrs Reporting on Item Missing Data in Murder Cases.”Homicide Studies 8.3(2004):193-213.Print。不過在筆者看來,NIBRS是對于UCR統計報告的一種細化,對于犯罪的分類更為詳細,其借鑒了NCVS的統計方式,使用以事件為基礎的方式,但是警務部門的統計畢竟是基于實務工作的需要,不可能完全模仿NCVS的統計模式,而且以事件為基礎也與警務工作的實際記錄有所不符,一個犯罪事件在NIBRS的統計中可能被分化為好幾次犯罪的統計,但在警務工作中,可能只被記錄為一次逮捕行動和一次犯罪的追訴,NIBRS統計為實務工作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是一種可以得到普遍適用的犯罪統計模式。
(27)參見謝俊貴:《關于社會現象定量研究的簡要評析》,載《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0年第4期第39-45頁。
(28)涂爾干一貫認為各種社會現象都有其規律性,他對在社會學中運用統計方法給予很高的評價,他不僅創立了社會現象研究的研究假設、經驗檢驗、理論結論的實證程序,而且通過《自殺論》一書,為如何利用統計分析和定量研究建構社會學理論提供了范例。參見謝俊貴:《關于社會現象定量研究的簡要評析》,載《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0年第4期,第39-45頁。
(29)參見林東茂:《一個知識論上的刑法學思考》(增訂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頁。
(30)參見林東茂:《一個知識論上的刑法學思考》(增訂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頁。
(31)參見張甘妹:《刑事政策》,臺北三民書局1979年版,第11-12頁。
(32)參見趙軍:《懲罰的邊界——賣淫刑事政策實證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頁。
(33)參見徐福生:《刑事政策學》,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頁。
(34)參見勞東燕:《刑事政策與刑法體系關系之考察》,載《比較法研究》2012年第2期第79頁。
(35)在美國,對于犯罪的恐懼的調查(fear of crime),也屬于犯罪統計之一,雖然其量度的指標相較于犯罪統計較為模糊,但是美國學者認為,不僅需要了解犯罪真實的發生狀況,也要了解社會民眾對于犯罪的恐懼狀態,如此才能更好地指導對抗犯罪的實踐。參見Lab,Steven P.Crime Prevention: Approaches,Practices and Evaluations.7th ed.Albany,N.Y.: LexisNexis/Anderson Pub.,2010.Print。
(36)有的學者就對于在我國警務系統中犯罪統計的真實性提出了很大的懷疑,其認為:“前些年,公安機關強調提高破案率,結果導致了大量的‘不破不立’;之后改為強調考察破案數,才使得案率有所回升;可再后來,當各地公安機關強調治安防控時,為了降低發案率,則又出現了‘控制立案’的情況。可見,如果僅僅立足于官方‘統計’的犯案率,沒有其他材料作為印證和參照,是不可能客觀反映現實社會的實際犯罪動態的,由此設計出來的刑事政策或法律制度也就難免南轅北轍了。”趙軍:《懲罰的邊界——賣淫刑事政策實證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頁。筆者認為,在推進統一的警務犯罪統計的過程中,趙軍博士指出的這些警務活動中固有的弊端是值得引起重視的,這也是筆者提倡應當以被害人報告統計作為另一面的犯罪統計以及學者自身的第一手的社會調查,予以盡量彌補官方報告的失真性。其實,警務活動政策研究也是刑事政策研究的一個方面,指導警務活動政策變動的因素是復雜的,筆者也相信,如果在刑事政策研究方面注重定量研究,較客觀地反映社會犯罪的真實情況,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警務政策的頻繁變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與實際情況想脫離的警務政策的出臺。
(37)胡適之先生在多年前就談到:“為什么談主義的人那么多?為什么研究問題的人那么少呢?這都是由于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得一種解決的意見……高談意見,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胡適:《容忍與自由:胡適讀本》,潘光哲編,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頁。筆者認為,胡適之先生的一番話是極有見地的,拿來與各位讀者、研究人員作為自我鞭笞的警語。
D631
A
1674-3040(2012)05-0073-06
2012-05-22
劉濤,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刑法學2010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刑法學。
(責任編輯:海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