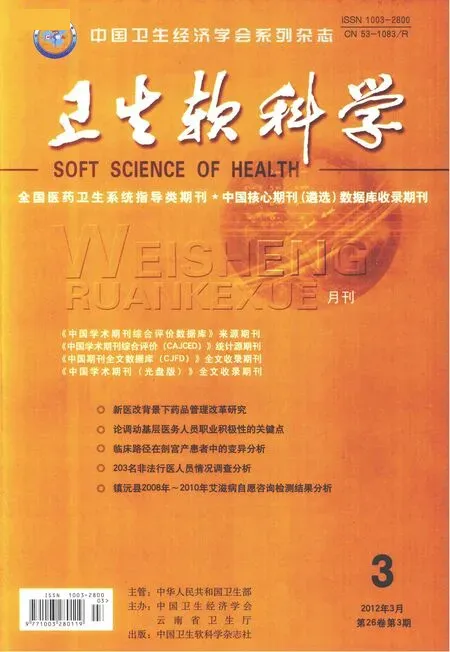新醫改背景下藥品管理改革研究
李曉東
(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藥劑科,廣東 廣州 510282)
2009年以來,隨著醫改新政的相繼出臺,我國醫療保障覆蓋率和醫療保障水平得到了顯著的提高[1]。然而,處于新醫改方案中心的藥品管理的改革,由于牽扯多方利益格局的重新整合,改革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有越改醫療費用越高的趨勢。
1 藥品管理中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
在醫改過程中,醫藥供方系統中生產方、流通方、銷售方等不同利益體之間,不同利益體與國家法規之間不斷博弈,低價藥品逐漸退出流通領域。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藥品生產企業對基本藥物的生產積極性不高
由于基本藥物絕大多數是常用藥,由政府進行定價,有的企業雖然獲得生產許可,由于利潤不大,只是少量生產或者干脆不生產,從而導致了價格低廉的基本醫療常用藥在臨床上消失或經常斷供,藥品生產企業注重生產利潤較高的其他藥物或者將同種成分藥物改變劑型重新注冊,高價銷售。
1.2 流通企業逐漸退出對基本藥物的經營
許多藥品零售和流通企業,出于藥品的生產和使用中的諸多問題,由于基本藥物流通性趨緩,為提高藥物流動性,降低庫存壓力,降低成本,逐漸退出一些基本藥物、廉價藥物的經營。
1.3 醫院對基本藥物應用的積極性不高
在公立醫院經濟補償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公立醫院應有的公益性質不能體現[2],而基本成為市場機制下自負盈虧狀態,醫護人員的福利只能通過醫院收益來保障。醫藥之間的利益共同體的存在,使醫院可能會基于自身利益的驅動不得不降低對基本藥物的使用。
1.4 醫生不開基本藥物處方
一方面,由于新醫改實施不久,醫師對基本藥物的相關規定不熟悉,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基本藥物的可獲得性;另一方面,病人缺乏對最基本醫藥知識的了解,在信息絕對不對稱的情況下,醫師缺乏有效的監督,容易受利益驅動降低開基本藥物處方,而是通過開高價藥處方以獲取高“回扣”[3]。
1.5 醫藥代表與醫生間的利益鏈積重難返
醫藥代表是藥品生產與使用中很關鍵的一環,在現行體制下,醫藥代表的收入與藥品的使用量直接相關,而藥品的使用則由醫生控制,在共同利益驅使下,高價藥物盛行在所難免,而國家控價的基本藥物則會逐漸退出流通領域。
1.6 大眾對醫藥基本知識缺乏
在新醫改體制中,國家要求各大醫院落實病人有自主選醫生和在醫師指導下選擇藥物的權利。但由于大眾對醫藥知識的絕對匱乏,使政策流于形式。
2 強化藥品管理的主要措施
2.1 建立醫院分級與用藥分級相結合的制度
首先,建立和發展穩定的社區及縣級醫院的基本藥物供應和價格監管體系,重點發展縣級 醫院,建立健全鄉鎮醫院[4],將縣級醫院及社區醫院和鄉鎮醫院作為國家基本藥物的主要用藥單位[5]。其次,發展三甲醫院為代表的高端醫療市場,主要醫治疑難雜癥和重癥,專利藥、創新藥和進口藥在這些醫院的供應所占比例可以有所提高。最后,建立健全基層醫療機構與大型三甲醫院間的轉診機制,保證基層醫療機構不能醫治的大病、危病時可以及時轉送到技術過硬的三甲醫院,三甲醫院要根據病人經濟能力與基層醫院的用藥建立適當銜接體系,保障病人的醫療費用不要過高。
2.2 完善基本藥物集中配送制度
國家對基本藥物及一些市場需求量小的藥品應該進行干預,采取定點生產的方式,以保證這些藥品的供應,而對于大部分藥品由市場經濟運行規律進行調控;在采購配送環節,政府應對基本藥物實行市場化的集中采購、直接配送模式。政府負責多元化主體“集中采購”實施的法律法規的制定及監督,包括制定規范的采購程序、控制批零差價等等,采購和藥物配送的主體則應由市場完成,充分發揮公共與市場的優勢,避免返回到計劃經濟老路上去,同時又確保基本藥物的供應順暢。
2.3 加強臨床藥師的培養,發揮臨床藥師在臨床用藥中的監督作用
“1997年美國臨床藥學院(ACCP)提出建立合作藥物治療管理制度(Collaborative drug therapy management,CDTM),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強化的研究。結果表明:由于臨床藥師的參與,每位患者可節省的平均醫藥費用是600美元,醫院由于提供藥學服務的藥師數量增多用藥錯誤率下降了65%”[6]。那么,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的藥師管理制度,藥師參與臨床合理用藥,與醫師、護士一起優化臨床治療方案。臨床藥師具有醫學、藥學雙重背景,他們能與患者良好溝通以提高藥物治療的依從性,并能兼顧藥物價格和醫療費用,從藥物經濟學角度和醫生的疾病診療兩方面來確定藥物治療方案,減少因藥物或治療不恰當引起的住院時間延長、藥費增加等問題。同時在用藥過程中對醫生用藥的合理性及合法性進行實時有效監督,最大程度避免醫療賄賂問題,維護病人的利益。
2.4 建立醫療補償機制,保障醫療領域從業人員切身利益
在醫療改革體制的建設過程當中[7],醫生和醫院始終處于核心地位,其合法權益和利益如果得不到保證,就很難調動其積極性,醫改也不可能獲得成功。因此,醫院藥品加價銷售被取消后,國家必須盡快建立醫療補償機制[8~9],保障醫療領域從業人員切身利益,這也是遏制醫療回扣等問題的必要前提。
2.5 明確醫藥代表的法律地位,減少醫藥代表收入與特定藥品使用量的關聯度
醫藥代表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曾為藥品市場經濟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于一直以來藥廠對醫藥代表的利益直接與其負責藥物的使用量掛鉤,而對其職業行為卻沒有明確的規范和約束。從而形成了醫藥代表個體與醫生的直接利益鏈條,國家雖然也出臺了一些規定進行打擊,然而倒買倒賣稅票、商業賄賂、掛靠經營、走票,利用回扣、開單提成等不正當的交易還時有發生,而且很難被發現。要解決這些問題,筆者以為藥品營銷應以廠家為主體,廠家可以定期以不同學術活動的形式,邀請醫師參加,讓醫生了解了藥品功效,而醫藥代表可以作為各種活動的實施者,明確醫藥代表的法律地位,避免其收入與藥品用量直接掛鉤,對其職業進行規范,解決回扣、提成等一直以來藥品流通領域難以解決的問題。
2.6 加強醫藥基本知識的普及,使病人在診療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在信息社會中,國家可以充分利用媒體的作用,以科普小常識的形式向群眾介紹一些藥物基本知識,從而使群眾能在藥品流通管理及使用中起到一定監督作用。改變信息的絕對不對稱局面,藥物流通中存在的許多問題也就會迎刃而解。
[1]干榮富.國家基本藥物目錄與醫藥行業[J].中國醫藥工業雜志,2009,40(1):67-70.
[2]杜樂勛.基本衛生服務項目及其需求[J].中國衛生經濟,1997,16(11):13.
[3]饒克勤.用科學發展觀指導我國衛生改革與發展[J].中國衛生經濟,2006,(10):10-13.
[4]李一平.也談農村居民醫療保障[J].中國衛生經濟,2004,23(12):44-45.
[5]王甫群.發展中的企業醫院[J].中國醫院,2009,13(1):25-26.
[6]Jameson J, VanNoord. The impact of the pharma-cotherapy consultation on the cost and outcome of medical therapy[J].Family Practice,1995,41(5):469-472.
[7]徐培紅,干榮富.新醫改后的醫藥行業發展之思考[J].中國醫藥工業雜志,2009,(5):102-106.
[8]杜樂勛.我國衛生改革政策的經濟學分析[J].中國衛生經濟,2006,25(2):5-9.
[9]李明哲.福利經濟學與醫療衛生改革的基本政策取向[J].中國衛生經濟,2007,26(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