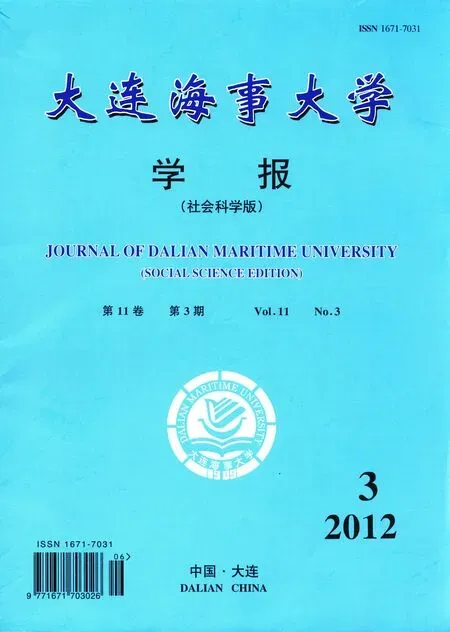明政府政策性失誤對"倭患"走勢的影響
王 娟
(大連海事大學 航海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遼寧 大連 116026)
明政府政策性失誤對"倭患"走勢的影響
王 娟
(大連海事大學 航海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遼寧 大連 116026)
以史料為依據,對明政府應對"倭患"的一系列政策和舉措加以分析,并闡述應對失策與"倭患"走勢之間的關系:首先,海禁導致"倭患"的爆發態勢;其次,剿撫不定與打擊目標的失當,屢屢招致更大的反噬;而一再錯失開海時機,更是造成"倭患"的延續.
明政府;倭患;海禁;勘合貿易;剿倭;開海
有明一代,"倭寇"、"海盜"對中國東南沿海頻繁地騷擾和劫掠,給當地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成為明中期以前必須長期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作為明政府,剿滅倭寇,經略海疆,護佑百姓是其當然的責任,并為此投入了大量的軍隊,耗費了大量的財政收入.然而,明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性失誤卻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甚至客觀上造成"倭患"升級和不可控狀態,并對海外貿易發展產生了深遠的無可挽回的負面影響.需要指出的是,所謂明政府的"政策性失誤",既包括相關政策本身制定的失誤,又包括政策貫徹不力以及頒布時機的失當.
一、海禁對"倭患"的客觀催化
中國東南沿海的倭亂起于元朝.此前,從魏景初二年(238年)倭女王卑彌呼遣使來華開始,歷經唐宋,中日雙方基本上保持著以中方為主導的友好關系.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在高麗人趙彝的攛掇下遠征日本,后于至元十八年再征,兩次都大敗而回.自此,中日雙方開始了敵對狀態,東南沿海"倭患"初現.元于大德七年(1303年)和至大四年(1312年)兩度取消市舶機構,禁商下海,而日本官方終元一朝也不再與中國來往.
1.明初海禁及其直接后果
明初,并沒有馬上禁海,相反,明太祖朱元璋對發展海外貿易顯示出積極的態度.稱帝前一年,"十二月,置市舶提舉司,以浙東按察使陳寧等為提舉" (《明太祖實錄》卷二十八下,吳元年十二月).其時,民間以朱道山為代表的海商頻繁"以寶貨往來海上" (王彝《王常宗集》補遺,《送朱道山還京師序》),官方"番舶接跡而來廷,蠻琛聯肩而入貢"(《明經世文編》卷二,宋濂《閱江樓記》),并且延續了宋元時代的抽分制,通海貿易在江浙和閩粵沿海頗為活躍.
明朝實行長期的海禁政策,主要是針對當時嚴峻的東南海疆形勢而設.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所部水師敗亡入海,盤踞海道,勾連海盜、倭寇,參與武裝走私貿易,并時常登陸劫掠,于洪武二至四年形成一個小爆發態勢.二年四月,"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略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亂》);同年,廣東潮州、惠州等地相繼遭倭寇襲擾.四年,海寇鐘福全等,"挾倭船二百艘寇海晏、下川等地"(郭《粵大記》卷三十二《政事類》).一時間",倭夷竊發,濱海一帶皆被騷擾"(同上).
于是,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乙未,朱元璋明確表態實施禁海:"朕以海盜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明太祖實錄》卷七十)幾日后下詔,"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同上).其實在前一年,即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就已下令關閉了太倉黃渡市舶司,正式下詔后,海禁政策頻繁出臺.七年(1374年),撤銷泉州、明州、廣州三市舶司,徹底關閉官方海外貿易;十四年(1381年),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三十九);十九年,廢昌國縣;二十年,強遷舟山島及其他四十六島(山)居民入內地;二十三年,再頒禁外藩交通令;二十七年,禁止民間使用和買賣番香、番貨;三十年,再申禁令,"人民無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五十二);三十一年四月,禁廣東通番.可見,終洪武一朝,明太祖一直在厲申禁海,沒有松動.
除了政策性的禁令頒布外,明政府又在《大明律》中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規定,諸如"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番貨到來,私買販賣蘇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發邊衛充軍".
通過這些政策和法律的規定,海外貿易的進口、出口及運輸環節均遭到嚴禁,必然導致其向無管理狀態的武裝走私發展.而強遷海島居民入內地,沿海島嶼被棄,給倭寇和海盜留下了隱蔽而可靠的落腳點.更為嚴重的是,濱海商民由于禁海生計無著,轉而成為靠搶掠為生的海盜.
其實,相對而言,洪武朝的沿海"倭患"只能稱為小規模騷擾事件,然而,明政府錯誤的禁海決定卻取得了適得其反的效果,客觀上成為醞釀大規模"倭患"的催化劑.正如時人所云"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嚴而寇愈盛"((明)謝杰《虔臺倭》卷上).
2.勘合貿易與盜、寇合流
明初的海禁不僅使本國深受影響,同時也影響到了貿易對象國之一的日本.14世紀末,日本結束南北朝混戰局面而歸于統一,整個社會對生活用品的需求大大增加,開始感受到明朝海禁帶來的限制和不便.于是,在應永九年(1401年),日本遣使入明,上表求貢.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日本再遣使者來華.永樂二年,成祖派趙居任回使日本,并發給日本政府"本"字勘合一百道,"詔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軍器,違者以寇論"(《明史.日本傳》),這就是"勘合貿易".明廷同時要求日本政府禁止倭寇騷擾我國東南海疆.
勘合貿易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貿易,而是海禁政策的一種補充.這種朝貢性質的交換行為,以明朝付出貢品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回賜為代價,而對于進貢方的日本來說,自然是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勘合貿易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由于禁海造成的中日貿易危機,短期內滿足了日方對明朝的商品需求,所以一段時間內兩國關系發展良好.日本方面也積極響應明朝鎮壓倭寇的要求,"明年(永樂二年)十一月來賀冊立皇太子.時對馬、臺岐諸島賊掠濱海居民,因諭其王捕之.王發兵盡殲其眾,縶其魁二十人,以三年十一月獻于朝,且修貢.帝益嘉之,遣鴻臚寺少卿潘賜偕中官王進賜其王九章冕服及錢鈔、錦綺加等,而還其所獻之人,令其國自治之.使者至寧波,盡置其人于甑,殺之"《(明史.日本傳》).
然而,由于勘合貿易畢竟難以解決兩國特別是日方的貿易需求,因此這種權宜之策注定深埋隱患,終于爆發了一場日本使團的"爭貢之役",并因此在沿海地區引發了一場小騷亂."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使宗設、宋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真偽.市舶中官納素卿賄,右素卿,宗設遂大掠寧波.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罷之."(《明史》卷八十一《食貨》五)
在這件事上,明政府從認識到處理,一開始就出現了偏差,由于中方官員受賄而引起的日方真偽貢使之爭,根本原因在于明朝給予日本的貿易機會不能滿足需要.而明統治者并未作出正確判斷,反而錯誤地認為"倭患起于市舶",于是進一步加強海禁,連僅有的疏通渠道都堵塞了,這必然造成矛盾的集聚和爆發.而且,有貿易需要的也并不只是日方,中國東南沿海對開展海外貿易的需求也相當迫切.進一步的海禁措施,不僅使官方貿易萎縮,民間事實存在的走私貿易也因受到空前的打擊而失去生存空間,于是形成"海禁愈嚴,賊伙愈盛"(唐樞《御倭雜著》,《明經世文編》卷二百七十)的局面.
明政府對爭貢事件的錯誤判斷和處理,直接導致勘合貿易的結束.而日本使團在中國的公然搶掠起到了一個極其惡劣的示范作用,日本浪人、武士、流民等群起效仿,與中國由于失去生計而被逼入海的武裝走私者大規模合流,造成時人所謂"江南海掠,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明)佚名撰《嘉靖東南平倭通錄》)的局面.
二、剿倭失策與嘉靖"倭患"大爆發
嘉靖初年的爭貢事件后,雖然海禁愈嚴,但武裝走私仍留有一定空間,并且事實上形成了幾大走私集團.明政府開始加大對武裝走私的打擊力度.嘉靖二十七年,朱紈以"佛郎機國人行劫"((明)鄭若曾《籌海圖編》卷二十五)為由,對當時最大的武裝走私集團"許棟集團"發起攻擊,"擊擒其渠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復以便宜戮之"(同上),隨即搗毀了"許李集團"的大本營,"筑塞雙嶼而還"(《明史.朱紈傳》).不久,又在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許棟亦就擒" (同上)."許棟集團"遭到重創,"棟黨汪直等收余眾遁"(同上),成為"汪直集團".嘉靖"倭患"轉劇,即以"汪直集團"的興起為標志.而朝廷剿倭政策的偏差,也成為"汪直集團"做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1.打擊目標的失當
朱紈無疑是堅定的剿倭派,上任伊始便實施"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明史.朱紈傳》)的嚴厲措施,然而非但沒有得到當地百姓的支持,相反卻遇到了強大的阻力,問題就在于其打擊目標有失偏頗,通過嚴禁民間走私貿易來剿除"倭患",失去了群眾基礎."閩人資衣食于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明史.朱紈傳》).及至朱紈攻破雙嶼后,更是引起民怨沸騰,"勢家既失利,則宣言被擒者皆良民,非賊黨"(《明史.朱紈傳》).
在這種情況下,朱紈也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并且被當成平息禍亂的替罪羊,御史陳九德"劾紈擅殺.落紈職,命兵科都給事杜汝禎按問"(《明史.朱紈傳》),結論是"奸民鬻販拒捕,無僭號流劫事,坐紈擅殺"(《明史.朱紈傳》),朱紈服藥自盡.朱紈的死,導致統治階級本來堅定的剿倭立場發生松動和變化, "自紈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 (《明史.朱紈傳》),此后以汪直為首的倭寇海盜集團趁機發展起來,成為海上霸主.
而朱紈在剿倭過程中的另一個重大失策是對通番勢家豪族打擊不力.關于朱紈進剿許棟集團的起因,《皇明馭倭錄》記載頗詳:"海上之事,初起于內地.奸商汪直、徐海等,常闌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于余姚謝氏.久之,謝氏頗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怒之曰:'吾將首汝于官.'諸奸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申聞上司,云倭賊入寇,巡撫紈下令捕賊……"(《皇明馭倭錄》卷五).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本來是參與走私的海商與"坐地商"共同釀成的禍亂,而朱紈只對汪直、徐海等海商進行打擊,對"坐地商"余姚大戶謝氏則非但不予問罪,反而予以保護.
東南"倭患"的加劇,與這些通倭勢家豪族關系重大."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竇,而官人不得顯收其利權.初亦漸享奇贏,久乃勾引為亂,至嘉靖而弊極矣"((明)張燮《東西洋考.銅稅考》).這些沿海豪族除直接經營海外走私貿易外,還勾引倭寇入內地,充當窩主,提供接濟.屠仲律在給嘉靖帝的《御倭五事疏》中便提到沿海豪族"為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入,陰相窩藏,展轉貿易"(《明經世文編》卷二百八十二).其實,以朱紈為代表的明政府已經對此有所認識,他說:"大抵治海中之寇不難,而難于治窩引接濟之寇.治窩引接濟之寇不難,而難于治豪俠把持之寇." (《明經世文編》卷二百零五)然而由于其勢力在社會以及朝廷內部的盤根錯節,予以打擊必將引起復雜的局面,而朱紈最終的死,與通番豪族操縱輿論不無干系.對這些通番豪族缺乏必要的打擊,也是導致長期剿倭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2.剿撫不定及其后果
汪直集團興起后,統治集團的對策一直是剿撫不定.由于當時海上寇、盜頻發,汪直集團也屢遭搶劫,海貿秩序受到極大擾亂,因此也希望打擊海盜,在這一點上和明政府是一致的.于是,明政府先是與汪直合作,剿滅了陳思盼、盧七、沈九等以劫掠為主的海上武裝勢力.汪直與官府合作,其目的就是"互市",即貿易合法化,而官方也以此向汪直許諾.剿除大盜陳思盼后,在官府的默許下,汪直得到了一段時間的貿易自由,"番船出入,關無盤阻,而興販之徒,紛錯于蘇杭,公然無忌"((明)萬表《海寇議.前編》).然而不久,隨著新任巡視浙江都御使王忄予以及參將俞大猷的到來,情況突變.嘉靖三十二年, "俞大猷驅舟師數千圍之,直以火箭突圍"((清)張海鵬刻《借月山房匯鈔.汪直傳》).王忄予與俞大猷對汪直的這次突襲另有隱情."時有賊首蕭顯等,誘倭入寇上海縣.賊首王十六、沈門、謝獠、許獠、曾堅,誘倭焚劫黃巖縣.參將俞大猷、湯克寬,欲令王直于黃巖拿賊受獻,而賊已遁,乃議王直以為東南禍本,統兵擊之于烈港……"((明)鄭舜功《日本一鑒》卷六《流逋》).按此,俞大猷無疑有失道義,所以汪直突圍后自然"怨中國益深"((清)張海鵬刻《借月山房匯鈔.汪直傳》),直接導致"倭患"大爆發.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王直令倭夷突入定海關,移泊金塘之烈港,去定海水程數十里,而近亡命之徒,從附日眾,自是倭船遍海為患.是年四月賊攻游仙寨,百戶秦彪戰死,已而寇溫州,尋破臺州、黃巖縣,東南震動."((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九邊四夷》)接下來,"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破昌國衛.四月犯太倉,破上海縣,掠江陰,攻乍浦.八月劫金山衛,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倉掠蘇州,攻松江,復趨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復薄蘇州,入崇德縣.六月由吳江掠嘉興,還屯柘林.縱橫來往,若入無人之境……明年正月,賊奪舟犯乍浦、海寧,陷崇德,轉掠塘棲、新市、橫塘、雙林等處,攻德清縣.五月復合新倭,突犯嘉興,至王江涇……余奔柘林.其他倭復掠蘇州境,延及江陰、無錫,出入太湖……" (《明史.日本傳》)這場"倭患"完全是出于報復,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官方政策突變以及打擊手段失當使矛盾激化,結果是東南沿海遭到涂炭.
胡宗憲巡按浙江后,又以互市為條件,對汪直進行招撫.汪直雖然一直未放松警惕,但經過兩年的接觸,最終決定渡海受撫.然而結果正如其事先做好的最壞打算,被下獄論死.汪直的死,雖然標志著東南沿海一個最大的武裝走私集團覆滅,然而卻因缺乏約束而導致"倭患"蔓延."逾年,新倭大至,屢寇浙東三郡.其在岑港者,徐移之柯梅,造新舟出海,宗憲不之追.十一月,賊揚帆南去,泊泉州之浯嶼,掠同安、惠安、南安諸縣,攻福寧州,破福安、寧德.明年四月遂圍福州,經月不解.福清、永福諸城皆被攻毀,蔓延于興化,奔突于漳州.其患盡移于福建,而潮、廣間亦紛紛以倭警聞矣"(《明史.日本傳》).這次爆發的"倭患"為害猶劇,直到隆慶年間才漸漸被平.幾十年后,談遷在其所著《國榷》中對此事評價到:"胡宗憲許王直以不死,其后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則岑港、柯梅之師可無經歲,而閩、廣、江北亦不至頓甲苦戰也."
嘉靖"倭患"的大爆發雖然是禁海政策下的必然結果,但是,由于明政府的政策搖擺、執行不力及處置不當,客觀上造成其規模擴大、為害更甚的惡果.
三、遲滯的開海舉措客觀上加劇了"倭患"的危害
在剿倭過程中,明政府內部也開始發生分歧,以朱紈、俞大猷、王本固等為代表的保守派主張堅決清剿,而以胡宗憲等為代表的務實派主張剿撫并用,以盜制盜.胡宗憲主張的"撫",是以開海互市為條件的,朝廷雖然一度支持招撫,但對開海互市卻一直沒有明確答復.
1.最佳開海時機的接連錯失
在汪直做大的時候,也是開海互市、平復"倭患"的最佳時機.首先,汪直與明政府的合作一直是以"同貢互市"為目標;其次,汪直對東南"諸倭"具有絕對的掌控力.
作為當時最大的走私商,汪直集團也屢遭海盜搶劫,因此在打擊海盜、建立正常的海貿秩序上和明政府是一致的.嘉靖三十年前后,汪直先后與官軍配合,剿滅了海盜盧七、陳思盼等.在官方的默許下,汪直集團獲得了一段時間的貿易自由,并得到了當地社會的普遍支持.然而不久后,王忄予、俞大猷對汪直的強力打擊使第一次開海時機被錯失,并由此造成報復性的"壬子之變".
汪直去日本后,一直沒有放棄謀求"互市".胡宗憲巡按浙江后,再次迎來開海互市、平復"倭患"的良機.嘉靖三十四年,胡宗憲派寧波生員蔣洲、陳可愿出使日本,和汪直及其養子毛海峰接觸.汪直表示"俞大猷絕我歸路,故至此.若貸罪許市,吾亦欲歸耳"(《明史.胡宗憲傳》),并派遣部下葉宗滿、毛海峰、汪汝賢等送陳可愿回國,"投赴效力,成功之后,他無所望,惟愿進貢開市而已"((清)張海鵬刻《借月山房匯鈔.汪直傳》).然而,當汪直帶著誠意歸來時,雖然有胡宗憲力保,但由于保守派勢力強大,最終還是被下獄問罪論死.官場紛爭與傾軋,導致又一次錯失開海時機,并招致"逾年,新倭大至"的又一輪涂炭.
2.隆慶開海與"倭患"的平復
隨著嘉靖時代的逐漸落幕,東南"倭患"也暫告平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中央政府批準漳州知府唐九德在月港設縣治的提議,并于隆慶元年(1567年)在月港設海澄縣.同年,即位不久的明穆宗采納福建巡撫涂澤民的建議,下令部分開放海禁, "準販東西二洋".這就是所謂的隆慶開海.
從隆慶開海首選月港這樣一個小港,就彰顯了明政府極強的目的性——以息禍為首要,發展海外貿易次之.因為嘉靖年間的所謂"倭寇"以漳州人最多,"有禁,然不絕其貿易之路者,要以彌其窮整易亂之心"(《明神宗實錄》卷四百七十六).這說明當時明政府已經部分認識到"倭患"爆發的原因.隆慶開放也確實達到了這一目的.從國初就一直飽受困擾的"倭患"問題得以暫時解決,東南沿海開始出現繁榮、安定的局面,明政府也得以從此抽身,集中力量加強日益吃緊的北部邊防.僅從隆慶開海有限的成果上,反證了明政府海禁政策和開海遲滯對"倭患"發展走勢事實上的反推效應.
四、結 語
明代"倭患"從洪武朝蓄勢至嘉靖朝爆發,固然是當時國內外政治形勢以及經濟、貿易發展狀況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明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性失誤起到了不可低估的負面作用.海禁政策逼使靠海貿為生的瀕海商民入海為盜,為"倭患"的最終釀成提供了"人力來源";勘合貿易有限的疏導功能不能滿足正常的貿易需求,必然導致矛盾的大量集聚和最終的爆發;在剿倭過程中,明政府的政策搖擺以及目標失當,往往非但不能形成有效的打擊力量,反而造成災難性后果;而圍繞剿撫問題的官場斗爭,使開海時機一再錯失,客觀上擴大了"倭患"的危害.隆慶開關后,"倭漸不為患"(《明史.兵志三》)的事實證明了明政府奉行兩百年的海禁政策徹底失敗.
1671-7041(2012)03-0090-04
F552.9
A*
2012-03-01
王 娟(1963-),女,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