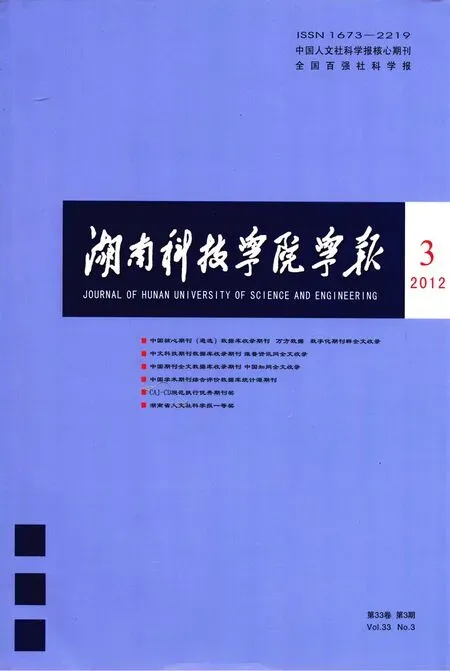從兩篇緒論看劉綬松寫作新文學史
尹 琴曾 輝
(貴州師范大學 求是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1)
中國現代文學自新文化運動始,至今發展已有百年歷史。但對這種現代的新式文學形式及文學樣式做出真正系統的歷史 考察,則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及其他理論著作,魯迅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及他為一些現代文學作品所寫的序言及有關論述,茅盾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及作家論系列,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以及馮雪峰稍后寫的《論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等,都是同時代文學理論家研究現代文學的最初嘗試。在此以前發表的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等著作,在學術界也產生過一定影響。繼40年代初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五四運動﹑新文化﹑新文學的一系列論述,為現代文學研究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之后,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才發展成為一個獨立學科。而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以下簡稱《史稿》)、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以下簡稱《初稿》)是最初的成果。
劉綬松編寫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分為上下兩卷(約55萬字),于1956年4月出版,在反右運動之前,曾數次重印,在當時王瑤及其《史稿》受到批評之后,劉綬松的《初稿》遂成為繼《史稿》之后一部影響較大的新文學史著。
“文革”期間,劉綬松受到迫害,過早離開人世,其《初稿》也受到批判。《初稿》初版于1956年,1958-1959年間,劉本人曾修改過一遍,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講義》在武漢大學內部印行;1979年,再次修訂。此次修訂,以著者修改過的《講義》為基礎,酌取《初稿》本的長處,于 1979年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次出版。劉綬松的《初稿》是清算胡風、批判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之后以更加“正統”的姿態出現的一部教材,其實際影響比丁易、張畢來的文學史都大。
韋勒克和沃倫在談到文學研究的“初步工作”時曾說:“一個版本幾乎包括了每一種文學研究工作。在文學研究的歷史中,各種版本的編輯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每一版本,都可算是一個滿載學識的倉庫,可作為有關一個作家的所有知識的手冊…”[1]P56這段話同樣適用于中國新文學的研究。本文則通過使用新文學的版本學的批評方法,對《初稿》初版與修訂版的兩篇緒論進行細致分析與比較,以此來窺探劉著不同版本變化所體現出來的作者修史意圖、創作心態、時代風貌、政治意識形態等各方面的變化。
一非正文頁的修改
一個完整的版本應該有九種因素,即封面頁、書名頁、題詞或引言頁,序跋頁、正文頁、插圖頁、附錄頁、廣告頁、版權頁,我們稱之為“九頁”。[2]p315以下即從“九頁”這九種因素來看這兩部文學史。
首先,這兩部文學史的版本均沒有做到九頁齊備。兩部作品均缺題詞或引言、插圖頁、廣告頁。另外具備的“六頁”中,除正文頁(即內容)方面有較大改動之外,其它“五頁”互有異同。
(一)語言規范
比較兩部著作,從外觀上看,文本形式上最大的變動即體現在文學史的語言規范上。從正文頁的文字及其排列方式,我們則能確認版本所屬的不同時代。
初版仍采用豎排版、繁體字,而修訂版則是橫排版、簡體。從新文學的版本批評學觀點來看,文本的排版與文字繁簡同樣是版本學中需要考察的重要方面。在語言規范上的這些改動,究其修改原因,最重要的是受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漢語規范化運動的影響。
1955年10月,全國現代漢語規范化問題學術會議召開,緊接著,大規模的現代漢語規范化運動迅速展開,涉及各種出版文檔資料,文學史及教科書的寫作更是需要規范的重點對象。于是在劉著修訂版中的語言,則有了從豎排到橫排、從繁體到簡體的較大變動。除此之外,修訂本還針對多處語言表達、語句陳述等錯誤進行修正,并把少量文言詞語改成了白話文,且在細細斟酌之后使用了較為規范的現代漢語的表達方式。
(二)序跋內容
初版寫于1955年,是在自己的一份課程講稿基礎上寫成的,當時的劉綬松正在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新文學史的。50年代初期,新文學被列為高校文學專業的基礎課,緊接著,教育部制定了新課程的編訂大綱,隨后多部新文學史接連問世,《初稿》的出現也正是處于這一次造史熱潮背景之中的。[3]
修訂版寫于1979年,此時正值“四人幫”被粉碎,中國文化界出現了繼“五四”之后又一個思想大解決、大震蕩時期,同時也是一個沉痛的反思歷史、尤其是反思新文學歷史的時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又出了重寫新文學史的熱潮。在修訂版的后記中也提到過對原著進行修訂的原因:劉綬松同志于1955年寫畢《初稿》后,1958-1959年間曾自行修改過一遍,原打算于60年代中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但后來因“四人幫”的禁錮使得再版計劃擱置;1979年修訂版的付梓是由武漢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的同志們在劉綬松1959年的修訂稿基礎上稍加修改而完成的。
從初版到修訂版,兩次寫史,都處于不同的兩次造史大背景中,這樣的變動,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新文學史的不斷建構、解構和重構。
二緒論部分的修改
比起僅僅是因為一場語言規范運動而引發的著作排版及用詞方面的形式改動來說,著作中有關于內容或主題的修改更能體現出作家的修史態度,并反映出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尤其是在新的國家意識形態下寫作新文學史的態度。一部文學史的緒論一般可視為對全書內容的概括。《初稿》的緒論談到了作者對于前人所修新中國文學史的評價、本人修史的目的、修史所遵循的原則及《初稿》中作者本人的文學史觀。故先以緒論部分為例,從宏觀的角度來看初版與修訂版的區別。
(一)分清“敵我”、“主從”界限——最主要的政治表態
50年代的文學史寫作一般都很注重政治表態和理論指導的明示,劉著也不例外,且他的“表態”更上升為明確的政治立場及適合操作的寫作套式。如在《緒論》中,劉宣稱研究新文學史必須具備幾個“基本觀念”:一是弄清新、舊文學的區分,要明確新文學“是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向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向前進的文學”;二是“劃清敵、我界限”,凡是“為人民的作家”、“革命的作家”就給予主要的地位和篇幅,凡是“反人民的作家”就無情地揭露和批判;三是把對魯迅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上來。
在初版的《緒論》中,第二個關于“要劃清敵我界限”的“基本觀念”,在修訂版中則被修改成了“要劃清‘敵我’、‘主從’界限”,并把如何劃清“主從”界限之間的問題進行了詳細闡述,并指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是我國新文學運動的主流”,這是以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文藝及文學創作方法進行論述的重述及再次強調。而劉的這三個觀念顯然也有“超越”王瑤等人寫著文學史的意圖——當初文學界批判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主要的“根據”也就是認為王瑤的“敵我不分”、“主從不分”。劉著在初版中明確提出要劃分“敵我界限”,并提出要分清“主從”,且在兩年后的修訂稿(劉自己修改的未出版的手稿)中再次明確提出如何區分“主從”問題,很顯然從與王著受批判一事中吸取了教訓。比起王著來,劉著的《初稿》則顯得更加政治化,更加富于戰斗性、批判性與排他性。
(二)對文學史進行分期與命名——對歷史的政治性劃分
劉著把文學史分為五個時期:一、五四時期的文學(1917-1921);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學(1921-1927);三、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的文學(1927-1937); 四、抗日戰爭時期的文學(1937-1945);五、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學(1945-1949)。
以上分期在修訂版中與原版保持著大體一致的情況,只是 1945-1949年的分期在修訂版中被改成了“解放時期文學”。
盡管分期的歷史時段未作改動,但這一分期名稱的變動其中也是大有文章的,這其中也反映出了在新的國家政權建立后、新的國家意識形態出現后對“革命史”修史的新的影響。從“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到“解放戰爭”只是一個名稱的變化,也能使人感覺到在這段期間戰爭背后的政治意識形態沖突——新的政黨在奪取了革命勝利、建立新的革命政權之后,新政黨對于之前被舊黨所統治的人民必然是進行了一次大解放。那么,很顯然,用“國內革命戰爭”這樣一個中性詞來概括這次包含著重大政治意識形態的戰爭則顯得不恰當了。
(三)作家作品選評——反映著者的文學立場
《緒論》有關作家的某些論述在前后兩個版本中改動較大。在談及前人對新文學史的論述時,劉著曾提到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和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中的觀點,認為那是“舊中國的反動文人們”在“卑鄙險毒地歪曲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真實歷史”;在修訂版中,劉曾提到胡風《論民族形式問題》中對新文學運動的論述,認為胡風的論述“妄圖否認我國新文學運動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之下發生和發展起來的這個鐵的事實”,是“否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文學對我國新文藝的巨大的深刻的影響”。
在修訂版中特意提出胡風的相關論述,并進行批判,這與當時的學術環境也是有莫大關聯的。1956年高等教育部組織了全國統一教材的編寫工作,新文學史由王瑤、劉綬松負責編寫工作。1956年7月審訂了這門課程的教學大綱。在這份大綱的“導論”中,一方面提了研究文學史要堅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清主次、鑒別材料”,但同時強調要“從具體材料理作具體分析,作出正確的結論”、一方成寫明了要批判胡適、胡風的理論,同時又強調“對于庸俗社會學傾向的糾正”。在“反胡風”運動結束之后進行修改的修訂版,必然地嚴格依照此大綱“導率”中的要求對胡風的理論進行嚴厲的批判。
又如在提及1945-1949年期間創作時,劉著認為我們有了“更為豐盛的主要收獲”,并提到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對于丁玲的這部反映土改生活的作品,初版把其歸納到“最豐盛的收獲”之一,由于當時這部作品自蘇聯捧獎而歸,因此它是“顯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前進方向”的。而在修訂版中,關于丁玲的作品及獲獎情況則全部刪節,且在提及同時代其他作家,如王實味時,則是放在新文學陣營對“托派王實味的斗爭”的相關論述之下的,這也與當時丁、王二人的歷史問題未解清相關。
(四)對文學論爭的史實介紹——替哪一個階級說話
關于新文學內部論爭的史實介紹,從前后兩個版本的不同用詞中可以看出劉在修訂初稿時體現出的小心翼翼。如在初版中提到:“但在革命文學的內部也不是沒有斗爭的,這些斗爭有時候是必要的,但有時候則不免夾雜了一些宗派主義和門戶的私風,成為不必要的浪費,造成了新文學運動在某些時候的毫無必要的損失。”在修訂版中,這段話則被修改成為:“但在革命的內部也不是沒有斗爭的,這些半爭有時雖然不免夾雜了一些宗派和門戶的私風,但也包含了相當重要原則性的意義,有重新加以研究和總結的必要。”
既然是革命內部的斗爭,那么就絕對不能不引起重視,對于那些與后來革命的主張不相一致甚至相悖反的觀點那么就是“相當重要的原則性”問題,不可忽視,并必須給予認真研究總結,嚴厲批判、禁止那些與革命相反、于革命有害的言論及論爭。
三從緒論修改看修史意識的改變
由上可看出,在1955年至1956年前期(上半年)寫就的初版,因為在“反胡風”運動結束后,中共中央傳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文學藝術和科學事業的方針的新政治氣候下,文藝界的思想漸現活躍,對于文學史實的論述,盡管有迎合新國家意識形態之嫌,但對于某些史實的描述還是盡可能真實、客觀的,且在表述中,作者的表述也更多地體現了其文學個性及學術品質。
在1957年對初版進行修訂時,由于受到當時國內反右斗爭等的影響,修訂版中出現了更多“嚴格遵照文件指示精神”的論述——堅決批判一切反對革命的、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思想、觀點、論爭、作家、作品,堅決擁護且大力弘揚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向道路上不斷前進和發展”的作家作品。劉著突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向的用意在于體現新文學發展的政治方向。他把社會主義的創作方法認為是工人階級對新文學的政治領導的體現。但是,在工人階級的政治領導下,也就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方向下,應該可以包容多種的創作方法。如果只突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種方法,必須導致文學價值的褊狹性。
[1]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2]金宏宇.新文學的版本批評[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3]黃修己.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4]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5]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6]魯迅.魯迅全集·小品文的危機[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