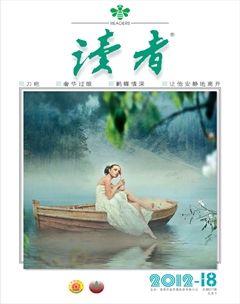國情
梁文道
前幾天和朋友吃飯,席間有人問起:“知不知道駱家輝又出事了?他居然在北京搭公交!”坐過經濟艙、排隊買過咖啡、還公布過身家財產,現在居然又以堂堂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出門擠公交。好在后來我回家上網查證,發現這條消息不過是場誤會,那個在公交車上戴著耳機、穿著格子襯衫的男子,只是長得有點像駱家輝。
這還不算完,最新的消息是,他帶著老婆孩子到桂林度假,居然不帶保鏢。難怪有網友語帶嘲諷地警告:“駱家輝,你可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真沒想到一個駐華外交使節竟能“吹皺一池春水”,引起這許多的輿論風雨。
很多人喜歡比較駱家輝和一般中國官員,贊美他平實儉樸,不尚奢華,不搞排場。也有人反過來懷疑他的動機,說他到京第一天就刻意低調,明顯作秀,乃“新殖民主義的陰謀”。可是任何一個對美國有點了解,或者在美國生活過的人都該曉得,這根本不是作秀,亦非為官者刻意為之,而是再正常不過的美國國情。
雖然美國也出過不少生活糜爛、炫富的暴發戶和“富二代”,但這大抵算得上是個“尋常人”的國度。比起老英倫風度嚴整的紳士會所,美國新英格蘭的豪門更欣賞氣氛悠閑的鄉村俱樂部。在這個總統候選人喜歡夸耀自己的父親當年如何老實工作,只是普通市鎮里的“ordinary man”的國度里,達官貴人自己背包、自己打傘、自己排隊買咖啡,根本就是一件不足為奇的小事。
然而一過太平洋,如此正常的國情卻成了一種耀目的奇觀。為什么?因為我們也有自己的國情。事實上,那種批判駱家輝散布“新殖民主義”論調的前提,正是因為咱們這兒的國情不同。
“國情”,一個陪伴了中國人多年的外交辭令。每回遇上外國政客或“反華媒體”甚或“漢奸公知”的批評,我們的標準回應就是“我們國情不同”。“國情”在這里指的當然是一種現實存在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它當然也是因國而異,不可能也不應該強求天下一統。所以,我們就可以繼續推論,由于中國官員一向不會自己背包,也不會自己打傘擋雨,故此就不能要求他們行事風格變得跟美國人完全一樣。
然而,要是我們放大“國情”這個概念的涵蓋范圍,把許多國人對現實存在的各種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看法也一并納入,整個推論可能就會很不同了。簡單地說,駱家輝那美式官員的做派或許不符國情,難道那許多中國網民對它的稱頌就不是國情嗎?
國情既是一國的現實,也是該國國民對這種現實狀況的認知和判斷。
現實和理想本該有所差異,每一個時代的人都會覺得自己身處最壞的時代,每一個社會的成員也都會嫌惡自己的社會不夠完美,由是批判,由是改變,人類方有進步可言。
總是用國情來擋掉一切外來批評,固然有套文化相對論的基礎,卻也是對理想的否定,因為它同時還擋掉了國民內部的不滿。這是以國情的現實面消解了國情的理想面,等于是在告訴人民“這已經是最好的情況,最理想的社會,不可能再好了”;如果有人想要更理想的社會,那他的理想一定是源自外國的舶來品。
新中國成立這60多年間,最大的意識形態轉折,恰恰就發生在這組“現實vs理想”的二元論上。
從前,我們高揚理想,無視現實,深信腳下大地是實現完美藍圖的一張白紙;現在我們標舉現實,漠視理想,甚至還把現實升華為理想,要大家像擁抱理想般地擁抱現實。近年學術界中種種“中國模式”的論說,便頗有這種把現實變成理想的味道,仿佛我們摸著石頭過河,摸了半天,原來已經一步步走出了之前無人料及的理想天地。而輿論界中最具代表的例子,則是前陣子某報紙那篇有名的社論,它宣稱“中國的腐敗無法通過打擊或者通過改革來消除……這是一個根植于社會發展整體水平的問題”,所以,“適度腐敗”也不妨接受。
以前大家反腐,是因為大家有一個社會不該腐敗的理想;如今我們應該順從國情,不只承認腐敗的現實存在,還要接受它。不努力以理想拉拔現實,反而要把理想拖回現實的泥沼,我不曉得,這是否也是我國的獨特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