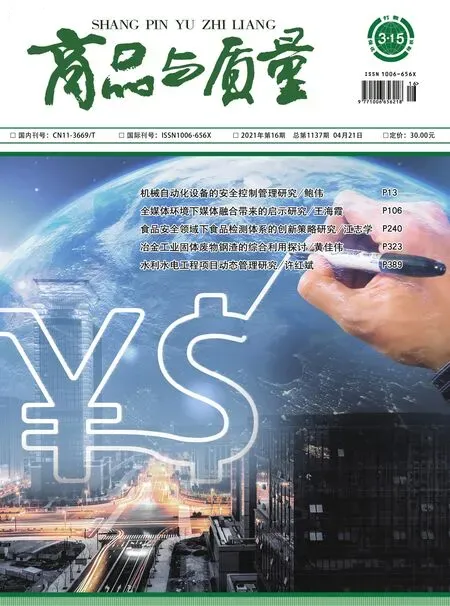電子天平計量檢定的影響因素及優化方法
胡浩 黃偉
重慶市計量質量檢測研究院 重慶 401121
電子天平應用于各行各業。使用時應注意掌握其工作原理,在檢定過程中規范電子天平的操作,定期做好維護工作,分階段處理計量問題,以保證電子天平計量檢定的準確性,延長其使用壽命,達到最大限度的方便、優勢、效益的目的,提高工作效率。
1 電子天平的工作原理
電子天平可以快速顯示出所稱的質量值,其方便性受到人們的青睞,廣泛應用于日常生產工作中。電子天平主要是根據電磁力平衡重力的原理制造而成的:通電線圈連接到秤的底部,被測物體放在秤體上,通電線圈就會進入磁場,產生電磁力,與重力大小相等[1]。發射器輸出的電流通過整流改變線圈上的電流,直到線圈回到原來的位置,電流的強度和物體的質量成正比。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電信號通過內部模擬系統在設備的屏幕上顯示被測物體的實際質量[2-3]。依據這上述的工作原理,天平具有操作相對簡單、數字顯示較快、體積小、易維護和計算準確的優點。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電子秤的種類很多,所配置的功能也不盡一樣,比如有的配備計件稱重,有的配備去皮稱重等,而且大部分電子秤平均都配有接口,可以直接連接電腦等設備,實現稱重的同時記錄功能。
2 電子天平檢定的主要內容
(1)檢定示值誤差。對于電子天平的檢定,應該先打開,充分預熱,然后用標準砝碼進行校準。負載應該從零負載逐漸向上加載,直到增加到天平的最大稱重,然后逐漸卸載,直到為零負載。其目的是驗證電子天平的空載、滿載、最小稱量以及誤差拐點是否滿足最大允許誤差的要求。
(2)檢定鑒別力與靈敏度。電子天平的檢定內容主要是檢定分度值,只有非自動指示的電子天平才會測量靈敏度,而一些半自動或自動校準裝置和數字指示天平則免于靈敏度測試。正常情況下,電子天平正常使用時,不需要驗證靈敏度。
(3)檢定偏載。在檢定不平衡負載的過程中,工作電子天平的試驗負載和不平衡負載與標準電子天平不同,需要區分清楚情況。工作電子天平的最大載荷為試驗載荷的3倍,其四角誤差等于各點顯示值與中心點差值的最大值;標準電子天平的最大載荷通常等于試驗載荷,其四角誤差等于最大值減去顯示值的最小值。
(4)重復性。對于重復性驗證,需要以加載或空載狀態為基礎,其加載方式包括滿載和半載。另外,在驗證過程中,需要做好讀取和記錄工作,每次加負荷后歸零。對于同一負載的多次測量,實際差值應控制在最大允許誤差范圍內,不得超過最大允許誤差。
3 電子天平計量檢定影響因素
(1)存放時間長。電子天平長時間不用會影響性能的穩定性。電子天平是電子產品,長期存放會出現各種問題,影響天平的測量效果。長期存放的電子天平在使用前必須經過嚴格測試和校準,以免天平內部零件不平衡,導致天平測量不準確。
(2)未預熱。電子天平作為精密儀器,在使用前必須進行預熱,使電子天平內部零件之間形成良好的匹配度,保證天平能夠準確測量。如果天平在一定時間后不能預熱,啟動后再使用,天平內的電子部件會配合不好,電子元器件和傳感器在一定時間內達不到熱平衡,測得的數據往往不能代表物質的真實情況。
(3)未預壓。為了保證檢定的順利進行,需要對電子天平進行預壓,以及工作前的預壓和預熱,這是最重要的兩個部分。如果天平不能及時預壓,就不能測試。電子秤預熱或長時間卸載后,不同部件會處于靜止狀態。如果進行稱重,各精密部件的反應性不夠靈敏,數據容易增減,示值波動過大會影響測量精度。
(4)校準不正確。目前,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電子秤出現了各種新功能。目前市面上銷售的電子秤,平均都有自己的校準功能。長期使用后,它們可以自我調節,保證自動校準。內部零件和外部結構的調整也已經自動化,小誤差不影響秤的使用。在電子天平測試過程中,有些工作人員不能認真對待,認為天平有自己的校對能力,不需要進行測試,導致顯示值狀態不合理。如零位顯示值為0,就認為電子天平合格。
4 電子天平計量檢定影響因素及對策
(1)做好電子天平的水平調整。電子天平如果長時間不用長期存放。使用前應充分對天平進行測試和校準,以保證測量精度的最佳調整,滿足各種測量需求。水平調整時間至少應為24小時。靜置一定時間后,可以保證各部分處于平衡狀態,保證天平的溫度與環境的一致性。溫度和測量環境之間也有實際關系,如果溫度不符合測量要求,會導致數據不準確,應全面進行水平調整。新型電子天平對環境要求較高,最好實現無干擾預熱,通過與環境的協調來保證測量精度。在靜態過程中,變壓器應放置在室外,以減少電磁干擾和熱噪聲干擾,從而有效保證平衡效果。預壓作業是重要環節,增壓階段和卸載階段要充分控制。預加載后,可以檢查電子天平承壓部件的運行情況。要全面增加責任心,不能盲目相信自動校準值,要用自己的經驗去驗證電子天平,嚴格執行各項操作指南的要求,做好天平的校對工作。
(2)做好環境控制。電子天平受環境影響較大,需要對環境進行全面控制。可以說,外部環境的變化是電子天平校準干擾的主要影響因素,需要對整個天平進行全面控制。電子天平環境過熱會導致測量變化和溫度漂移。除了溫度漂移之外,濕度、氣流、電磁、震動等干擾也會導致電子天平相應漂移,所以要處理好濕度、氣流、電磁、震動,保證測量的準確性。
(3)提高操作人員的責任感。在電子天平檢測過程中,工作人員必須手動操作,因此對操作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檢查人員粗心大意,會誤讀電子天平的顯示值,從而使相關測量結果不準確。只有嚴格的操作規范才能保證讀數準確,保證讀數時的角度。
5 結語
只有充分保證電子天平的準確測量,才能在各種實驗中提取準確的數據,進一步提高教學教育質量和科研機構水平。電子天平的精確測量對相關研究機構具有重要意義。只有做好電子天平的計量檢定工作,才能避免計量誤差,保證數據的科學準確性,最大化電子天平的使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