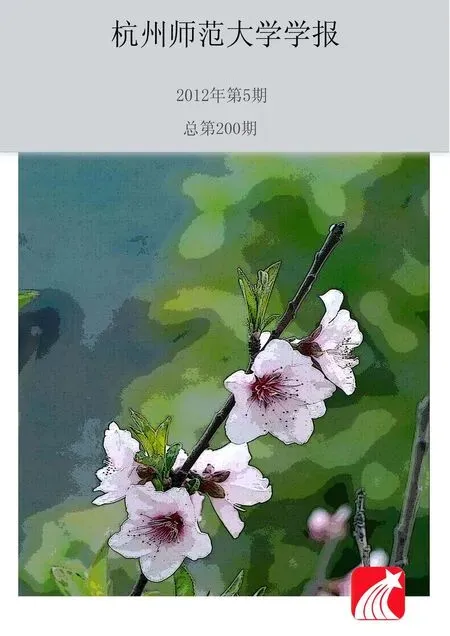《大學》與“全體大用”之學
楊儒賓
(臺灣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臺灣 新竹 30013)
21世紀儒學研究
《大學》與“全體大用”之學
楊儒賓
(臺灣清華大學 中國文學系,臺灣 新竹 30013)
《大學》原為《禮記》的一篇文章,唐代以前,這篇文章并不重要。理學興起后,《大學》的地位終于沖天而起,成為儒家經典的核心。《大學》到底提供了什么樣的思想資源?理學家又如何改造了這些思想資源的意義,使得它可以從“記”的地位躍升為儒家重要典籍?其中的關鍵在于理學家將這篇文章視為“性命之書”。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他們對此篇文章的重要概念作了系統轉移的工作,大體是將泛論的美德提升為本體論的語匯,這種改造經書性格的工程規模大而情節細致。透過理學家的改造,《大學》遂得脫胎換骨,由一般的學習綱要變為性命之書。
《大學》;明德;格物致知;全體大用;性命之書
《大學》,孔門授受之教典,全體大用之成規也……遵其規矩,自然德成材達,有體有用。頂天立地,為世完人。[1]
一 前 言
《大學》原為《禮記》中的一篇,其原始地位并不比其他48篇來得高。后來朱子將它采入《四書》,其價值迅速獲得儒林的共識,極少受到后儒質疑*質疑較激烈的儒者在中國大概只有楊簡(慈湖)與陳確(乾初),在日本則有伊藤仁齋。但伊藤仁齋與陳確的思想已走出理學的范圍,他們不該列入名單。,此篇遂成為儒門中最核心的圣經。《大學》圣經化的歷程是一出張力十足的傳奇,其在宋代之前與之后的命運截然不同。在兩宋之前,它長期埋沒在儒家的典籍之海中,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更沒有像它的兄弟篇章《中庸》一樣被抽離出來,單獨刊行過。*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曾賜進士王拱辰《大學》一軸。司馬光也曾取以講說,撰成《大學廣義》一書。這是《大學》自漢代被編入《禮記》后,最早脫離《禮記》單獨流傳的記載。這種被遺忘的狀態直到新儒學的先驅韓愈、李翱之時才有改變。韓愈作《原道》,引《大學》修齊治平、正心誠意之說,以破佛老“治心而外天下國家”之非。《原道》辭義皆淺顯易曉,此文在文化方向上的作用遠大于哲學上的意義。能從哲學的高度將天下國家與正心誠意的關系提高到體用論的層次來討論的,當是韓愈的弟子李翱。李翱可能是第一位將《大學》提升到“性命之書”*“性命之書”、“性命之學”在李翱的《復性書》中時常出現,此詞語當取自《易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性命之學”指的是一種建立在心性體驗上的形上學。秦漢以下,這種風格的學問儒者殊少問津,入宋之后,其學乃得大明,李翱可算是孤明先發的一位。層次的儒者,他作《復性書》,暢論個中旨趣。李翱的解釋不見得為后儒所接受,但他指引的方向大體為宋明儒者所遵循。
《大學》在唐中葉以后,其地位開始轉變。到了宋代,注意到《大學》的學者逐日增多,影響最深遠的儒者當是程、朱兩人。程子將《大學》當作“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朱子引程子之語,引自趙順孫編《四書纂疏》之《大學纂疏》,臺北:新興書局,1972年影印復性書院刻板,第1頁。“孔氏遺書”之說原見于程明道,原文作“孔氏之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參見《二程遺書·二先生語二上》,《二程集》,第18頁。然此說實二程所共許。。朱子編《四書》,更將《大學》置于卷首,視此書為建房子的基礎之書。*“大學是修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個地盤。地盤既成,則可舉而行之矣。”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冊,卷14,第250頁。傳說朱子臨終前三日,仍在修改《誠意章》。此說縱不可靠,但有此傳聞,也顯示《大學》在朱子心中具有極高的地位。事實上,《大學》一書的經典化最主要的關鍵即是經由朱子之手,將它編入《四書》之中,其地位才穩固下來的。《大學》也才由《禮記》中的一篇變為儒家新圣經中的一經,其地位隱然已非原來的老東家所能抗衡。*依據黃郎俊《禮記著述考》(臺北:國立編譯館,2003年)的考證,后世對《大學》此篇義理的探討達493種,《學》《庸》合論或與其他經書合論者尚不計算在內。
程、朱將《大學》當作孔門的入德之書,他們認為,在儒門典籍中,沒有一部書像《大學》這般具有基礎的意義。所謂基礎,意指《大學》一書勾勒了一個很好的為學輪廓,其他的經典是在此輪廓下逐步充實的。如果說意義的創造不能脫離“形式”的框架作用*“意義”的結構不能脫離“形式”的因素,參見博藍尼(Polanyi, Michael)著、彭淮棟譯《意義》,臺北:聯經圖書公司,1984年,尤其第五章,第101-116頁。,那么,程朱學派眼中的《大學》就是儒者成德活動中必備的實踐形式。朱子論《大學》的性質,常用的形容詞如“規模”、“大坯模”、“間架”、“腔子”等*參見《朱子語類》卷14,第249頁“某要人先讀《大學》”條,第250頁“人之為學”、“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兩條,以及第251頁“《大學》是一個腔子”條。,大體都是指“形式因”的意思。基礎的另一個意義乃是此書也有某種決定作用,如同地圖上的路標,可指引旅人往正確的方向邁進。也可以說,它具有一種定向(orientation)功能,而定向原本即是人類活動最基本的要求,是文明起源的動力之一。*參見段義孚(Yi-fuTuan)著《恐懼:人類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恐懼感》,潘桂成、鄧伯宸、梁永安譯,臺北:立緒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40-41頁。程、朱的《大學》既定下了規模,也定住了方向,這樣的“基礎”顯然已不是初階之事,而是有很深的哲學依據。
如果單看基礎之書,或單看輪廓、路標這樣的隱喻,我們有可能將此書當作一種只具初級教學作用的入門讀物,而非決定理論系統的要籍。如果真是這樣,《大學》的詮釋史就單純多了。而這樣的單純化,可能更符合《大學》的本來面目。然而,宋代的《大學》接受史實恰好相反,所謂的“入德之門”是有基本規定的,程、朱對《大學》幾處核心概念的解釋,其入門門檻極高,絕不是初階者所能理會,它與程、朱兩人核心的性理思想息息相關。宋朝以后,儒門典籍中幾乎沒有一本書或沒有一篇文章像《大學》這般引起多方的爭議。筆者認為根本的原因是《大學》的原文并沒有決定理論系統的作用,但后來卻被性命之學化了,而且此性命之學是一種極圓滿的型態。理學在傳統上被稱為“全體大用”之學,《大學》則被認為是這種型態的學問之代表。《大學》從一部綱領式的典籍變為儒門的無上秘籍,是經過一番細致的詮釋之改造而成的。
《大學》被改造的規模極大,朱子、王陽明兩人解釋“格物致知”,各出新義,引發的各種立場之回響尤多。然而,誠如唐君毅先生所說:朱子或王陽明兩人的論點如就《大學》相關章節的“隱義”而言,可以說各有貢獻,也可以說“皆是”;但如就“本文之注解”而言,可以說皆不符合《大學》原義,因此,也可以說“皆非”。[2]唐先生的論點集中在此書的“格物”論上面。“格物”論的后世回響已如此復雜,《大學》全書詮釋史的實際情況當然牽連更廣,可以說幾乎此書的每字每句都被重新打造過。我們如要從中選取重要命題作為探討的樣本,委實容易顧此失彼,掛一漏萬。
不過《大學》一書有“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三綱目之說,可視為《大學》一書的綱領,亦是《大學》詮釋史中的熱門議題。由此入手探討,似可得到綱舉目張之效。但言各有當,筆者認為其他的選擇也是可以的。以下,筆者將集中探討《大學》中兩個受到高度關注的概念:“明德”、“格物”,前者是“心性論”的語匯,后者是“工夫論”的語匯。本文也要探討一個整體性的概念“全體大用”,此概念代表一種思維模式。筆者認為理學家借用《大學》一書的架構和德目的名目,分別從心性論、工夫論以及整體思維模式三方面入手,將此書抽梁換柱、移花接木,他們從事的是國史上少見的偉大工程,也是偉大的精神冒險。改造后的《大學》基本上仍維持了文本原來的模樣,但其內涵卻蟬蛻飛躍,變成了一部扎根于天道性命深處,并表現出儒家政治哲學與文化哲學要義的典籍。
《大學》從儒門的基礎之書蛻變為無上秘義的性命圭旨之書再回返到本來面目,這一過程是經學史上最富戲劇性張力的事件。本文將探討此過程前半段的經典化之改建工程,后半段的拆解工程或恢復“原貌”工程不是本文的核心關懷。但本文探討理學家如何建構時,不能不涉及“原義”的問題,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在溯往的過程中孕育了拆解的含義,觀者自知,茲不細論。
二 “明德”論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大學》破題的大文字,朱子后來作章句,把“明明德”作為“三綱”之首。我們如要探討《大學》在儒學詮釋史上的特色,恐非得從“明德”、“明明德”開始談起不可。
《大學》最早的注家鄭玄對“明德”的注解非常簡略,他說:明明德乃“顯明其至德也”。鄭注類似同義反復,注了等于沒注。相比之下,朱子走的路就曲折多了,他注“明德”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在《語類》中,朱子更進一步解釋道:“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于中無少欠闕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明德”一詞文義清淺易曉,原可不注。朱子所以注解發揮其義,并不是出于文字訓詁的興趣,而是從根本性的哲學立場出發,是教派下的哲學性詮釋。朱子在《語類》的補充解釋中提到了“心”、“理”、“情”等字詞,顯然是典型的“心統性情”的語式。“心統性情”的命題可以上下其講,一般層次的“心統性情”之“心”乃是人心,最完美的“心統性情”之層次則是“道心”。“明德”既冠上“明”字,不可能沒有規范的意義,所以這種“得乎天而虛靈不昧”的“心”指的只能是一種勝義心,用朱子的語言來說,即是“道心”。如果我們比較朱子對“明德”與“道心”的理解*且看《朱子語類》下列這些指述“道心”的語言:“因鄭子上書來問人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靈其覺于理者,道心也。’”(卷62,第1487頁)“道心是知覺得道理底。”(卷78,第2010頁),不難發現兩者實乃同一指謂。
朱子的“道心”意指最勝義之心,在這個層次上,“心”的內涵與“性”的關系變得極微妙。明德是心?是性?朱子本人的意見未嘗沒有游移過。有學生曾問他:“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他回答:“便是”。如此說來,“明德”便是性。然而,在多數的場合,朱子是把“明德”當作一種呈現眾理的虛靈本心。朱子言語上的出入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德”字一般易作“性”、“理”之類的語言解釋。“明”字加在“德”字上面,成為形容“德”字的狀詞,“明德”因此可以解作“義理之性”。然而,“明德”不一定要往性體的方向上解釋。筆者認為朱子因為強調心在道德主體實踐上的樞紐地位,所以他設定了一種原初的道心概念,我們不妨稱呼此“道心”為朱子學意義的“心體”。此“道心”不易以一般常見的經驗―超越的二分法勉強區分之,它是天人、性心之間的綰合點,朱子的“明德”實即此“道心”之謂。
“明德”與“道心”的歸屬問題是理學的重要論辯,說重要當然極重要。但就本文的關懷而言,其精微之區別倒不是那么相關,因為不管是性是心,“明德”最起碼可以意指一種準超越的本初狀態,所以朱子才有“復其初”之說。這種原初的心靈狀態被當作爾后一切意識活動的依據,所以朱子又將此“明德”當作人的“本體”。如果對理學的語匯不太陌生的話,只要看到“本體”、“復其初”之語,即不難嗅出個中濃厚的東方式的形上學氣味。
把“明德”視為一種具有萬理的本心概念,這是依朱子的語言推衍出來的。“明德”既是“虛靈不昧”,又有“初”、“本體”的屬性,這樣的意識層次自然可以稱作“本心”。朱子的《大學》注在后世引發的爭議極多,比如后來的王學將“明德”視為“良知”,“良知”即為“本心”。這種類型的本心承體起用,知行合一,其動能特強,它和朱子型的“本心”大不相侔。但不管本心是何種型態,程、朱、陸、王理解的《大學》之“明德”都不是來自經驗性的概念,“明德”作為《大學》一書核心概念的地位也極少受到兩派學者的挑戰,這些都是確切無疑的。《大學》的“明德”與《孟子》的“性善”,兩者幾乎同化了。
然而,“明德”一詞的性質不宜抽離時代而論,再如何有原創性的概念,其出現都要有相關歷史條件的配合,而且其證明都應有文本上的依據。“明德”如果具有“具眾理”的屬性,那就應該可以在同代的經書或文獻中見到,事實不然。考“明德”一詞不但見于《大學》,也普見于經書,如《書經·召誥》:“保受天威命明德”;《君奭》:“明德惟馨”;《詩經·大雅·皇矣》:“帝選明德”;《左傳》哀公二十六年:“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易經·晉卦》:“君子以自昭其明德”。然經書固常言“明德”,言其他德如“文德”、“大德”、“俊德”、“盛德”、“懿德”者亦不少,伊藤東涯說:這些“德”皆言“他人之稱贊,而非言己心之靈明”[3],其言洵是無誤。經書中的“明德”無論如何不能實體化,“德”不是性體,“明”也不是超越的心體或性體之屬性,“明德”更不見得是人人皆可擁有的人之本質。我們看經書中這些“明德”大體用于政治場合,頗有“君德神授”之氣味,即可略知個中三昧。
“明德”一詞不但見于經書,金文中亦屢見不鮮。金文的“明德”的意義較少受到注意,我們且看下文的語詞傳達了什么樣的內容:
永念于厥孫辟天子,天子明德,顯孝于申。(大克鼎銘)[4](P.124)
丕顯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虢叔旅鐘銘)[4](P.136)
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叡尃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秦公鐘銘)[4](P.273)
余不暇妄寧,經雝明德,宣邲我猷,用召匹辝辟。(晉姜鼎銘)[4](P.266)
丕顯高祖、亞祖、文考,克明厥心,疋尹典厥威儀,用辟先王。○不敢弗帥祖考秉明德。(○鐘銘)[5](P.104)*為排版方便起見,古字均改為今體字。
上述五條引文中的前兩條出自宗周,后四條出自秦晉等國,地域與年代跨越的幅度都很大,由此可見“明德”一詞是普遍流行的概念。這些銘文中出現的“明德”的意義顯然都是正面的,就“光明之德”的語義稍加聯想,這些金文似乎承認人性是善的。商周銅器凡論及“明德”的銘文通常帶有肅穆恭寅的氣息,極具古典韻味。尤其○鐘銘文中既言“明德”,又言高祖、亞祖等先祖“克明厥心”,這樣的語言與《大學》所說“克明厥德”極接近,兩者應該可以相互詮釋。我們如采取理學家的立場,可以將這些銘文的“明德”全部解作一種先驗的性德,這樣的詮釋在文義上似乎也可以講得通。
問題在于:時代的定位點兜不攏。如果金文這些“明德”指向一種先驗的本初之德,那么,我們馬上會面臨思想史的一道難題:如何解釋孟子的“性善論”在儒學思想史上的原創性?孟子當日提出性善之說,可謂處在四面楚歌之地,不管是儒學團體內部或外部,大多不以孟子之說為然。其中,來自于儒學內部的異議之聲尤烈。孟子雖曾援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之語,以證明前人已多言及性善之語。但孟子的援語是否真的可以成為孟子性善說的援軍,恐大可疑。從各種文獻看來,孟子的性善說在當時實屬創舉。所以當時及后來凡反性善論者,皆將矛頭指向海濱鄒邑的這位大儒,而不再往上緝捕元兇。他們認為孔子及其弟子都不曾和性善說沾上關系,孟子是自我作古。
如果“明德”不能解作具有理論決定性的實體字,而此概念又確有正面意義,那么,“明德”的意義只能往非決定性的狀詞方向上解釋。說得更明白一點,“明德”之所以不能當作實體字解釋,乃因“明德”的“德”字不能用成熟的理學之性理概念理解,而只能視為泛泛之論的“德性”之意。祖先、天子、“小子”有“明德”,他們就是有此“明德”,其說不牽涉到此德性的依據為何,更不要說超越的依據了。因此,是否人人皆先驗地具有此“明德”,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如果要追根究底的話,負面答案的可能性也許還高一點。筆者的意思不是說,“明德”不能有“向上一機”;而是說,它當時并沒有這樣的發展。
金文與經書的“明德”概念具極正面的價值,但不能將它本體化為性體、心體之意,那么,其來源為何呢?筆者認為,很可能來自中國早期的光明崇拜,因而可以追溯到太陽神信仰。太陽神話是神話題材中流行最廣的神話之一*參見雷蒙德·范·奧弗著、毛天祜譯《太陽之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太陽神話牽涉到明暗的原始分化,明暗的原始分化則可視為秩序創造的第一步。在一片黝黑的原始混沌中,無時無空,沒有坐標,沒有動能,一切停滯在不可名言的黑暗中。光明對照黑暗而來,這是視覺的概念;光明也對照陰冷而來,這是溫度的感覺。感覺活動啟動了,生命也跟著啟動了。但太陽神話之所以重要,還不僅止于各種感官引發了原初的經驗而已。它之所以普遍流行,乃因陽光照耀,黑暗迸裂,世界的秩序才初步形成。沒有分裂,沒有對照,即沒有秩序可言。太陽神話在所有神話中,所以居有始源的位置,乃因太陽神話之象征牽涉到本體論的優越性之問題,只有光明才會帶來萬物的存在。*卡西勒早已說過:所有民族、所有神話的開辟章主題多集中于“光”之創造,參見E.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Manheim trans, New Haven: University of Yale Press, 1957, vol.Ⅱ.pp.94ff。
太陽神話在上古中國的政治中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上古人君常被比作太陽。商代國君常以日為名*參見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收入《王觀堂先生全集》,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68年,第2冊,卷9,第419-432頁。,可想見,殷商君王之資格當帶有太陽的神性。不僅殷商先公先王如此,古圣王列傳中的“帝”莫不如此,其中黃帝、帝堯之太陽神性格,更是強烈。黃帝其面四方,影響力強,實質上是一種最高神的歷史化,因此,其神的性格不免兼攝地祇、戰神、始祖神等功能。但就核心義而言,他的性格當是天神,尤其是太陽神。*參見拙作《黃帝四面——天子的原型》,收《廖蔚卿教授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第181-214頁。帝堯的真實面目也是如此,帝堯的真實身份在《尚書·堯典》一書中已作了相當完整的體現,此篇中的“寅賓出日”等儀式行為,無非就是對太陽神的禮贊。“欽明文思安安”的形容詞,也可看出從“光明”象征轉化過來的痕跡。《尚書·堯典》是儒門圣典,此圣典可視為文明史上常見的“從神話到經典”的一則典型敘述。*參見馬伯樂著、馮沅君譯《書經中的神話》,長沙: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1939年,第3-20頁。
太陽神話在上古中國的影響是全面性的,楊希枚先生早年即從“語言”及“生活”兩層面,分別探討太陽神話在上古生活世界的分布。*參見他的兩篇著作《中國古代太陽崇拜研究(語文篇)》《中國古代太陽崇拜研究(生活篇)》,兩文皆收入《先秦文化史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依據楊先生的舉證,舉凡“神”、“帝”、“天”、“皇”、“昊”、“上帝”莫不帶有光明的意象,如“明明上天”、“明昭上帝”、“陽之精氣曰神”等等皆是。事實上,世人對最高神祇所作的最高的贊美詞,主要皆取自“光明”的意象。
筆者認為“明德”出現的背景和經書中“昭明上帝”、“皇矣上帝”、“倬彼昊天”、“明明上天”出現的背景是一樣的,和古圣王的出現背景也是一樣的。不管是“欽明文思安安”的帝堯、“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的祝融,或是五帝系統中的任一帝,我們都可以看到光明的天神之影子。我們比照德目―神祇―帝王這三組例子,不難發現它們的構造都是以“光明的意象”加在“名詞”之上的形式組成的。這些名詞可以是天神、圣王,也可以是道德語匯。類似的表達方式反映了同一時代的思維方式,在“光明”意象流行的時代,很難相信此時的“明德”一詞可以拉到孟子“性善”的思想水平上作解。
“明德”的“明”要追溯到光明源頭的太陽神話,其“德”字也應當回歸到此字的歷史脈絡。德者,得也。物得之于天者,其所得可成為其物之性質。“光明”乃太陽的基本意象,也可以說是天神的屬性;合理推測,可以說:人也具有太陽的光明屬性。這樣的德顯然有正面的含義。然而,從有“正面的含義”到“嚴格的哲學概念”之確立,發展的歷程是必需的,而這樣的歷程不是短時間可以達到的,不難想象其中要跨越多少的理論關卡:有沒有普遍的人性?有沒有執行此天賦美德的道德動力?有沒有意志與情、理的角力問題?等等。從孟子到程、朱、陸、王諸理學家,他們的性善論的“性”字,都蘊含了本體義。如果說在孟子手中,其義仍只蘊含而未明言的話,至少,理學家眼中的“性善論”之“性”字乃是實體字,形容詞“善”乃是名詞“性”的屬性,此善性之性,即為“體”、為“本”之意。《大學》的“明德”可以往這樣的方向解釋嗎?
一般認為嚴格意義的本體論述出現的年代不會早于魏晉,即便年代再放寬,可以解釋的空間恐怕也不會太大,筆者不認為《大學》中的“明德”可以有“具眾理以應萬事”的含義。如果我們不以本體論的語言定位“明德”,而仍想將此詞語解作一種先驗(先天)的語匯的話,大概只能從宗教經驗的論述中尋找。筆者此處所說的宗教經驗意指某種特殊的心性突破經驗,冥契經驗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在東西各大宗教傳統中,都可看到某些類似的冥契報道,這些報道往往運用了“光明”的意象。*光明意象與悟道或道體的關系參見印順《解脫者之境界》,《佛學三要》,臺北:正聞出版社,1987年,第206頁;拙作《先秦思想的明暗象征》,《中國文化與世界》第6輯,上海,1998;M·Eliade,“Experiences of the Mystic Light”, in The Two and the One, J·M·Cohen tran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理學家中,楊慈湖、高攀龍都曾提到他們經歷過一種“光的體驗”,這種體驗帶給他們極大的影響。筆者認為莊子的“虛室生白”及“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之說指的大概也是類似的境界。然而,《大學》一書的內容精簡明確,后世學者雖常以心體、性體、體證之語解釋“明德”,筆者相信這些所謂的證悟之語都是勉強解釋出來的。怎么看,《大學》此書的“明德”的“明”字只能是泛論的贊美詞,“德”也是一般意義的德行或德性之義,后世所說的先天(或超越)向度是沒有的。
如果“明德”的“德”不能作實體義解,《大學》一書中出現的“心”、“意”、“知”等語匯,同樣也沒有本體義的功能。在心性論當令的時代,這些意識語匯先后都曾躍上歷史的舞臺,被視為蘊藏了宇宙與人生的奧秘。王陽明言“良知”,劉宗周言“誠意”,其“意”字、“知”字被提升到本體的地位,觸及到了造化的奧秘,這樣的用法顯然都是他們自己的思想引申出來的,《大學》一文本無此意。羅整庵和王陽明論學,力主“知”從來沒有作本體義解的;陳確論《大學》,力反其師劉宗周的論點,主張《大學》的道德殊無可觀。羅整庵和陳確不見得可以領略王陽明、劉宗周之學,但就文本考據論,他們的批評倒是說得過去的。《大學》中的主體性語匯都沒有超越的意義,后儒的解釋是后儒的,我們只能依后儒的思想格局去理解后儒理解的《大學》,不能將后來的詮釋當作經典的原意。
三 “格物”論
如果《大學》一書中的重要名詞如“心”、“意”、“知”等皆是泛論的意識語匯,并沒有超越的本體之義,那么,宋代以降儒者所重視的工夫論如“誠意”、“正心”等,在《大學》的原文中,也就沒有承體起用、返本歸源之類的意義。《大學》一書中影響后世最深遠的工夫論莫過于“格物窮理”之說,“格物窮理”與“誠意”、“正心”的語匯形式不一樣,因此,不宜一體看待,似乎也不宜輕率地一筆抹殺。但統觀全局,筆者認為這些工夫論語匯的情況差不多,它們在理學詮釋傳統中的意義和經典的意義相距極遠。理學“格物”論的工夫論基礎也是落在超越的本性,其說能否成立,也要受到相同待遇的檢視,本節將討論“格物”說如何被打造成理學語言的模式之歷程。
“格物”說的名氣甚響,“格物”牽連的問題尤多。“格”字在甲骨、金文中常見,“物”字也可見,但“格物”一詞在先秦文獻中卻只見于《大學》一書。由于《大學》一書在后代的影響極大,“格物”在程、朱理論系統中又具有關鍵的位置,“格物”經由后儒的詮釋,其內涵遂不斷擴充,“格物”涵蓋的范圍也由心學延伸到后世科學的領域。但外延廣者往往內涵薄,“格物”過度解釋,其意義反而難以澄清。筆者認為在理學的范圍內,格物論基本上是和理學家關心的核心價值之心性論結合在一起的。換言之,他們理解的格物論是經由一種改造的過程后,才被吸收進《大學》的教義內的。
《大學》在理學傳統中居有核心的地位,然而,如果細考《大學》有關“格物論”的原文,不難看出它的內容其實很單純,單純到了簡略的地步。原文的脈絡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依據朱注,這是《大學》中的“經”;“格物論”另外一條相關的文字是“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依據朱注,這是一條殘缺的“傳”。*因為朱子認為其文殘缺,所以才補上一段文字,以完其義,也才引發后世長達八百年的議論。由于原文甚簡,所以乍看之下,我們不太容易澄清“知”、“物”、“致知”、“格物”的真實內涵為何。倒是漢唐儒者對于“致知格物”之說有清楚的解釋。鄭玄注“致知在格物”云:
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6]
孔穎達的注解比較詳細,但疏不破注,他尾隨鄭注,其解重點還是落在“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之好”這類話語。鄭、孔兩人看“格物致知”,將它看成一般性的道德格言,認為它所說僅表示行為結果與人的人格間有種緊密的相應關系。更確切地說,也就是行動者與對象有感應的關系:善行有善應,惡行有惡報。工夫論、心性論、形上學這些話語都是搭不上邊的。
鄭玄、孔穎達的注解很常識性,很可能他們認為原文的意思就是這么簡單,沒有太多可以發揮的空間。鄭、孔的注解能否成立呢?筆者認為有可能成立,它有文本內在的依據。儒家一向強調人君的感化力量,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大學》繼承了儒家道德政治的論點,也很重視道德在政治上的感應效果。此書說:“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又說:“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類此道德感應之言充斥《大學》一篇。依據鄭、孔之說,“致知”乃是“招致某種人格境界的知”,“格物”則是“招來相應于此人格狀態的回應”,“格物致知”意味著“人(尤其指執政者)的人格層次會招來百姓相等層次的響應”。一言以蔽之,《大學》的格物論說的就是人君道德奇理斯瑪的感召論,鄭、孔的注解是有文本依據的。
鄭、孔的注解不但在《大學》文本中可以找到內證,在孔、孟、荀的政治哲學中可以找到支持的文獻,在20世紀末出土的郭店儒簡中,我們也可找到相類似的論點,《成之聞之》一文所說即是人君的道德感化論,人君治國,“身備善以先之”。《論語》中有名的難解之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們現在透過《成之聞之》的解釋,才知道它的意思是說:百姓只能依人君的道德感染力自動去行,強說強勸是沒用的,這是道德感應說的極致說法。郭店儒簡和子思學派關系很深,而子思對人君的感應論一向深具信心。*子思佚文有言:“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不令而行,誠在令外。圣人在上,民遷如化。”說得最是明白。郭店儒簡的感應論或感召論只是再度確認儒家政治哲學的一項老觀念罷了。
原文很簡略,但依《大學》文本內證、先秦儒家政治學傳統以及出土文獻佐證,鄭、孔的注解很可能即是正解。正因人君的感論或感化論是儒門通義,所以鄭、孔的注解才會將格物說注得這般稀松平常。既然如此,它后來何以會變得這么重要?此事真是費解。但有一件事情可以確定,《大學》“格物說”所以具有“性命之學”的性格,朱子作《格物補傳》是最根本的原因。朱子認為《大學》一書有缺文,它的缺文剛好落在最重要的“格物致知”上面。朱子根據他對經典的理解,以心傳心,填補其文。《大學》一書的空白,恰好成為容納朱子思想大幅度跨越的創造之支票簿。后代的學者不管贊成或不贊成朱子對“格物致知”的解釋,他們提出自己的理論時,背后總有朱子“即物窮理”的學說作對照面。但由于《大學》一書的思想走向并不確定,其文過于簡略,朱子的《補傳》影響力又大,所以他們提出與朱子不同的主張時,往往也采取類似朱子的手法,或作補傳,或移章句。*最早改編《大學》次序的學者當是程顥,但朱子的改本影響最大。朱子之后,代有改著,詳情參見程元敏先生《大學改本述評》、蔡仁厚《大學分章之研究》。兩文皆收入吳康等著《學庸研究論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第61-134頁。又參岑溢成《〈大學〉之單行及改本問題評議上·下》,《鵝湖》第101、102期,1983年;以及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年。后世儒者即使采用不動文字的“古本”,其解釋模式依然走的是超越論的途徑。《大學》是部神奇的經典,它的素樸的文字滋養了后世不斷蔓延的詮釋,它的混沌的空缺變成反映注者心態甚于反映“原作者旨趣”的羅斯特試紙。
《格物補傳》是我們了解《大學》地位升降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下文還會再細論。但《大學》正典化的起點不是從朱子開始,而當從中晚唐的李翱開始。最早的注家鄭玄不見得沒有人性論或形上學的理念,但他注解《大學》的“格物致知”之論,并沒有帶進太多性命之學的消息。李翱之后,“格物致知”的形上性格就不斷加強,筆者認為這種形上化的途徑大抵有兩條,一是李翱、陽明之路,一是程、朱之路。籠統而言,也可以說前者是心學之路,后者是理學之路。
《大學》所以在哲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李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李翱注解“致知在格物”,說道:“物”是“萬物”,“格”是“來”、“至”的意思,“致知在格物”意指:“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7]
“格”字釋“來”或“至”,訓詁上非不可通,鄭玄、孔穎達也是這樣理解的。但“致知在格物”解成“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著于物者,是致知也”*原文“不著于物”作“不應于物”,其義難通。《佛祖歷代通載》引作“著”,其義較勝。,這種解釋恐怕是李翱自創的,李翱將“格物致知”解成性體與萬物的關系。性體明照即為“致知”,“致知”的“知”不是知識義,而是一種類似“般若智”或“德性之知”的創造性直覺。同樣,性體明照中的萬物并非以“對象”義呈現在性體前,而是“萬物皆為性體所貫穿”。《復性書·上》有言:“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這大概就是李翱所說的“格物”。性之與物,正如體之與用。這樣的“格物致知”基本上是境界語,“格物”是境界所至的自然產物,它沒有獨立的意義,學者根本不必做“格物”的工夫。
李翱的格物論將“格物”心性形上學化了,這樣的詮釋與魏晉隋唐以來的思想史走向是一致的。在心性論仍發揮影響力的時代,心性化的“格物致知”之說即不可能缺席。程門弟子呂與叔的“窮萬物之理同出于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致知。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謝上蔡的“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楊龜山的“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等等,皆屬此一詮釋路線。*上述的說法以及朱子對他們的批判,參見《大學纂疏》第59-61頁。這些解釋只能出現在心性論主導的年代,兩漢不與焉,魏晉則無意與焉,細節茲不贅述。筆者在此只想指出一點:在形式上最接近李翱的用法者當是王陽明,李翱、王陽明的格物論可以代表一種重要的類型。
眾所共知,王陽明思想成長的歷程,可以說就是不斷與程、朱格物說搏斗的歷史。他年輕時,遍讀朱子之書,還依照他自己理解的朱子格物方法,對著官署中的竹子,不眠不休,耽思其理,結果格出一場大病。[8](《年譜一》,P.1223)以后,他就過著精神流浪的生涯,做詩人,煉丹道,出入佛老。37歲時,他被貶放到窮山惡水的龍場驛已三年,《年譜》記載他一開始還無法看破生死一關,乃“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他還想到:圣人落此地步,該如何自處?久而久之:“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8](《年譜一》,P.1228)
王陽明在龍場驛大悟格物致知的道理,但當時所悟之具體狀態為何,王陽明沒有特別的描述,此事相當可惜。但王陽明對《大學》始終非常重視,這是事實。他對“格物致知”有一套完整的理論,足以和朱子之說并峙。在《大學問》*參見劉述先先生的解釋,見《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第492-496頁。[8](《續編一》,PP.968-972)一文中,王陽明從“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破題,洋洋灑灑數千言,他平日的《大學》理念至此宣泄無遺。首先,他將《大學》所說的“知”界定為良知。王陽明的良知是本心的概念,“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其次,他將“格”視為“正”。良知靈昭明覺,它在明覺的作用中自然就有存有論意義的匡正功能。第三,他將“物”界定為意識所在之事謂之物,所以他說的物其實包含了事與物,事尤為大宗。王陽明良知學中的“物”絕無實在論的意涵,它意味著在脈絡中顯現的事件(event)之意,而且它也預設著“在意向性(王學的語言是‘良知’)中呈現”的向度,noesis和noema一體難分。“知”、“格”、“物”皆已另出新釋,“致”字的意義自然也跟著改變,成為擴充、推廣之意。
王陽明的“格物致知”說非常簡要,“致知”就是“致良知”,“格物”就是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王陽明的論點與李翱的相當接近,兩人的“物”都是明覺感應下的物,而不是認知意義下的對象。他們的“格物論”都是虛的,“格物”其實無一物可格。他們之間的差別在于:李翱的“格物致知”說強調物物在本心流行中自如,這樣的“格物”是果地事,無工夫義;王陽明則強調良知的道德判斷能力,它是是非非,使萬物由不正轉正。重點雖然不同,但這兩種說法都是道德主體籠罩下的論述。
如果說李翱、王陽明等人的“格物說”完全沒有認知的意義,“物”也無法突顯獨立的性格的話,另外一支影響力很強的解釋則著重知性活動與終極的體證境界有極密切的關系,其主要代表即是朱子。
朱子一生的學問盡瘁于《大學》一書,又尤其注重“格物致知”的概念。他認為這個概念太重要了,而《大學》原文所說太簡,因為中間有些重要段落業已脫落,后人不得握其樞要。因此,他揣摩前賢原義,作《格物補傳》,匡濟其事。《格物補傳》重點強調:(一)人心有知而萬物有理;(二)學者要務當即物而窮其理;(三)最后要豁然貫通,使眾物表里精粗無不到,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問題是:什么叫“即物窮其理”?物的范圍有多大?理的內容為何?什么叫“豁然貫通”?
朱子認為《格物補傳》所說,乃承襲程伊川思想而來。事實正是如此,他在《文集》《語類》《集注》中,多方引程伊川的話語解釋其事。*如底下引文所說:“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引自《大學纂疏》,第48頁。簡言之,“格物”不能只格一物,亦不可能格盡天下之物。“一”,不合法;“少”,不可以;“無限”,不可能。我們只能說:工夫論中的“物”的范圍是不確定的,但它一定是雜多的,至于雜多到什么程度,此事無法確定。學者該做的事,只是不斷地因已知之理而窮究之。程伊川當然也強調“格物”還是免不了要有選擇,“道德之物”具有實踐的優先性。所以他提出警告:“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于慈,子止于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9](P.50)又曰:“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其得之尤切。”[9](P.50)
從實踐的過程看,程、朱不能不承認事情該有輕重緩急。但就實踐的范圍看,很難說有哪件事是道德意義上不相干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每一事物都落在具體的情境中,學者處理它時,需要考慮各種不同的具體因素。但同樣重要的乃是學者還要反過來從各種異樣的具體之理中,推拓上去,窮究至極,深思它們同出一源之太極。所以就實踐的觀點看,隔斷紅塵,閉目反思,冥契太極,這樣的途徑是行不通的。即使行得通的話,這樣的道德實踐也不是程、朱認可的儒家之道德實踐。“理一分殊”是程朱學一個重要的概念,這個概念不僅適用于本體宇宙論的論述,還適用于所有的致知格物之活動,它含攝了許多的層次。程、朱一再強調:學者不管要體證總體之太極,還是分殊性之理,他心里應該先了解,這個太極一定有許多的殊相之理,太極與這些殊相之理有不一不異的關系。學者一定要窮盡這些殊相之理,才可以理解“太極”之具體內涵。
程、朱和佛老取徑不同,甚至和儒家其他學派重點有異的地方,最明顯的莫過于程、朱強調下學—上達、精里—粗表、純一—雜多、太極—眾理之間的相融。學者格物有成,非得同時證悟“太極與眾理圓融無礙”的層次不可。如果他只了解統體一太極,這就是著空;如果只知眾理平列,這就是滯末。真正的道德不能偏于一曲,而當理會事事物物之理與總體之太極,兩者乃是差異中之詭譎同一。所以就工夫而言,學者該如何做,答案自然呼之欲出了:
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大學纂疏》,第48頁。類似的語言處處可見,如下所言亦是:“有人只理會得下面許多,都不見得上面一截,這喚做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看得大體,都不就中閑細下工夫,這喚做知得里知得精。二者俱是偏,故大學必欲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則無不盡。”又如所說:“必致知之功到,而吾本然之體皆有以周偏昭晰,本然之用皆無所隔絕閑斷。體常涵用,用不離體,其實非兩截事也。”
萬物一定要窮到表里精粗一貫,吾心一定要致到全體大用皆明。不能跳開過程、雜多、經驗,這是程、朱永不放棄的立場;而太極一定要在一一事物中彰顯,這更是程、朱永恒的執著。反過來從主體講,吾心一定要一一反映萬物之理,同時此萬物之理也要在心體流行中顯現,這也是程、朱始終的堅持。他們認為:這是“白的虛靜”與“黑的虛靜”的差別,儒家與佛老的界限即在此處。
至于豁然貫通如何可能呢?程、朱將此事視為自明的道理,他們勸學者:不要怕最后不能貫通,只怕學者沒有踏著實地用功。什么時候可以貫通?學者要達到什么修養層次,萬理才可通而為一?程、朱認為“到得豁然處,非人力勉強而至者”,此事急不得。程、朱雖然沒有說明“豁然貫通”的理論依據,但我們也許可以迂回前進,嘗試厘清其間的關鍵。
筆者認為:從“格物”到“豁然貫通”的路程不是直線的,王陽明格竹成病,恰好可以給我們提供反面省思的教材。真正引發學者豁然貫通的心理經驗,其動能不是來自格物致知的饾饤歷程,而是“主敬”的工夫提供了充足的動能。因為主敬可以收斂身心,造成異質的跳躍,豁然貫通。貫通后的世界圖像乃是純一與雜多融會,超越與經驗互入,這就是“眾物表里精粗無不到,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的境界。程、朱說:這是《大學》的意思,他們發揮的是孔門教學的精義。[10]
朱子后,代代都有人對“格物”說提出新解,到明清之際,已有學者宣稱古今學者對《大學》格物理論的注釋有72家。*參見劉宗周《大學雜言》,《劉宗周全集(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第771頁。72家之說后來成為套語,清儒亦多沿襲其說,徐養原《格物說》、謝江《格物說》亦采此語。引自《經義叢鈔》,《皇清經解》,臺北:藝文印書館,卷1388,第25-26頁。此說不管有無夸張,但《大學》注解紛紜不定,這是事實。這72家中,固然有如司馬光那般素樸的解釋者,但主流的講法都是將“格物”說抬高,程、朱、陸、王的“格物說”都預設了一種超越主體的存在,他們的“物”也都是超越經驗層面的“物之本相”。“物”、“知”被抬高到“物格”、“知至”的果地事。這樣的高度,恐怕《大學》原作者從來都沒有幻想過,更不要說碰觸過了。至于最早的注家鄭玄、孔穎達看了,恐怕也要舌撟不下了。
四 “全體大用”論
《大學》一書的架構從誠意正心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個由內而外、逐步擴展的實踐歷程。《大學》在理學思想史上之所以占有重要的位置,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給儒家提供了一種特別的政治哲學。眾所共知,儒家的主流政治主張基本上是道德政治,而道德政治的一個主要設定,乃是認為執政者施政之良窳與其人之道德攸關,更進一步講,兩者甚至是因果關系,政治領域的成敗建立在個人道德修養的基礎之上。*關于儒家的道德政治,論者已多。最近的研究參見江宜樺《〈論語〉的政治概念及其特色》,《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24期,2008年,第191-233頁。其次,儒家的道德政治主張:執政者如果道德意識強,他甚至可以不用言說,百姓自然而然會受到感召,變成良民。道德政治的范圍超出了政治的形式之外,它包含了非言說的德行統治技術。*有關非言說的治術,參見佐藤將之《戰國時代“誠”概念的形成與意義——以〈孟子〉、〈莊子〉、〈呂氏春秋〉為中心》,《清華學報》,2005年第35卷第2期,第215-244頁。第三,儒家的道德政治相信人的道德情感是逐漸擴充的,而其量是無止境的。它自親親到仁民到愛物,無不關懷。上述所說要點,《大學》一書表現得特別清楚。但《大學》這種主張在《論語》一書中已看得很清楚,孟子、荀子在這點上也表達了同樣的主張,《大學》的論點可以說是儒家的共法,它只是以綱要的方式,突顯了儒家政治哲學的論點而已。
《大學》的修養論綱架基本上為理學家所繼承,但其繼承已脫胎換骨,在形式的相似性下增添了異質的內涵。這種新添進去的內涵明顯地表現于南宋后期真德秀的《大學衍義》[11]以及明中葉丘浚的《大學衍義補》[12]兩書之中。丘浚的著作是對真德秀著作的補充。真德秀之書依據朱子的理論,以“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作為全書主軸。在這四條綱要之下,真德秀又分成幾個子目,如“格物致知之要”下面又分“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四項,依序舉前人言行以為例證,用以警惕人君。與《大學》原文相比,真德秀的架構缺少了“治國、平天下”的部分,后人遂不免認為其書在結構上有所不足。于是到了明中葉時,乃有丘浚的補充之作。《大學衍義》與《大學衍義補》這兩部書常被視為儒家政治哲學尤其是理學家政治哲學的代表作。這兩部書對實際政務的影響如何,固難確認,但至少它們是后代君王施政時必備的參考書。在經典論述仍屬政權正當性基礎的年代,《大學》一書應該發揮了我們今日難以想象的作用。
《大學衍義》與《大學衍義補》所理解的《大學》到底是什么樣的典籍?不妨先考察真德秀。作為南宋末期的重要學官,真德秀的政績如何,時人及后人多有議論,他的出仕似乎是個失敗的案例。但就政治哲學而言,他的貢獻極大。真德秀很自覺地將《大學》代表的道德政治運用到實際政務上去,而且設計了相關的配套理論。真德秀就像正統理學家一樣,主張理想的政治是學事合一,有體有用。老莊言理不及事,所以是“天下有無用之體”;管商言事不及理,所以是“天下有無體之用”。[13]好的政治是體用并舉,所以他作《心經》與《政經》兩書以呼應之。兩經并舉,很難不令人想到“體用論”的格式。《心經》側重內在的道德意識,《政經》側重邦家之事,結合《心經》與《政經》兩書的關懷為一者,即是《大學衍義》。此書想傳達的,就是“本之一身為體,達之天下為用”的“有體有用”之“圣人之道”。*關于真德秀《大學衍義》,參見朱鴻林《理論型的經世之學——真德秀〈大學衍義〉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食貨月刊》(復刊),1985年,第16-27頁。
真德秀作《大學衍義》一書,自視為完書,但就形式看,“治國”、“平天下”似乎當有獨立的位置,“大用”的格局才算完備。丘浚的工作正落在此點上面,而《大學》所代表的“全體大用”的意義,他的發揮也特別徹底。我們且看丘浚在《大學衍義補·序》中表達的論點:“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于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乎億兆人民之生。”這一本書很重要,它是“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丘浚的衍義之語由一堆贊美之詞堆砌而成,對《大學》的評價之高無以復加,此書骎骎然竟有“無上至極宇宙第一書”的意味。但他的贊美是有理路的,此書之所以重要,關鍵在“全體大用之學”這樣的內涵上。“全體大用”一詞的內涵可以更進一步規定為“原于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
“體―用”、“心―理”這組用語是理學家《大學》之學的核心義,丘浚在文后又衍其義道:(一)“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乎萬事”。(二)“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為體,亦有所不全矣!”(三)“由乎內以及外,而終歸于圣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丘浚設定了“心為體、為本,事為用、為末,但體用、本末一貫”的格局,他認為《大學》一書所要表現的,就是這種主張。依據丘浚的注解,天下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偶然的,都屬于道德實踐的范圍。少掉任何一事一物,道德即不完整,人的本體也就有了欠缺。由于本體是無限性的,所以儒者的道德實踐也是無限的,丘浚的論點代表理學家一貫主張的“無盡的責任倫理學”。
丘浚的解釋一般認為源于程、朱理學。*關于丘浚的《大學衍義補》,參見朱鴻林《丘浚〈大學衍義補〉及其在十六七世紀的影響》,收《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辨與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體用”是中國哲學的重要術語,宋代以下,其施用的范圍無所不至,波沿至今,效用仍在。關于“體用”一詞的沿革,晁說之、王應麟以下,前賢多有探討。明末清初,顧炎武、李二曲往返修書討論,尤為著名。現在大概可以確定:“體”、“用”分用的情況已見于《易經》,兩字并用的例子在《荀子》《周易參同契》等書中也已見到蹤影。但先秦兩漢時期的用語之心性形上學內涵不強,就嚴格的哲學語義考慮,“體用”聯用的語組可能起源于魏晉,王弼、鐘會已有是語,后來的道、佛兩教更堂而皇之地使用之。
至于“體用”成為儒學的重要詞匯,應當在北宋朝才發酵。體用論的論述首先是在政治領域里出現,劉彝上朝對召時,說及其師胡安定的教育乃是“明體適用”之學[14],其功績非王安石所能比擬。劉彝此對問極有名,對問背后應當有不同學派競爭儒家正統的用意。接著政治性的語匯之后,“體用”成為儒學重要的心性形上學語匯也在此時出現了,與程伊川活動大約同一個時期的邵雍、周敦頤、張載等人大約同時展現了“全體大用”之學的論述。邵雍說:“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皇極經世·觀物內篇》)張載說:“兼體無累。”(《正蒙·乾稱》)又說:“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正蒙·神化》)兩人所說的“體用”都具有高度的哲學內涵,應當就是典型的體用論語式了。但無可否認,最重要的體用論當是程伊川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說。自程伊川開始,“體用”從一種哲學性格極強的詞語變成了一種思維方式,被理學家普遍接受。“體用”這組詞語到了朱子以后,用得更是頻繁,它儼然成為理學論述的公共形象,其佛道的源頭反而湮沒不彰了。*有關“體用論”的歷史發展,參見張立文《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天道篇》之《體用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321-358頁;楠本正繼《全體大用の思想》,《日本中國學會報》第四集,1952年,第76-96頁。
追蹤體用論在儒學體系的滲透史,大致上可以將胡安定、程伊川、朱子三人的用法當作三個逐漸深化的階段。胡安定在理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在教育領域,經學史的意義大于哲學的意義。“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是體,皇極之道是用,這種體用論的用法比《大學》本文所說的“本末”還要寬松,但可以看出胡定安將儒家的道德實踐項目編成本末先后的企圖。“體用”論述到了程伊川手中,意義脫胎換骨了。程伊川使用此語是在他給《易經注》寫的序言里。《易經》此書異于儒家其他經典者,在于此經既有心性形上學的思想,又別具一副獨特的象征符號。此象征符號以自然界的8個原始意象為核心,兩兩重卦,共得64卦。此64卦用以指示天下的事事物物,從人事行為以至自然事件,無不包括。就全書結構看,此書論“神”、“道”的心性形上學語匯如果可視為“體”,則64卦的卦象所指涉者當然可以視為“用”。依儒家連續性的世界觀之思維模式,這樣的“體”與“用”被視為同源而發,而且其差別并非本質的不同,而是“顯”、“微”的發展歷程之差距而已。
《易經》確實是很有資格代表“全體大用”思想的典籍,理學家看待此經,通常也這樣定位。但此經不管在歷史傳承或經書內涵方面都是復雜繁難、聚訟紛紜。以朱子這么著迷宇宙論、存有論的儒者,都覺得此書糾纏太甚,因此,沒有將它列為和《四書》同一等級的經典。相比之下,《大學》的眉目非常清晰,八目中的“心意知物”與“天下國家”大致上可以“身”為中界點,分成內外兩區域,“內”、“外”的范圍又很容易和“體”、“用”的范疇同化。所以從朱子開始,體用論的表達方式和《大學》遂密不可分。“全體大用”一詞即出自朱子《格物補傳》所說:“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他論“明德”概念,也常使用此一術語,如云:“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于日用之間。”[15](第2冊,P.484)不管言“格物”或言“明德”,他都用了“全體大用”的語匯,顯然在他心目中,《大學》代表的就是全體大用之學。后來的真德秀、丘浚所以有《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之作,而且以體用論的思維貫穿全書,都是受惠于朱子而善紹善繼。至于在《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之后,陸續有“衍義”體的著作大肆衍義,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詳情參見朱人求《衍義體:經典詮釋的新模式——以〈大學衍義〉為中心》,未刊稿。但筆者認為這些“衍義”之書多少還是受體用論思考方式的影響。
當理學家以體用論的思考重新詮釋《大學》一書時,《大學》的整體架構即發生了質的變化。《大學》的真身如果是學習綱要之書,則不難發現,此書在原有的學習歷程或架構中,成德的依據以及道德事件的性質是沒有被觸及的。但體用論的模式介入之后,所有的政治、社會領域的事件都被視為是有厚度的事件,它們都是一種作為價值與存在根源的本體所生發出來的“用”。在這種思維模式下,任何只重本體而將外王事務視為“末”、“外”、“俗”的學問——理學家認為佛老即如此——都是不可取的。反過來講,凡是只重政治社會領域本身的工作,而不知這些工作具有本體論的意義者——理學家認為佛老以外的諸子或俗儒之學皆如此——也是不可取的。*朱子《大學章句序》說:“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李幼武編纂《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引朱子說:“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嘉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臺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12,第13頁)所說亦是此意。類似的話語在理學文獻中不時可見,茲不贅述。理學家兩面作戰,同時匡正方外之學與方內之學的不是。
體用論是理學很重要的思考方式。前儒如晁說之、顧炎武等人皆認為理學有取法乎佛教。就心性形上學的內涵來講,理學興起前,佛老已充分使用這套語言,這是事實。但誠如呂澂所說,佛教重性寂,其法性共相等語皆不可作本質觀,其修行論述也很難使用體用論的語式思考。*呂澂之言在其著作中不時可見到,唯識宗的立場固如是也。比較密集的討論參見他與熊十力的書信往返,尤其他的第五封答書。參見洪啟嵩、黃啟霖合編《呂澂文集》,臺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第287-289頁。在緣起性空與息妄歸寂的法印限制下,體用論的體與用都不免帶上如真似幻、兩皆不取的色彩。從儒家的觀點來看,其體用不免只是姿態,虛欠不實。所以牟宗三先生力持理學的體用論無取于佛教,即使最接近華夏心性論模式的真常唯心系統所說者,本質上仍與中土的體用論不同*參見牟宗三《佛教體用義的之衡定》,此文收入《心體與性體》第1冊,臺北:正中書局,1987年,第571-657頁。,筆者認為牟先生的分判是很有說服力的。因為體用論的架構很難不帶有真實(“誠”)、動能(“氣”、“神”)的屬性,“物與無妄”、“不誠無物”是儒家形上學的基本設定。《大學》一書的“物”指向了心身家國天下,一旦《大學》變成了全體大用之學,這些“物”也會齊登法界,它們的性質也都會被視為是體現誠體的真實無妄。但佛法則很難不認為這些論述只是違章建筑的“戲論”,所以雖然體用論語式的創造與佛教有關,兩者在本質上畢竟難以水乳交融。
《大學衍義》與《大學衍義補》并不以哲學創發見長,但這兩部書最可見出理學“全體大用”之學的架構。由于體用論預設有體必有用,有用必有體,凡存在處,無一能脫離體用論的架構,所以理論上講,“全體大用”這一概念施用的范圍可以逸出《大學》所說。但如果我們采較寬的觀點,《大學》的內涵大到“天下”小到“心意”,無不包括,它的實質范圍和佛教的“法界”就很類似。《大學》被視為“全體大用之學”的代表之資格一旦建立,儒者長期以來一直想賦予倫理與文化價值一種宗教性的價值之焦慮,終于獲得解決。不但如此,宋元后的方外之士甚至也以理學家的眼光看待《大學》一書,不覺捍格。*如蕅益大師《四書蕅益解》即是。參見蕅益大師《靈峰宗論》卷6之1,北京:北京圖書館,2005年。《大學》能歷經八百年還有生命力,不能不嘆服“體用論”的思考方式之魔咒力量。
五 結論:不再是“大人之學”的《大學》
《大學》一書所以在理學傳統中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乃因宋代以后,它徹底地理學化了。這本理學化的經典被認為關懷理學成德之教的基本問題:它提出了成德的超越根據,凡是此書中的心靈語匯如心、意、知以及“明德”等詞匯,皆被當作超越的道德主體看待。此書也被認為提出了如何體現此主體的方法,凡書中心靈語匯上的動詞如“誠意”之“誠”、“致知”之“致”、“正心”之“正”或“明明德”之“明”,都被視為有工夫論的含義。最重要的工夫論語言當然是“格物致知”,這四個字的每個字被翻來覆去詮釋了不知多少遍,此中細節固不待論。《大學》的心性論與工夫論又被認為依循體用論的模式展開,由于《大學》的內涵包含極細微的深層意識層面以及極廣大的天下國家范圍,它遂構成了體用論演出的極佳舞臺。因此,從宋代開始,《大學》便被視為講究“全體大用”之學的典籍。
本文以“明德”、“格物”、“全體大用”三個重要術語為例,追溯理學家從心性論、工夫論及思考模式所詮釋的《大學》圖像,我們不能不遺憾地說:它們都不合《大學》的原意,“明德”原本出自太陽神話的余蔭,“格物”表達一種神秘人格的神秘感應力,至于“全體大用”說原來的圖像只是表達儒者的道德關懷無止境而已。然而,理學家將這三個層面的問題深化了,也一貫化了,從此,我們有了完整的體用論思考模式。
理學家的“誤讀”或過度詮釋事出有因,本體的追求是理學家精神活動極重要的動力,就像本體的焦慮是理學家一生常會面臨的關卡一樣。《大學》一書所以會從《禮記》中的一篇文章蔚然變為核心的圣經,而且只要理學存在的時日,它的作用也一直存在,這樣的現象不會是偶然的,筆者認為關鍵在于《大學》滿足了理學家追求本體的心理需要。身為儒門教義下的學者,理學家對倫理世界與文化世界的價值是不可能放棄的,但在新的思潮挑戰下,他們不可能不給倫理與文化的世界更深刻的基盤,體用論的思考就這樣誕生了。但體用論要在儒門內生根,不能沒有經典的依據。由于《大學》本身綱目清晰,而又隱含兼具內、外兩個面向的實踐領域,在此背景下,它很快成了體用論思維最好的載體,《大學》成了“全體大用”或“明體達用”之書,其地位甚至超過其他更富形上趣味的儒家經典,比如《易經》或《禮記》中的《仲尼閑居》《樂記》等等篇章。
體用論的思考是理學的核心要義,從朱子后,其作用更大,體用論的語言從心性論擴散到禮樂、政治、詩文各領域上去。可以說凡有事物存在處,即有體用論的思維。公元1160年(紹興庚辰年),時值壯年的朱子臥病山間,有親友到朝廷任官,召請朱子,朱子戲作兩首詩,以作回應。詩曰:“先生去上蕓香閣,閣老新峩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另一章云:“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云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么青。”這兩首詩傳到胡五峰手里,胡五峰頗為欣賞,但不免覺得“其言有體而無用”,所以他要作一首詩“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胡五峰詩云:“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云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15](第8冊,P.3988)就詩論詩,胡五峰與朱子的詩其實各有興味,各具勝場。朱子的詩表達出的一種機智的婉拒,就不是胡五峰的作品所能傳達的。但理學家強調生意,強調體用一如,所以一種能興發云雨的詩之境界就被視為有體有用,其評價就會較高。準此,我們對《大學》何以會從教科書性質般的典籍,一躍而為儒家傳統中四部最重要的圣經之一,即不會感到訝異。因為同樣的心、意、知、物、家、國、天下,不同的眼光觀之,也會呈現不同層次的意義。境隨心轉,世界的意義在世界的命題之外,理學家正是別具只眼的儒家學者,他們的體用論思維轉化了所有事物的本體論意義。
永恒的經典一旦落入人間,成為對己(for-itself)的存在,也會具有歷史性。《大學》這部曾強力引發代代儒者往全體大用的路途上邁進的經典,其影響力并不全然是由經書的本質所決定的,而是有著文化風土的滲透。簡單地說,《大學》的時代就是理學的時代,孕育理學的土壤也是孕育新的《大學》論述的土壤,理學—《大學》—全體大用之學可謂三位一體。脫離了理學與全體大用思想的加持,我們很難想象《大學》可以發揮多大的效用,或者會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當代正是體用論被送入加護病房、理學不再占有指導社會運行之地位的時代,《大學》這本曾是近世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典籍甚至在政治領域也已失去了指導作用。道德政治似乎已淪為教科書上的語匯,王道政治則成了語言博物館的藏品。20世紀初,孫中山曾高亢贊美此書的政治價值,仿若它是中國文化世界中最燦爛的一顆明星。*參見孫文《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如下一段話:“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中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么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但從后來中國政治局勢的演變看來,其贊美倒像是日落西天最絢麗的一道晚霞,撐不了多久,絢麗終究歸于平淡,甚至淡入黑暗之中。
時至今日,《大學》顯然不再被視為體現全體大用的“大人之學”,它走出了宋、明。但即使沒有理學論述的加持,筆者相信其書仍有其不可磨抹滅的價值。沒有形上學預設的《大學》主張一種道德的人生與道德的政治,這樣的堅持不管會受到多少的挑戰,也不管它是否無法正視政治的權力分配本質,但它顯示了儒家在現實權力運作中一種理念的設計,一種理想永遠超越于現實秩序、而且還要轉化現實秩序并體現于現實秩序的堅持,這樣的堅持與“道統優于政統”、“言必稱堯舜”等典型的儒家政治論述是一致的,同樣顯現“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偉大悲劇精神。作為帝王學的《大學》是不會再回來了,但作為一種儒家政治哲學的《大學》不見得會過時。而且如果我們認為現實的人間秩序不可能完美,它永遠需要轉化,那么,《大學》此書恐怕就沒有過不過時的問題。*晚近亞里士多德的德行倫理學以及晚期福柯的工夫論日漸受到重視,即可見出方向轉變之一斑。
“《大學》的現代價值”之問題還可從此書之體制考慮。當代通儒傾向于認定《大學》的論點沒有決定性,它呈現的毋寧是儒家的共法。但即使僅就儒家的共法而論,也有表現效果的問題,《大學》的體制在此點上正有其殊勝處。因為和其他儒家經典相比,《大學》綱舉目張,實行步驟特別清楚,這樣的體裁易于接引初機。我們知道“經”通常具備理論導引的大方向,個中的思想命題不暇細論,也不必細論。就一時一地而論,它受到后來者的重視,有時候比詮釋它的教派下學者之論著還不如。*智顗感慨佛弟子往往重論甚于重經,明清反理學的儒者指出當時的儒者往往重視先儒語錄甚于六經,皆可見出此種風氣。但就長遠而論,經終究是不刊之鴻教,是無法被取代的。《大學》在格式上倒比較像“經”的形式,而不像儒家的“傳”或佛教的“論”。*朱子將此書分成“經”、“傳”兩部分,經一章,傳十章,這是更細的分類。但即使依朱子的分類,“經”、“傳”既然合體,全書仍是經典化了。政治是儒家重視的領域,但論及儒家的政治思想,歷代的相關著作雖多,但至今為止,仍沒有一本書或一篇文章比《大學》更受到重視。個中原因固有多端,但應該與此書精簡扼要而又被視為“孔氏之遺書”有關。儒家的《大學》和佛教的《金剛經》在這點上有些類似,同樣是以“以簡駁繁”取勝。
《大學》被視為“孔氏之遺書”,并沒有足夠的傳世文獻佐證,但宋代后,質疑者并不多,它曾經歷過一段好日子。入民國后,疑古之風大盛,《大學》就和儒家的命運一樣,大體上日趨下坡,從年代、作者到理論價值,皆受質疑。然而,物極必反,晚近經典詮釋的方向已由疑古漸趨釋古。自從郭店與上博楚簡陸續公布后,釋古的走向更明顯,學者對《禮記》諸篇的年代與作者學派屬性的看法又擺蕩回去,日漸趨近理學家的觀點,這一趨勢很值得留意。歷史證據的部分不是本文的重點,但歷史證據往往會影響到經典的正當性之基礎,晚近的考古發現無疑使已大量流失的經典基礎又重新穩固下來。而只要《大學》被視為擁有“圣言量”的資格,它就不可能存有而不活動,經典有自己的生命方向。
[1]李颙.二曲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6.401.
[2]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M].臺北:學生書局,1986.302-304.
[3]伊藤東涯.古今學變·卷之上[G]//井上哲次郎,蟹江義丸.日本倫理匯編·古學派の部:冊上卷中.東京:育成會,1901.226.
[4]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M].東京:文求堂書店,1932.
[5]周法高.三代吉金文存補[M].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80.104.
[6]鄭玄,孔穎達.禮記正義[G].十三經注疏:卷60.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1.
[7]李翱.復性書·中[M]//李文公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9.
[8]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冊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9]趙順孫.大學纂疏[M]//四書纂疏.臺北:新興書局,1972.
[10]楊儒賓.格物與豁然開通——朱子《格物補傳》的詮釋問題[C]//鐘彩鈞.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219-246.
[11]真德秀.大學衍義[G]//四部叢刊廣編2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12]丘浚.大學衍義補[G]//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13]真德秀.鉛山縣修學記[M]//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2.
[14]黃宗羲,等.宋元學案[M].臺北:河洛圖書公司,1975.25.
[15]朱熹.朱子文集[M].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
TheGreatLearningandLearningof“Quantidayong”
YANG RU-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Hsinchu 30013, Taiwan)
TheGreatLearninghad come from a chapter in theClassicsofRites, and it was not so important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Its significance and position was increasingly promoted and became the core of Confucian classics when Neo-Confucianism rose. Then, what ideological resources did it provide? How did Neo-Confucianists renovat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sources to turn it into an important Confucian classic? The key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saw it as a “book of nature and fate”. For this purpose, they did a systematic transfer of the important concepts in the work, mainly upgrading universal virtues to an ontological level. Such a renovation was a big project which also needed careful work. Through Neo-Confucianists’ efforts, theGreatLearninghad a complete change, from a common learning guide to a book of nature and fate.
GreatLearning; manifesting virtue; Extension of knowledge li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Quantidayong; book of nature and fate
2012-05-18
楊儒賓(1956-),男,臺灣臺中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B244
A
1674-2338(2012)05-0015-015
(責任編輯:沈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