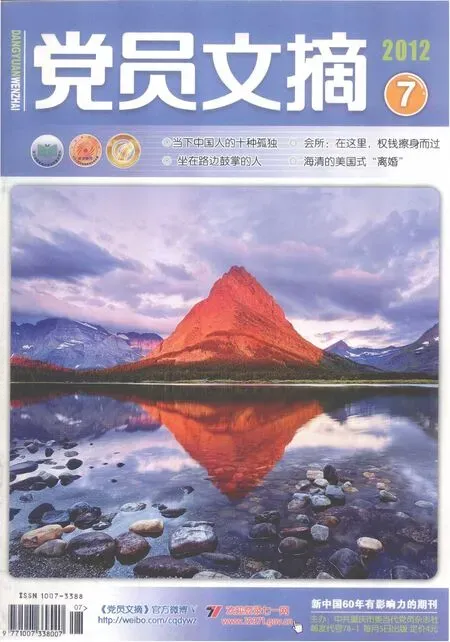巴西緩解貧富懸殊之路
周志偉
盡管巴西貧富差距依然比中國大,但在破解收入分配不公現象方面,巴西人的政治智慧、治國理念和社會政策值得同為“金磚之國”的中國借鑒
巴西的基尼系數曾經高達0.6,幾乎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處于社會分裂與動蕩的懸崖邊。
在工業化的驅動下,巴西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進入了GDP年均增速超過10%的“經濟奇跡”周期。與此同時,巴西也進入了一個兩極分化迅速擴大的階段。到1990年,20%最富有者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為64%,最窮者占有的比例僅為12%。
片面追求經濟增速而忽視社會分配的經濟模式到20世紀80年代讓巴西難以為繼,并且還須為此前的負債發展模式埋單。從80年代末開始,巴西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開始集中爆發。此刻,巴西人懸崖勒馬,從90年代中期起,以“公平社會”政策作為優先治國戰略,通過三位總統卡多佐、盧拉、羅塞夫十多年的連貫施政,大大降低了基尼系數的峰值,并逐步走向一個中產階層占社會一半以上的橄欖形社會。
三位總統接力跑
盧拉的前任卡多佐總統面臨的問題是,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和外債水平都特別高。
1993年底任聯邦財政部長的卡多佐成功實施“雷亞爾計劃”(雷亞爾為巴西新貨幣的名稱),久治不愈的高通貨膨脹率在90年代中期回歸正常水平,1993年,巴西通貨膨脹率達到2489%的峰值,到1995年驟減至22%,1996年降至一位數。高通貨膨脹的降低直接減少了中下層民眾的生活成本,與此同時,也壓縮了富人階層投機經營的空間,而通過加征稅收(遺產稅、金融交易稅)等辦法使得富人階層的財富面臨縮水。憑借“雷亞爾計劃”的成功,卡多佐在1994年底的大選中當選為巴西總統。
盡管卡多佐實現了當時巴西宏觀經濟的相對穩定,但巴西在20世紀90年代末一直徘徊在市場動蕩的邊緣。經濟乏力成為卡多佐在任八年的首要挑戰,兩極分化依然延續著“擴大”的慣性,基尼系數在1996年達到了0.599的歷史峰值,在其卸任總統的2002年,依然高達0.586,屬“世界最不公平”的國家行列。
在貧民人口超過總人口數一半的巴西,盧拉提出的“確保每個巴西人一日三餐”的競選口號迎合了中下階層的集體訴求。在盧拉執政的八年間(2003~2010年),聯邦政府推出的社會政策多達30多項,一般將它們統稱為“零饑餓計劃”,其中的資助貧困兒童入學的“家庭救助金計劃”、提高貧困學生大學入學率的“全民大學計劃”、實現貧困地區通電的“全民電燈計劃”、改善中低收入階層住房條件的“‘我的房子、我的生活計劃”等,是盧拉政府社會政策的主干。
在盧拉總統卸任前,巴西的社會不公問題得到明顯好轉,社會政策惠及家庭達1100萬戶,受惠民眾達2900萬,中產階層的比例從2004年的42%升至52%,赤貧人口的比重從28%降至15.5%;基尼系數從2002年的0.586降至2009年的0.538。
盧拉政府一攬子社會政策不僅實現了社會分配問題的改善,另一大效果是橄欖型社會已經在巴西形成。隨著中產階層的壯大,巴西國內的消費市場逐漸成熟,國內消費成為帶動經濟的重要“引擎”。
當前的巴西羅塞夫政府在延續盧拉的政策理念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一種協調的發展,強調讓所有人享受經濟增長的好處。
用教育治療不公
巴西在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諸多新政中,教育一環至關重要,也是治本之策。
巴西的基礎教育、公共教育差,私立教育好,富人和窮人的教育起點并不公平。盧拉執政以來,包括現任總統羅塞夫,政府實行收入直接轉移政策,貧困家庭可以領到政府的補貼,但是有條件,受助家庭必須把孩子送到學校去讀書。以前巴西基礎教育輟學率比較高,現在已有明顯降低。高等教育則推行“全民大學計劃”,在公立高等教育學校設一定比例給窮人的孩子。
最近,羅塞夫總統又推行了一個級別更高的“科學無國界”計劃,通過公私合作的方式,設立獎學金,把巴西學生送到國外接受教育。此外,羅塞夫還把盧拉的“家庭救助計劃”升級,推出“無赤貧的巴西”計劃,用占GDP的1%的投入,把受惠的家庭范圍擴大,補貼數額提高。
其實,從卡多佐時代開始,巴西就把教育當作扶貧利劍,1996年巴西國會通過法律,規定州教育預算中的15%必須用于基礎教育。經濟學家舒爾茲認為,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差別,直接的原因是他們的要素稟賦不同,導致的收入不同。享受良好教育,變人口資源為人力資源,這是窮人提升要素稟賦的必由之路。
社會自治
在醫治社會“不公先生”時,巴西民間社會配合政府,形成合力,官民良性互動。巴西的非政府組織非常多,它們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大多是貧困和教育問題。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行動非常歡迎,推出了一系列有非政府組織參與的社會計劃,并將政府在社會領域的部分職能委托給非政府組織執行。
在教會和非政府組織與眾多民眾的積極參與下,巴西形成了一支“反對貧困,爭取生存”的反貧困隊伍。在各城市建立了近4000個自愿的市民委員會,各社區、公司、教堂、非政府組織、工會、鄰里委員會和學校均自發和獨立地成立了委員會,向約1000萬人免費發放基本食品。20世紀90年代中期,“爭取道德運動”和其他非政府組織還致力于解決就業和臨時安置無地農民等社會問題。
工會領袖出身的盧拉總統上臺后,為創造與非政府組織之間對話的新渠道,并創建公民參與新機制,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反貧困、反饑餓、反社會排斥的政策措施,直接推動了政府部門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
巴西非政府組織的社會角色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它不僅是推動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力量,而且也扮演著政府部門的“合作者”、“監督者”和“督促者”的角色。
(摘自《南風窗》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