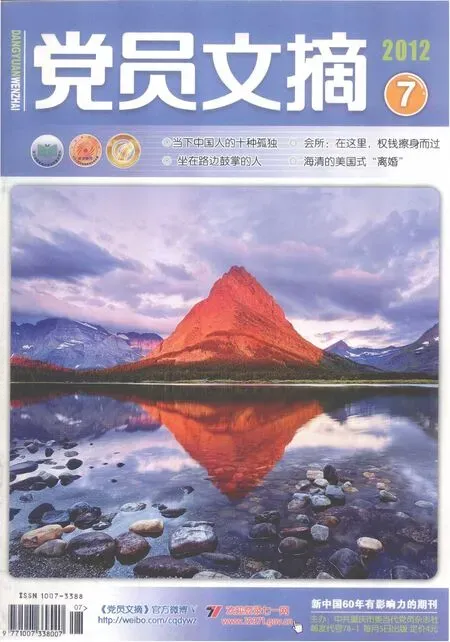知識分子和干部后代更易從政?
鞠靖 王成
“龍生龍,鳳生鳳”。知識分子和官員的后代更易從政?誰都沒有想到,這樣一個存在于人們想象中的問題,真的成了學者們的研究對象。
同濟大學社會學系青年教師孫明在2011年第5期《社會》上發表《家庭背景與干部地位獲得(1950-2003)》一文,得出了這樣的研究結論:知識分子、干部的后代在干部選拔中占據了優勢。這一研究實際上使全社會普遍關注的“官二代”問題,以學術研究的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
數據分析揭示“從政”之道
孫明所研究的是1950年至2003年間,家庭背景與干部地位獲得之間的關系和影響機制。研究顯示,家庭背景始終對子代的干部地位獲得產生影響。1978年以前,良好的家庭出身和黨員身份是獲得干部地位所必需的政治資本,軍人子弟憑借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入黨中的優勢,最有可能成為干部。而作為新政權核心的領導干部沒有實現地位的再生產,他們在政治運動中也可能成為打擊對象,其子女因受到牽連,并沒有在干部選拔中占優勢。
1978年以后,知識分子和干部的后代通過入黨和教育獲得兩個中間機制,在干部選拔中具有優勢。
孫明的論文,從廣度和時間兩個維度描述了家庭背景與“當官”之間的關系。在廢除了科舉制度之后,中國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一直是中外學者熱衷的話題。
孫明概念中的干部是指“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中代理國家權力的管理者和領導者”,并將“國家行政級別”作為衡量干部身份的依據。
孫明的數據來自2003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該調查被學界認為是當時較為權威的社會調查。在那次社會調查中,記錄了受訪者的工作變動起止時間、行政級別變動、18歲時父母職業信息。孫明根據調查數據,用回歸分析方法考察家庭背景與成為干部之間的關系。
學術之外的現實
在社會學者眼中,社會流動、社會階層的固化是一個永恒的話題。
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仇立平認為:“在社會流動中家庭背景是一個重要因素,也是一個社會事實。”在更宏觀的層面,孫明的研究結論具有現實合理性,社會階層的固化是穩定社會的必然現象。“社會階層的急劇流動,往往發生在整個社會出現制度性變革的特定歷史階段,比如在1949年前后和1978年前后,特定階段之外,社會階層流動都趨于穩定”。
仇立平說,現階段所謂的社會階層固化,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出現,這是經歷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會變革之后的必然現象。90年代以后,只有小部分人能夠向上流動,而大部分人會維持在原來的社會階層位置。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友華也表示:“恢復高考的最初十年,很多底層人士可以通過自我奮斗,實現向上流動。但是90年代以后,政治、經濟資本更多地參與了資源配置,使中國出現階層復制,階層再生產的表現明顯。”
包括陳友華在內,很多學者表示,今天,一個普通百姓依靠自己努力,不容易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會面臨“天花板效應”。“出身于普通家庭,在縣里可以做到股長,在市里可以做到科長,在省里可以做到處長,但是如果要再向上,就非常困難。”陳友華說。
在陳友華看來,這種情況的出現有其必然性:“第一,社會上層家庭,能夠為子代創造更好的生長環境。第二,父母成功本身也會給孩子某種意義上的壓力,使得孩子在年輕時可能就追求這種成就感。第三,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父母可以給他們創造很多機會,這可能是其他家庭一輩子都不會有的。第四,普通百姓家的孩子接觸的都是百姓,而總統家里的孩子,接觸的多是社會精英,容易形成豐厚的社會資本,對成長有很大幫助。”
毫無疑問,更好的教育、更多的交往機會、更高的展示平臺是每一個人得以成功的重要條件。“如果不是以受教育程度、已經展示的能力來衡量一個人的潛質,那反倒是不正常的。”一位社會學者說。孫明認為,在西方,家庭背景同樣對子女發展有影響。
但問題是,無論你是怎樣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當人們競爭的目標是“做官”的時候,就必須有一套維系公平的程序。對家庭背景與“做官”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其意義在于揭示其中的規律和機制,為完善干部選拔任用機制提供借鑒,這是很多中外學者關注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
陳友華說:“來自中上社會階層家庭的孩子們更容易成才,但是這樣的人在社會中是少數。普通家庭基數比較大,雖然成才率比較低,但是絕對數也不少。在發達國家官員中,也是出身于上層社會階層的人較多,但在中國顯得更多一些。”
(龔寶良薦自2012年5月10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