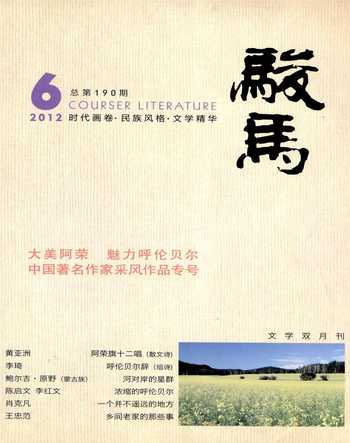漂流的記憶
紅孩
人生就像一次漂流。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最終你都要被推進生活的漩渦。或許你順流而下,一路歡歌;或許你屢遇險灘,險象環生,甚至是中途付出生命的代價。直到你抵達生命的彼岸,你才能上岸,你才能對整個里程做出終審般的裁定。
所以發出這樣的感慨,是我在呼倫貝爾草原阿榮旗查巴奇鄉阿倫河參加漂流后的一次思考。在旅游區漂流,我已經不是第一次,以前在京郊密云、承德的塞罕壩、銀川的黃河灘都曾經進行過。至于小時候在鄉間的河流里漂流的次數和花樣就更多。但只有這一次,我似乎真正地悟到了什么。是因為我已經人到中年對生活的經歷豐富了,還是我更善于思考了?
阿榮旗位于內蒙古東部,背倚大興安嶺,與黑龍江交界。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抗日戰爭時期,東北抗日聯軍曾三進呼倫貝爾,其主要戰場就在阿榮旗。1965年7月14日,一個響徹華夏大地的名字——王杰,就是阿榮旗人民驕傲的兒子。2012年6月21日上午9時,當陽光灑滿阿榮旗的大街小巷,我來到位于旗政府對面的王杰廣場,肅立在高大的英雄雕像前,去憑吊這位我不曾見過的兄長。看著雕像背面的碑文,我的心里不由輕輕地叫他一聲大哥。自從我的胞兄19年前去世后,我已經多年沒有叫大哥的習慣了。王杰犧牲的那一年,我的胞兄剛剛出生。我的胞兄不是英雄,王杰是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他們都將記憶在我的生命里。大哥你好嗎?這樣的問候,我想絕不屬于我一個人。
阿榮旗不是呼倫貝爾最大的旗(縣),人口只有32萬。但這里卻聚集著20多個少數民族,滿、蒙、鄂溫克、朝鮮、達斡爾、鄂倫春等,他們宛如一家人,在這片富饒的土地上長期友好和睦地生活著。在查巴奇鄂溫克民族鄉,我們來到一個獵戶家里。獵戶姓杜,全稱應該是杜拉爾。我記得有個女作家的名字就叫杜拉爾·梅,不知道她與這個獵戶家有沒有關系。鄂溫克族人過去以狩獵為生,現在提倡生態保護,他們便把獵槍交給了公家。他們的生活主要是種地,種上百畝的地,地里有小麥、大豆和玉米。他們的房子雖然是平房,但功能很全,窗臺上堆放著主人昔日曾經用過的獵槍手套,扣扳機的地方明顯露著一個大窟窿,邊緣早磨得沒了棱角毛茬,想必主人過去是個不錯的獵手。屋外的窗臺下有一大一小兩個瓦缸,上面罩著塑料布,當地朋友讓我猜是什么。我說是酸菜,東北這個地方盛產酸菜。朋友笑了,說都快七月了,哪里還有那么多的酸菜,即便有也會漚壞的。那里邊裝的是家制的大醬,也就是黃豆醬。東北人大都是山東移民,有愛吃大蔥蘸大醬的習慣。電視里經常看到東北一家人坐在炕桌上,吧嗒一口小酒,撕拉一把大蔥蘸醬的生動畫面。那感覺真是誘惑人啊!
獵戶家的孫女叫杜娜,奶奶78歲,一張圓臉紅通通的,講起話來很穩重,像經過大事的人,也很慈祥。杜娜房間的寫字臺上有一副麻將牌和一臺電腦,這一古老和現代的東西放在一起很讓人聯想。杜娜告訴我,麻將是供奶奶玩的,電腦不能上網,只能打打文字、玩玩游戲。我說別急,上網很快就會解決的。我又問,村里的年輕人還多嗎?她說,很少,大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杜娜家的大門口有一大垛柈子,用于燒火取暖。柈子的材料主要是白樺樹和柞木。由于從小對白樺樹產生很多浪漫的想法,也聽兵團戰士說他們當年的愛情就是通過白樺樹皮傳遞的。所以,見到用這么多的白樺樹燒火,看著真是令人心疼。當地的朋友說,出于生態保護,漢族人已經不讓隨便上山砍柴了。而對于鄂溫克人則網開一面,可以適當采伐一些,大概是為延續他們狩獵民族的習慣。
杜娜家房子的西側,是一棟破舊的茅草房,里邊黑洞洞的。當地的鄉長說,這房子是鄂溫克人最早居住的,現在這樣的房子已經不是很多了。十幾年前杜娜家蓋房子時,曾一度要把舊房子拆了,鄉長聽說后給制止了。他說,還是給后人留點念想吧。
是的,留點念想給后人。不知怎地,我還是希望在杜娜家的墻上能掛上一桿獵槍,旁邊再掛上幾張狍子、野兔甚至是狼的皮毛。
夜晚,在一處偌大的場院上,鄂溫克族鄉親們為我們準備了“瑟賓節”表演。本來這個瑟賓節是在前一天舉行的,為了迎接我們采風團的到來,他們特意推遲了一天。瑟賓節是為了祈福、慶祝豐收的意思。這一天晚上,周圍一二十公里的鄂溫克族鄉親們老早就從四處趕過來,他們穿著節日盛裝,載歌載舞,特別是圍著篝火群舞的樣子,使任何圍觀的人都會被感染,都會情不自禁地起身離座置身于這歡騰的人群里。
說實話,這一次我沒有真實地漂流,也不曾在瑟賓節上舞蹈歌唱,我只是在稍遠的一隅,靜靜地看著想著。我知道,此刻我的心一直在隨著這高山、河流、草原以及鄂溫克人家一起漂流著。漂流著的,一定是充滿活力而有生命的。我喜歡這種漂流的感覺。
克爾倫河畔的情思
夜幕降臨,克爾倫河畔的思歌騰博物館門前的知青廣場上響起了歡快的舞曲,奔波勞碌了一天的人們三三兩兩地來到這里漫步、舞蹈。我所居住的賓館就在知青廣場的斜對面,走著也就五六分鐘的樣子。下午五時許,從牙克石市一路觀光過來的我們赴呼倫貝爾作家采風團一行三十余人,剛到達新巴爾虎右旗城區,接待辦的同志就招呼我們稍事休息后立即到思歌騰博物館參觀。
思歌騰是蒙語,意為知識青年。就是說,思歌騰博物館該是知青博物館。知青這個詞,在我們國家有特殊意義。對于三十歲以下的人,知青的含義他們或許還真的無法弄清,有的連聽說過都不一定。1971年,我家所在的京郊農場,就曾接收過大批的知青插場插隊。我清楚地記得,在這一年的秋天,我們家突然搬進來三個漂亮的女知青,從此我們家與知青便有了四十余年的不解之緣。
我不知道在全國其他城市是否還有知青博物館和知青廣場,反正在呼倫貝爾的新巴爾虎右旗,我是被這個知青博物館和知青廣場震撼了。據文字記載,從1968年到1978年,全國共有1780萬人響應國家號召成為在廣闊天地里大有作為的知識青年,而在新巴爾虎右旗就有1020名天津知青來到這里。在這千余名海河兒女中,女知青張勇因搶救落水羊只而犧牲,一時成為全國知識青年中的先進典型。
張勇1969年從天津42中畢業來到新巴爾虎右旗額爾敦烏拉公社白音寶力格生產隊,她因為無限忠于毛澤東思想,曾起了一個蒙古族名字——烏思琪(忠誠的意思)。在思歌騰博物館,我看到了從《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到《天津日報》等幾十家報紙對張勇先進事跡的報道,隨著時間的流逝,那些報紙已經變得發黃,唯一不變的是張勇那張英俊的臉龐。位于知青廣場與知青博物館之間的張勇雕像從哪個角度看,她都十分的完美,特別是她的眼睛是那樣的晶瑩透亮,充滿著那一代年輕人才具有的理想。
在思歌騰博物館參觀后很多人都匆匆而去,見我一臉的凝重,工作人員打開留言簿對我說,您給留個言吧。我拿起筆想了想,寫下:難忘的知青歲月,無盡的文學之源。陪同參觀的女導游見我寫下這樣的文字,說:“您對知青真有感情啊!”我說:“是的,過去的許多事我們怎么能忘記呢?這不僅由于有的人獻出了寶貴的青春和生命,這其中還有著一代人無法忘記的青春記憶。”
我想到2010年的8月,我曾到過北大荒燕窩島知青烈士陵園。那一天,燕窩島晴空萬里,夕陽映照在碧綠的湖面上,片片的睡蓮黃燦燦地煥發著青春的氣息。而在此不遠的烈士陵園里,卻是靜悄悄的,像死亡一樣的安靜。我和東北作家阿成、趙國春、于德北、袁炳發等人默默地為羅海榮、張德信、陳越玖三名烈士敬獻上了花籃,他們的年齡分別為26、32、24歲。這顯然不是按順序排列的,其中的一名知青于1975年患上了癌癥后仍然堅持工作,他在臨終前寫下遺言:我是北大荒人,死后請把我的骨灰埋在北大荒。
我是北大荒人,我是北京知青,我是天津知青,我是上海知青,我是杭州知青——我是中國知青!這樣的聲音不是我喊出來的,它就鐫刻在中國地圖的知青分布圖上。你懂得什么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嗎?你若看到中國地圖上的知青分布圖,你就會明白,你就會發人深省地明白。
夜深人靜,我躺在舒適的賓館客房里怎么也睡不著。遠處克爾倫河的流水肯定依然在歡唱著奔涌,它能知道今天有個從北京來的年輕人在這里沉思冥想嗎?我想它會的,我相信克爾倫河是一條有情有義的河。(責任編輯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