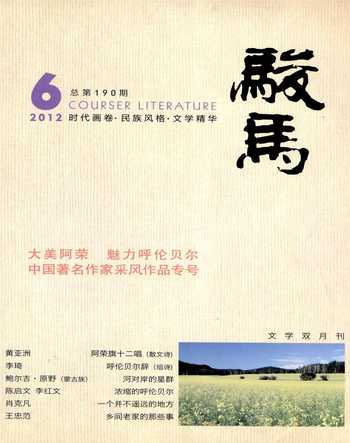鄉間老家的那些事
王忠范
中國作協會員、中國詩歌學會理事、內蒙古兒童文學創委會副主任。先后出版長篇小說、詩集和散文隨筆集共32本書,獲各種文學獎60多項。
土 豆
我的農村老家是中國有名的土豆之鄉。土豆的學名是馬鈴薯,但家鄉人還是叫它土豆,古時就這樣叫,一輩輩傳下來叫慣了。家家戶戶都種土豆,一年四季的飯桌上誰家都離不開土豆。
家鄉的農田大多都在坡崗上,地薄、土松、耐澇,非常適合土豆的生長。有這樣一句順口溜:“坡崗陡,種土豆,到秋都是好年頭。”土豆產量高,怎么做都好吃,跟魚、肉和各種蔬菜混做都行,綿軟、淳厚、實在,確是好東西。以前,有些孩子的乳名叫黑蛋子、白胖子、圓敦子,甚至直接叫土豆子,這都表明人們對土豆的偏愛。
糧食緊缺時,土豆可以當飯吃,連吃幾頓都不會反胃的。更重要的是家鄉的土豆質量好,好賣,還能賣個好價錢。如果土豆經過深加工,制造出粉面、粉條、粉絲,那便是市場上的香餑餑,更值錢了。我的祖父曾跟我說過:“土豆胖又圓,個個都是錢。”
然而,土豆的種植和田間管理,可是一項精細而累人的農活。頭一年就要選好土豆種子,貯藏在深深的地窖里,不能熱了更不能凍了。我家的土豆窖由祖父一人掌管,定期查看,通風、培土、測溫度,像侍弄孩子那樣精心。轉過年的春四月,土豆種子見芽時,祖母和母親就用鐮刀或者剪刀不緊不慢地把土豆種子切割成一個個小塊,這小塊叫栽子,每個栽子至少有一顆芽,這芽要留在栽子的正中間。母親說,這活有技術含量,要仔細,老爺們干不了。一堆堆栽子切好后,祖父便均勻地拌上草木灰,我知道這是從根上防止病蟲害。開犁了,豁開地壟時,父親撒下一筐又一筐的農家肥。他氣喘吁吁地說,種土豆不能上化肥,化肥板結土地,土豆最怕泥土板結。祖父帶領我們一家人種土豆,把土豆栽子芽朝上地擺進土里,栽子與栽子之間的距離是六寸,密了不行,稀了也不行。這活實在累人,整天哈腰,挎著栽子筐挪步,弄得我直喊腰疼。祖父眼睛一斜楞:“誰也不能偷懶,人糊弄土地一時,土地就糊弄人一年。”
幾場透雨,大約二十來天,土豆的秧苗就拱土了。滿壟鋪綠,綠得新鮮,綠出了靈氣,叫人稀罕得直咂嘴。再過一個月的光景,土豆花滿壟盛開,或紫或藍或白,鮮艷而又好看。土豆花一謝,祖父和父親就打尖掐葉,防止光長秧子不長果實。他們天天踏露田間,濕透的褲角緊貼腿肚子,腳丫子沾滿泥濘,臉上大汗淋漓。立秋前后,土豆成熟了,又大又圓,有的把地壟都給拱裂了。父親帶我去護田,就從地壟的裂縫處伸進手,摳出幾個大土豆來。坡頭上,挖個小坑,把土豆放進去,上面點燃一捆干柴燒土豆。也就是幾袋煙的工夫,土豆就熟了,而土豆挨地的那面有點生,父親一邊用手捏一邊說:“土豆沒有爹,架不住三捏。”剝去土豆皮,土豆瓤黃焦焦的、肉嘟嘟的、面乎乎的,咬一口滿嘴香。
土豆收回來后,堆成小山似的大堆,放在外面晾曬,去去濕氣。“土豆滿場,女兒看娘。”盡管只有五六天的休閑時間,年輕的媳婦也要回娘家看看,帶上二斤鮮肉或者咸肉。這地方姑娘出嫁那天,媽媽把一塊鮮肉纏上紅線送給女兒,這肉叫離娘肉。而收回土豆女兒回娘家時,也要帶塊肉,表明一直沒忘女兒是娘身上掉下來的心頭肉。小時候,我常常穿上新衣服,跟母親坐小馬車或者騎自行車到姥姥家,像過年一樣歡快。其實在姥姥家只住兩三夜就趕緊回來,因為這時村里總要請來戲班子唱臺戲,慶賀土豆豐收。唱完大戲,各家都是土豆上磨,開始把土豆磨成淀粉,接著插伙輪流漏粉。漏粉這天一早,都要燃放一掛鞭炮,圖個高興和吉利。只聽大粉匠一聲:“漏粉嘍!”所有的人便各就各位一起忙活起來。四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和粉面子,一個專門燒火的人負責把大鍋里的水燒得開開的,兩個人手握細棒撥粉,粉匠則抓住懸掛的漏瓢一掌又一掌地往下拍和好的粉面子,啪啪呱呱,很響亮。時有大塊的粉面子掉進鍋里,撈上來叫粉耗子,既滑溜又筋道,好吃好玩,孩子們圍在這里,就等這一口。那漏瓢就像噴頭,垂落下根根飄悠的粉絲,經過開水一浸,撥粉人就麻利地把粉絲挑在粉桿上,然后掛在外面的粉架上晾曬。此刻,桿桿粉絲就如同白色瀑布,在微風里飄飄閃閃,好看極了。如今,這樣的漏粉少見了,大多都是機械制粉,開水沸騰,機械聲一片。人們只需跟著機器走,成粉,烘干,包裝,一袋袋放進倉房就是了。
這幾年,家鄉的土豆淀粉、粉條和粉絲送進了大城市,換回來大把大把的錢,農民的腰包鼓了。鄉親們說,土豆變成金蛋了。所以漏完粉以后,趁天還沒煞冷,家家戶戶就開始整地、上底肥、打秋壟,開始為第二年的土豆種植做準備了。這時候是在豐收的喜悅中忙碌,大家就不覺疲累,好像越干越有奔頭。你聽,坡野上山地里的歌聲、喊號聲總是此起彼伏。晚上誰都要喝幾杯,細品著農家殷實的日子,那樣自在、幸福。我一直以為家鄉人的性格像土豆:純樸、實在、厚道,和諧共生。
那年頭的雪
我調到嫩江以北那吉縣城工作的那個冬天,被派到長安鄉當蹲點干部,這是三十幾年前的事情。我年輕,又不懂農村工作,便啥都不管,挺輕閑的。我住在鄉政府,跟組織委員、團委書記和民政助理同一間辦公室,每天掃地、擦桌子、打水這些保潔的活就由我包下了。最忙活最累的是掃雪。那年頭雪多雪大,每隔十天半個月就要下一場。一旦夜里下雪,第二天一早起來,我就戴上皮帽子和手套跟燒火爐子的工友一起掃雪。在上班之前,用板鍬和掃帚清理出通往大院外和通向廁所的兩條長長的道,常常累得腦門子和脖子上都是汗。
有一天掃雪以后,坐在辦公室閑聊,突然發現鄉政府大院前的田野里有一只雪天下山打食的狍子,它站在那里東張西望。我們幾個人急火火跑出大門,去追狍子,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也沒攆上,都很惋惜。組織委員抱著膀說:“狍子肉包餃子吃那才香呢。”他的話讓我饞得直咽口水。回到辦公室,見我的初中同學、珍珠村學校老師劉遠亮正坐在那里等我。前些日子,我幫他辦了個“紅本糧”指標,不知道這回又有啥事。他搓搓手跟我說:“星期天我家殺年豬,請你去吃年豬肉。”接著又加上農村的一句老話:“幫了忙,吃點熱血腸。”我說那好哇,正想解解饞呢。
星期天后半晌天陰了,我借一輛自行車騎著緊蹬快趕直奔相距十二里地的劉遠亮家。半路上飄起了雪花,頃刻紛紛揚揚,直糊眼睛,我只能推著車子走。進了劉遠亮的家門,見炕上地下都是人,歡聲笑語裝滿了屋子。東北農村有個老習俗:不管誰家殺年豬,都請鄉里鄉親吃一頓,是體現團結和諧,也是營造年的氣息。鄉下人喝酒實在,我也沒客氣,所以吃喝得痛快淋漓。遠亮知道我喜歡紅辣椒,說倉房里有,我便自己出門去取。趿拉著鞋,就覺雪淹鞋底,涼瓦瓦的;我第二次出去是上廁所,那雪已埋鞋幫,灌進鞋窠,濕了腳脖子;吃完飯,把空酒瓶從窗子扔出去,竟毫無聲息。如此大雪,我沒法回鄉政府了,只好住在遠亮的家里。遠亮逗趣:“這叫人不留天留。”這雪悶著頭足足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真是雪封房門了。推不開門,遠亮從窗子跳出去,把門前厚厚的雪清理到一旁。門開了,大人小孩一起出來,先是掃出一條道,然后一片片掃雪,撮成堆,再裝進筐里抬到院外去。
掃完雪,孩子們就跑到院子外掃出一塊露土的空地,撒兩把谷粒、豆粒,用系著長繩的木棍把帶孔眼的篩筐支在金黃的糧食上面,然后手抓長繩躲在柴垛后面觀察。雪天小鳥找不到吃的,一旦發現谷粒、豆粒,就會一只又一只地鉆進去叨食。孩子們看進去的小鳥多了,就猛地拽繩,棍倒筐落,鳥們就被活捉了。這時孩子們擊掌喊號,樂得直蹦高。劉遠亮去挑水時,看見幾只野雞正往谷草垛里鉆,他掄起水扁擔抽過去,又來個猛撲,一下子捉到兩只。他笑瞇瞇地跟我說:“別走了,中午吃野雞燉蘑菇。”
吃過午飯,我才上路返回鄉政府。鄉路上的風口處,雪飛路凈,可以騎著車走;更多的是彎彎拐拐的地方,遍布雪包雪坑,很滑,就得推著車走;而窩風的路段積雪過膝深,只好扛著車子走。僅僅十二里的鄉路,我走了小半天,渾身都是汗。晚上坐在床沿上燙腳聽著有線廣播,跟著小喇叭里的歌唱家呂文科唱《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搖頭晃腦,悠悠然。
現在說起雪來,人們頓生些許感懷,都懷念那年頭的雪。
豆 收
快到“白露”的時候,我的老家嫩江北岸黑土地上的大豆田變得黑綠黑綠的,長長的豆莢一天比一天鼓,里面的豆粒越來越圓,即將成熟了。這季節最怕早霜,所以家家戶戶都在田頭地邊點燃一堆堆事先準備好的蒿子,火苗閃閃,煙霧騰騰,制造一種小氣候環境。有的人家用三楞草扎成小小的掃帚掛在房檐下,像裝飾品,蕩蕩悠悠,說是正在掃霜呢。母親不信這些,說盡是迷信,沒有用。她認命,是順其自然的人。
父親天天帶我去大豆田逛游,他像端詳我那樣看著每一顆大豆,看著看著就咧嘴樂了,臉上盡是笑容。父親拔起幾把豆棵子,撿來干柴,點燃燒毛豆吃。這豆粒圓圓胖胖,鮮鮮嫩嫩,吃了這粒想那粒,不一會兒肚子就鼓了。我的手和嘴巴總是弄得黑糊糊的,父親說我像山里的小黑熊。
仿佛只是眼睛一閉一睜的工夫,就是“秋分”了。滿地的大豆悄無聲息地落葉,豆秸和豆莢忽地變黃、變黑,開始嘩嘩啦啦地搖鈴了。那些從山里飛來的尖嘴鳥在空中盤旋,“咯咯嘎嘎”地歡唱,似乎在說:割啦、割啦……
豆收的日子到了。
這時候祖父就要跑一趟鎮里的市場,買幾把新鐮刀、小磨石和露著手指頭的特制皮手套。還扎進小酒館跟熟悉的老哥們喝幾盅,嘮嘮收成,泡在豐收的喜悅之中。回來他在月光下給鐮刀開刃、細磨,嘩哧嘩哧,磨得鋒快鋒快,搭上一片草葉立刻斷成兩截。
開鐮這天,全家人頂著晨星下地,一人抱三條壟,中間壟開趟子,再來回割另外兩條壟放鋪子,沿著長壟一截一截地往前推進。這時太陽還沒出來,露水大,大豆不能炸角,要快割多割。太陽像個火球時,就回家休息,等日頭卡山再下田來割,就是避免大豆炸角。祖父常說,豆收時若是讓大豆炸了角,滿地豆粒,不但損失大,還要被人家笑話,說你算什么農民。其實豆收是最苦最累的,大哈腰,使足勁拉拽鐮刀,不一會兒就汗珠子滿臉了。而攏豆棵的那只手的指尖,被豆角尖扎得血糊糊的,疼得人直筋鼻子。往往一條壟沒到頭,鐮刀就鈍了,祖父便摘下掛在褲腰帶上的小磨石給大家磨磨刀,只有這工夫才能直直腰。接著又割,刀快聲響,心頭滋生幾分豐收的喜悅。豆收這幾天活累,各家的飯菜多種多樣,盡是好吃的東西。我家祖母在家做飯,她烙牛舌頭餅、燜帶豆的黃米飯、做小雞燉粉條、炒青菜、煎河魚、煮咸鴨蛋、熬酸辣湯……一頓一個樣,看著饞,卻吃不了多少,是累的。不過祖父天天晚上還要喝幾盅,他說喝了酒能睡一夜好覺,那就緩過乏了。
只是幾天時間,地里的大豆全放倒了,一個個豆鋪子成行連串,像幅大自然的版畫那樣好看。接著開始拉地,就是把豆鋪子一車又一車地拉回家去,在場院里堆起小山般的豆秸垛。等“寒露”一到,就打場。這期間,那些唱大鼓的、說書的、演獨角戲的、變戲法的鄉間藝人,常常來村里祝賀豐收掙賞錢,幾乎天天都有節目。不管怎么熱鬧,家家都留人看護豆秸垛,因為一旦失火,一年的血汗就泡湯了。
現如今豆收也用上了機械,人們只需跟著收割機往前走,把豆子灌進袋子就行了,沒啥累活。然而,我老家那地方好多人家不雇用收割機,不差錢,就因收割機不能把倒伏的豆棵子收起來,更怕糟踐了豆秸和豆皮子,豆秸和豆皮子可是牛羊最好的飼料。父親說,生長在田地里的一切都是汗水泡出來的,浪費啥俺都怪心疼的。
打完場,大豆入倉了,農家滿院都是大豆的芳香。父親抓一把大豆瞧了又瞧,拿一粒用牙一嗑,“嘎嘣”一聲,他就憋不住笑了。這么好的成色,農人怎能不高興呢。母親樂顛顛地走過來,掐一把父親:“今年會親家,咱們要殺一口豬。”“金豆金豆,親家碰頭。”農家一年四季都忙,就是兒女親家也很少見面。現在豆收過了,有點空閑時間,總要會會親家,走往走往。會親家時,除了吃喝玩樂以外,還要踏田,規劃明年,每一雙眼睛里都充滿了希望。
瓜窩棚
瓜窩棚在鄉間老家紅旗社名叫偏臉子的坡地上,是老瓜頭的住處。人字形的馬架子兩側用草苫蓋,后頭留個通風的窗口,前面是柳條編織的門。瓜窩棚里上窄下寬,一鋪小炕、一個鍋灶、一盞馬燈,特別簡單。瓜窩棚背靠一片楊樹林,前面是瓜田,瓜田旁山花爭艷,野草噴香,真是“風景這邊獨好”。
老瓜頭有名有姓,叫楊貴昌,還不到五十歲。但他年年種瓜賣瓜,村子里的大人小孩便稱他老瓜頭。老瓜頭是種瓜的好把式,從播種、間苗到壓蔓、掐尖、打謊花全由他一人操作,盡管很累也不讓別人插手。還沒立秋,香瓜就陸陸續續地熟了,地里爬滿了長長圓圓或短短胖胖的瓜蛋子,噴吐著濃濃的甜香。老瓜頭在瓜窩棚前支起遮陽涼篷,擺上幾個小板凳,這是為吃瓜、買瓜人準備的。全村二百多戶人家只有這一個瓜園一個老瓜頭,所以人來人往,偏臉子便成為這個時節最熱鬧的地方,當然也是我們這些孩子最想去的地方。
每天,老瓜頭身穿對襟馬褂,頭戴草帽,脖子上搭著一條毛巾,默默地等待來人。不管誰來,他都沒有一句多余的話,只會笑,純樸得像他的那些無語的瓜。涼篷下擺著好幾堆瓜,任你自己挑撿,隨意吃。有脆生的白糖罐瓜,有綿甜的灰鼠子瓜,有長滿花道道的楞頭青瓜……老瓜頭從不夸自己的瓜,可挨樣一嘗,都是甜甜香香,禁不住叫幾聲好。在瓜窩棚吃瓜不用花錢,臨走總要挑一些帶回家去,老瓜頭就挎起筐到田中摘些新鮮的瓜。他的瓜一律賒賬,但要按斤記下來。老瓜頭拿出來秤和拴著鉛筆的厚本子,先是一秤一秤地稱,然后拿鉛筆蘸蘸嘴里的唾沫寫下名字和數量。送走一撥又來一撥,這段時間是老瓜頭最忙活最高興的日子。
大熱的天,我們這些小蛋子常常晌午下河洗澡,從水里拱出來就湊到一塊偷偷地去窩瓜棚,因為大人總是喝斥不讓去。老瓜頭一見我們就瞇瞇微笑,指著地上的瓜堆讓我們擦干凈了可勁吃,沒多一會兒我們的肚子鼓了,就想撒尿。老瓜頭說,瓜園的瓜不怕吃,就怕踩亂了瓜秧子碰掉了剛作紐的瓜,你們幫我看著點。其實他是怕我們偷瓜禍害了瓜園。這天也偏巧,我們突然發現瓜田旁邊的蒿草里有個人影閃動,就悄悄過去,逮個正著。那人是地主成分的徐婆子,她說她的老頭病了想吃瓜。老瓜頭挑個大瓜遞給徐婆子:“嘗嘗吧,又脆又甜。”他從瓜窩棚里翻出個布兜子,裝滿了瓜,送給了徐婆子。徐婆子說那就記個賬吧,老瓜頭搖搖頭:“不用了,我知道你們家困難。”徐婆子說這事要讓別人知道了會牽連你的。老瓜頭哈哈一笑:“吃幾個瓜還能吃出階級斗爭呀!”徐婆子走了,我們呆呆地望著老瓜頭,都覺得他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秋后,糧食賣了,人們絡繹不絕地來到老瓜頭的家結賬送錢,像村里開會人員那樣齊。老瓜頭用舌頭舔舔手指頭嘩嘩啦啦翻著賬本子,他說多少就是多少,沒有一個賴賬的或者耍滑少給錢的。賒賬這么長時間,孩子們還隔三差五去白吃,誰能不說幾句感謝的話呢。而老瓜頭總要把來的人一一送出大門外,指著偏臉子的瓜窩棚說:“明年按期開園,有錢沒錢都去吃瓜,捧個場呀。”
現在提起瓜窩棚,就讓人想起那時候鄉下人的厚道熱情,懷念那誠信互助的鄉俗民風。
掛 鋤
過了立秋,就掛鋤了。掛鋤就是三鏟三趟結束了,把鋤頭收拾起來,不再下地干上趟子的農活。這算農閑季節,大約一個月的時間,然后開鐮收割。
那時候我最盼的就是掛鋤,因為這時節總可以歇歇喘喘了。鏟地、趟地是農家忙季,活緊活累。每天一大早扛著鋤頭下地,頭上烈日炎炎,腳下土壟長長,一直鏟到天黑,熱得汗珠滾滾,累得氣喘吁吁。“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這首誰都知道的古詩,那時我就覺得太逼真了。掛鋤了,不那么繁忙緊張,也散淡了許多。村里有首《掛鋤》的民謠,至今我還記得:雨云朵朵薄,掛鋤家家樂;采山逛逛景,打魚玩玩河;沒事串串門,閑來聽聽歌……
從莊稼封壟開始,鄉村里走親戚串門子的人就多了起來。那些媳婦打扮得流光水滑,或騎自行車或坐丈夫的摩托車,帶著孩子回娘家。回娘家都要帶一把粉條,表示沒忘爹娘,親情是絲絲縷縷綿綿長長的。掛鋤會親家是個老習俗。兩家人趁農閑湊到一起殺一只羊,吃羊肉喝羊湯喜氣洋洋,這叫親親熱熱有福同享。我和一些年輕人結伙上山,這時候正是采黑木耳捉猴頭蘑的好季節。野生木耳都長在樹林間的朽木上,黑黑的厚厚的一層,抓一把滿手都是水靈靈的香氣。猴頭蘑生在柞樹枝上,在這棵樹發現一只后,再照直往前走十米左右,保準在相對的一棵樹上找到另一只猴頭蘑,神了,怪了。這時節的猴頭蘑肥肥胖胖,絨嘟嘟的針毛金黃透紅,格外好看。筐滿了,袋子鼓了,大家說說笑笑下山。走到苞米地旁,架起干柴,燒早熟的苞米吃,吃出嘴巴上的一圈黑。這叫啃青,野趣橫生,別有滋味。晚上回到家后就去看節目,有演二人轉的,有唱單出頭的,有變戲法的……熱熱鬧鬧,歡歡樂樂。
掛鋤期間,莊家院也不是什么活都沒有,只是不用起早貪黑罷了。好多人家都在起豬圈糞,清理垃圾,積攢農家肥;每天太陽升高沒有露水時,那些老人常常手拿鐮刀下地,去看看莊稼拔拔大草。甸子里有打羊草的,坡地上有起土豆準備開磨漏粉的,石頭山下有采石打算來年春天建房的……村里村外,人影閃動,笑聲不斷,掛鋤這段日子竟是如此火熱、安然,有滋有味。
剛到白露,母親就喊父親:“別再懶了,快去供銷社買割豆子的漏指皮手套和鐮刀,順便割幾斤肉回來。”我知道這掛鋤的日子結束了,就要開鐮了。
遛 茬
秋日,田野里的大豆割倒了又收回家了,只剩下一壟壟茬口白、底根黑的豆茬,一水水的,齊刷刷的,規整悠靜得像幅版畫。這個時候,牧羊人都要到大豆地放牧羊群,叫遛茬。
早年我在故鄉那個叫紅旗社的村子務農,曾經當過羊倌,那時就特別注重遛茬。豆棵上所有的東西羊都愛吃,所以遛茬這二十幾天最能抓膘,羊若膘肥體壯不但值錢,而且能安全過冬。每天一早,我甩出幾串鞭花,就把上百只羊趕進了大豆地。這些吃了一夏青草的羊們,好像碰上了改善伙食的大聚餐,撒著歡撿吃掉在壟臺上和壟溝里的豆莢、豆粒、豆秸、豆葉,滿地移動著嘩嘩啦啦的聲音,分外好聽。此時不用繞著圈圍群,更不能狂吼轟攆,而是讓羊們慢慢尋找并且細嚼慢咽,好消化。我抱著牧鞭跟在羊群后面緩步輕走,時而唱幾句鄉間老掉牙的牧羊調,熟悉我的聲音的那些羊仿佛知道有人管護它們,便無憂無慮地歡吃了。羊們是最愛聚堆的,但遛茬時從來就不爭不搶不奪,親親密密,沒有急眼了立角相頂的。這一點可能比人還強。它們喜歡自由隨意,可更喜歡集體。有的羊吃著玩著離群了,只要我大聲一喊,它就順從地歸隊了。
遛茬時也有意外的情況。那天頭午,一支娶親的隊伍從大豆地旁的鄉道上走來,敲敲打打吹喇叭,還放鞭炮。那些羊可能沒見過這種陣勢,支楞耳朵凝望,有些發毛。我怕炸群,立刻站到羊群中間,豎立牧鞭,手抓頭羊,連聲喊叫:“聚聚,窩窩……”羊們安定下來,沒有炸群。娶親的人馬通過以后,羊群沿田壟散開,又開始尋吃了。羊們眼尖腿勤,還不挑挑撿撿,所以很快就吃飽了。羊都是機靈鬼,不像牛吃起來沒完沒了,它們飽了就不多吃了。或搖動刷子般的短尾巴,或揚揚蹄抖抖毛,或似對話一樣咩咩叫幾聲,玩得歡快,那樣子惹人喜愛。羊吃飽了,我就收群回家,不管什么時辰。祖父告訴我,遛茬吃豆的這些日子,不能給羊啖鹽,因為啖鹽羊就要喝水,喝多了就會脹肚,容易生病。所以關上羊欄后,我都抱幾捆草扔進去,算是送給羊有點水分的零食吧。
過了遛茬這段時間,羊的膘情正好,那些倒騰羊的販子就從城里開車來買羊了。看著被抓上車的羊咩咩咩地直叫,再想象它們被宰殺的樣子,我的心里說不清是什么滋味。因此,每每看見買羊的車輛進村,我就故意晚些回去,那些羊也許理解我的心情,轉轉悠悠很聽話。我放牧羊,羊陪伴我,天長日久,人與羊自然難舍難分了。
前不久,鄉下放羊的妻侄進城來串門,我勸他多住幾天,卻沒留住。他說馬上就遛茬了,這抓膘的節骨眼是不能讓別人打替班的。看來,不管怎樣發展怎樣先進,有些事情還是不會變化的,像遛茬。
打烏米
我很小的時候,就喜歡跟本家寬哥去放豬。寬哥大我幾歲,他早早退學回家當豬倌,只想幫家里掙點工錢。入秋后的一個星期日,跟寬哥在東大甸子放豬,我一邊幫著圍群,一邊采紫紅紫紅的酸漿吃。這天沒風,很暖和,臨近晌午似乎更熱了。寬哥看我沒了精神頭,就問:“餓了吧?”我瞅瞅他,點點頭。他回身帶我把豬群攆進爛泥洼子,那些大大小小的豬好像進入了它們的游樂場,或倒臥或蹭身子或拱泥水,歡快得哼哼叫叫,沒有逃群的。這時寬哥拉起我的手:“走,打烏米去。”
烏米長在高粱秸的上頭,挺好吃的,那時并不多見。走進密密層層的青紗帳,細細尋找,慢慢采摘,叫打烏米。我和寬哥一壟一壟地搜索般往前走,仰著臉一棵一棵地往上望,發現沒有吐粒秀穗的高粱,那頂頭保準是長長圓圓的烏米。見到長著烏米的高粱秸,我們先是小心地搬彎桿棵,然后從頂頭上輕輕地掐下來。烏米只有兩種:一種是被葉子緊緊裹住,里面的烏米白白胖胖,嫩嫩的。咬開后,那瓤花花搭搭黑茬茬的,綿軟柔潤,有甜味。我們管這種烏米叫小伙烏米。另一種烏米叫老頭烏米。就是鼓鼓脹脹的烏米撐破了葉子,露出一團毛嘟嘟的黑絲,像胡須。老頭烏米淳厚濃香,富有野味,幾口就吃出嘴巴上的一圈黑。我和寬哥邊打邊吃,小肚子很快就鼓了起來。寬哥說,咱們再打一些烏米,拿回去給你爹下酒。
收工了,寬哥趕著豬群沿街呼喊:“收豬嘍!收豬嘍!”他挨家挨戶地送豬。我捧著用衣服包著的烏米,蹦蹦跳跳地回家了。俺媽干凈麻利,很快用烏米做了蛋煎烏米和醬蒸烏米兩個菜,接著燙了二兩老白干。爹從地里回來,盤腿坐在炕桌旁,夾了幾筷子烏米,又呷了一口酒,咂嘴品味,臉上露出了笑容。我睜大眼睛問爹:“高粱上怎么能長出烏米呢?”爹放下筷子,臉上惋惜的陰云遮住了笑容。他說,烏米盡管好看好吃,但它不頂用,你想一棵高粱只長烏米不秀穗要少打好幾兩糧食呀。停一下,他接茬又說,農人把每一棵高粱都當成孩子來侍弄,可有的秀穗籽粒飽滿,有的卻癟了長出烏米,可能是種子問題,從根上出了毛病。把土地和糧食融進血液里的爹,情感竟是這樣純樸而復雜。他摸摸我的腦袋:“不說了,長大你就懂了。”
糧食和烏米哪個重要?同樣流汗為什么耕耘出兩種結果?根上的毛病該怎樣防止?在這一系列沒頭沒尾的問題之中,我長大了,進城了,遠離那片土地了。
去年上秋,寬哥打來電話:“還想打烏米嗎?回來一趟吧。”我真想烏米這一口,卻沒立刻回答他。只因為種子的差別,高粱竟長出不同的果實,這讓我聯想到人生,陷入深深的沉思。
倒套子
“倒套子”,是大興安嶺林區一項特殊的活,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我很年輕時在老家紅旗社當農民,每每下過幾場冬雪以后,父親就跟六七戶人家插伙進山“倒套子”掙工錢,抓點“外塊”。“倒套子”就是把上不去任何車輛的山頂尖上伐下的樹木,綁牢捆住拴進套子,用馬爬犁一棵一棵地拉下來。這活又苦又累,而且有危險,必須會使馬,還要腿腳靈便。就是現在,山尖上的原木仍需“倒套子”,這特殊的活兒工錢挺高的。
那年冬天我頭一次跟父親進山,只見冰雪把所有的地方裹得嚴嚴實實,一派潔白,閃光透亮。老神樹下灑下一瓶酒,拜過山神,我們就牽馬上山了。這座山叫老爺嶺,很高很陡,沒有路,往上一望真有點眼暈。父親走在前面,用獵刀砍下一個個記號,做為木頭下山時的路線。氣喘吁吁地登上山,不能歇息,因為山頂上雪厚風大,嘎嘎寒冷,容易凍透身子,使手腳不聽使喚。大家先是排好各家用樺樹疙瘩做成底架的爬犁,然后相互合作,把原木抬到爬犁上,拴進鋼絲繩套子緊緊綁住捆牢,接著給馬掛上夾板套。一個人牽一匹馬,一匹馬拉一只爬犁,一只爬犁裝一根木頭,前后照應著同時下山。父親是總指揮,前面帶路,領頭大聲喊著號子:“爬犁下山嘍!人小心喲,馬聽話呀,慢慢走喲,別滑坡呀……”不時喊號子,讓人精力集中,步伐一致,安全行進。否則一不小心,爬犁容易被林子掛堵住,或者掉進雪坑,那便麻煩費事了。而一旦馬驚人亂,跌倒滾山,就慘透了。我們后村的徐二,那年“倒套子”時耍單逞能,過陡坡時人馬掉進深溝,沒命了。我們一路上鉆林縫,繞陡彎,過滑坡,左閃右躲,常常嚇出一身冷汗。大家抓住韁繩,緊跟父親扎扎實實行走,誰敢馬虎,誰敢不聽他的話。他則像資深的山把頭,很威嚴,更認真。
下山來到貯木場,木頭打號歸楞,就拿木頭票去領當天的工錢。夜里,給馬添草加料后,大家擠在兩間小木屋里,喝酒吃肉,樂呵呵地唱二人轉小調,玩五子棋,摔撲克,好像把疲累全忘掉了。父親按時吹滅小油燈,大家便睡進狍皮被,咬牙放屁說夢話,又是一夜,天亮早早上山。有時碰到暴風雪天上不了山,就捉兔子抓野雞,特有趣。兔子一見紛紛揚揚的大雪就發懵,你發現后就拿棒子去攆,跑出不遠,就能逮住兔子。野雞是顧頭不顧腚的,它一見到人就把腦袋拱進雪堆里,尾巴明晃晃地露在外面,你悄悄上去一下子就抓到手了。打回來野雞、兔子自己舍不得吃,賣給林場的食堂,很值錢。
這“倒套子”的活一干就是兩個月。春節臨近了腰包也鼓了,大家要回家過年了。鞭子上拴系紅火火的纓穗,馬脖子下掛一串銅鈴,放幾只吉祥的二踢腳紙炮,一串爬犁就飛跑出山了。父親一改在山上那種嚴肅的表情,坐在爬犁上唱電影《老兵新傳》里的插曲: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他那跑了調的歌聲,讓人們笑個不停。
(責任編輯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