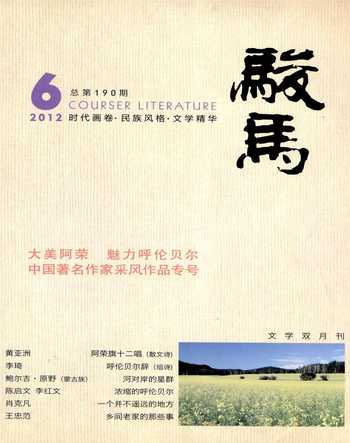開在心底的一朵鄉愁
紫陌
本名于雪梅,1970年冬月一個飄雪的日子出生于呼倫貝爾市阿榮旗,職業記者。出版過散文集《女人不醉》《一米春天》。散文《想你的夜晚沒有你》《愛那么短遺忘那么長》分獲呼倫貝爾市第五屆、第六屆文學藝術創作政府獎(駿馬獎)。
今春陌上花開遲。有時想,他在南國,該是早已淹沒在煙柳繁花中了吧。
夜里睡得正酣,忽然被手機鈴聲驚醒,迷蒙中接起,傳來久不聯系的他的聲音。我賴唧唧地說:“干嘛呀?讓不讓人睡覺啊?你看看幾點了啊?”他說:“不管,我不管幾點,我就是想給你打一個電話,就想在此刻聽到你的聲音!”
我已然感受到了他的醉意。我不回應,任憑他滔滔不絕。偶爾,他試探性地:“喂?”一聲,我懨懨地回:“在呢,說吧。”
他說,離開家鄉,掙多少錢都不是重要的,在茫茫人海中,他始終無所傍依,他說他仿佛沒有根,一直漂泊。他有了大房子小轎車,可是他找不到幸福感,他總覺得他還沒有家……
掛斷電話,看到手機屏上顯示凌晨兩點五十八分。
再無睡意。想珠江岸邊的他,定然正在海風中踟躕徘徊。
盛夏,一位闊別多年的女同學從深圳回鄉探親,在一個新開的餃子館兒,我們幾個摯交邊吃邊聊。席間,不知是誰提到了余光中的《鄉愁》,恰逢服務生將一盤酸菜餡兒餃子端上桌來,我的女同學,是一家擁有雄厚實力的私企高管,不再顧及什么吃相,將滿盤餃子移到自己面前,熟練地用筷子夾起一個塞到嘴里,邊吃邊含糊不清地說:“你們不知道,我的鄉愁不是一枚窄窄的郵票,而是一盤酸菜餡兒水餃!”
在場的人差點笑翻。可是,幾乎在一瞬間又都停止了笑,甚至,有點點淚花在眼里閃爍。
這時,她停箸,舉杯,娓娓述說:“你們也許不會體會一個游子想家的心情。”
她說,有一天,她難得清閑半日,與老公一起逛街。經過一家音像社時,忽然被一種天籟般的聲音所吸引,再邁不動腳步。那是一首家鄉的歌啊,是她聽了千遍萬遍也不厭倦的《銀色氈房》。“草原深處有一座氈房,裝著我幸福童年美好的時光,氈房前有一條彎彎小河,帶著金色的夢幻流向遠方。養育我的大草原,給我生命的銀色氈房,你把我扶上了人生的路,你的恩情我終生難忘……”
那時候,夕陽正緩緩西斜,給深圳這座開放的都市披上了一件金色的外衣。她當時很奇怪,這是深圳啊,怎么會有人播放蒙古歌曲呢?一時竟疑似夢中,被蒙古族歌手瑪希的純正音色所牽引,她如癡如醉般地一步步向那家小店走去。
攀談中,她知道店主是個轉業軍人,曾在內蒙古當了十二年的兵。她問,你在這里播放蒙古歌曲能賣得出去么?他說,沒想過,就是忍不住對內蒙古的想念,就想聽蒙古歌。聽說她來自內蒙古,店主非要送她一本蒙古歌曲的碟子,她說什么也要給錢,店主拒收。最后,她放下歌碟落荒而逃。
此后,只要有空,她就去那家小店看看,哪怕僅僅是聽一首蒙古歌曲就走,也像是去親戚家串門了一樣。
正是緣于這一縷鄉愁,讓臺灣著名詩人、散文家和畫家席慕蓉踏上了回故鄉的路。席慕蓉的父母都是蒙古族,五歲以前她能說一口流利的蒙語。1989年,四十六歲的她平生第一次走進內蒙古。草原的遼闊與熱情讓這位詩人心中埋藏了四十多年的鄉愁燃燒起來。此后,這位曾低吟淺唱愛情故事的臺灣女詩人,儼然一位背負著蒙古族文化闡釋者和傳播者使命的學者。她數次回到內蒙古,回到草原,而這一切,正是因為那濃濃淡淡的揮之不去的鄉愁。
曾經有人問席慕蓉,你去內蒙古那么多次,都干什么呢?誰知她的答案竟出人意料地簡單,飽含情感卻令人動容,她說,我就是想在草原上坐一下。在她眼里,內蒙古的朝霞、彩虹、巖畫、古城墻等等都沒有遠去,蒙古族文化歷經歲月的洗禮,更加光彩照人。席慕蓉在南開大學演講的時候,曾大聲說:“我多么希望別人可以選擇我寫故鄉的那些詩來讀!”
自古,鄉愁就不分男女,不分老幼。月圓時分,想起蘇軾那句經典名句: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此刻,鄉愁定是那一輪亙古唯一的當空明月。而更多的時候,鄉愁是開在心底的一朵茉莉,那幽幽花香,似有若無,又無時不在。
(責任編輯 晉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