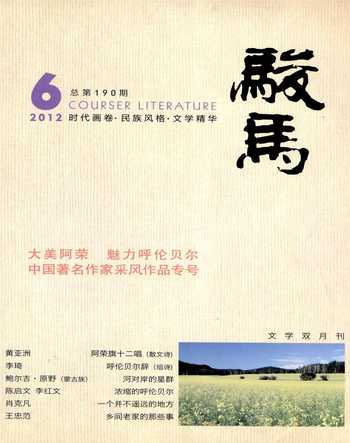阿榮情結(jié)
方炎
筆名芳絨絨,生于內(nèi)蒙古阿榮旗。《內(nèi)蒙古商報(bào)》記者、呼倫貝爾市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阿榮旗戲曲協(xié)會(huì)副主席。曾任阿榮旗電視臺(tái)《阿榮看臺(tái)》欄目主持人、編導(dǎo)。現(xiàn)任阿榮旗宣傳文化中心創(chuàng)編、節(jié)目主持人。在《內(nèi)蒙古日?qǐng)?bào)》《內(nèi)蒙古商報(bào)》《草原》《林海雪原》等報(bào)刊發(fā)表詩歌、散文、報(bào)告文學(xué)作品。2011年散文集《水夢(mèng)年華》獲呼倫貝爾文學(xué)藝術(shù)創(chuàng)作政府獎(jiǎng)(駿馬獎(jiǎng))。
單位的對(duì)面原本是一塊很大的空地,不知道什么時(shí)候起,空地的四周已經(jīng)豎起一道色彩繽紛的廣告墻,據(jù)說是要建一棟高層別墅。
秋日的陽光執(zhí)拗地照在這片空地的沙土上,沙土之外的阿倫大街和離這不遠(yuǎn)的明德小學(xué)也沐浴著溫?zé)岬年柟猓业母锌突貞浘驮谶@碩果滿枝的季節(jié)蔓延開來……
二十年,我土生土長的阿榮小城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變化之大讓人始料未及。每一次經(jīng)過水務(wù)局大樓的時(shí)候,我都忍不住要向那里多看上幾眼,盡管這里童年記憶中的茅草房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大樓,可那些有關(guān)貧困的記憶依然那么清晰地在我腦海中浮現(xiàn)。
那時(shí)候幾乎所有人家都很困難,僅憑父親低微的工資養(yǎng)活我們一家六口已經(jīng)是不堪重負(fù),母親只好每天要去水泥管廠干體力活。父親很少和我們說話,母親整日因?yàn)檫^度疲勞郁郁寡歡,甚至是牢騷滿腹,而敏感的我已經(jīng)感覺到我們這四個(gè)孩子已經(jīng)成為家庭的負(fù)擔(dān)。更多的時(shí)候母親會(huì)把我們鎖在低矮的不足十平米的茅草房里,夏天漏雨冬天透風(fēng),土炕上四季放著一個(gè)掉了漆的大盆,夏天接雨冬天放炭。
我們最害怕母親出去了,不僅不讓出門還要讓我們看著那口巨大的飯鍋,飯鍋里永遠(yuǎn)是難吃的大米查子飯,等到她晚上回來,如果我們沒有打仗或淘氣,母親的嘉獎(jiǎng)是在煮好的大米查子粥里放上糖精,或者是用醬油炒上一顆卷心菜,既沒有肉也沒有油,可是每次我們兄妹幾個(gè)都吃個(gè)盤底朝上。最高興的事情是盼著母親回娘家,這樣父親回家的時(shí)候偶爾會(huì)給我們買一個(gè)麻花,然后給我們用麻花煮掛面。
記憶中最好吃的東西是糖水罐頭了。我因感冒發(fā)燒嘔吐不止,后來父親給我買了一個(gè)桃罐頭,以后我居然天真地希望自己能再次感冒。糖水罐頭的味道至今難忘,現(xiàn)在想來童年一直是我生命最難熬的部分,雖然時(shí)間很短但讓我懂得了什么是貧窮。
上小學(xué)的時(shí)候,我家已經(jīng)搬進(jìn)了父親單位統(tǒng)一建筑的瓦房,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只是令我最尷尬的事情是我沒有一件合體的衣服。
記得一次上間操的時(shí)候,由于天氣變暖,校長要求不要再穿大衣上操了,我回頭望去,幾百人的操場就只有我一個(gè)人還穿著一個(gè)黑色的呢子大衣,這件母親的外衣我已經(jīng)穿了四五年了。我一路哭泣回家,而當(dāng)母親問我原由之時(shí),我居然說不出口。其實(shí)我們兄妹幾個(gè)也常常因?yàn)閾Q穿衣服上學(xué)而互相埋怨,至于想擁有一件新衣裳的想法簡直是天方夜譚。而當(dāng)時(shí)我們家的條件就算是同學(xué)中比較好的了,我十四歲之前沒有見過雪花膏,沒有穿過高跟鞋,沒有一件合體的衣服,沒有看過電視,沒有上過飯店,家里沒有長電,沒有洗澡的場所。現(xiàn)在想來,盡管我們可以把它歸結(jié)為全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性不高,但作為七十年代出生的同齡人,我們記憶中最深的是交通的困惑。
上學(xué)的路不但是漫長而且難走,到處都是土路,泥沙滿地,垃圾成堆,農(nóng)用車、馬車常常讓我們心驚肉跳,盡管我們每天都排隊(duì)放學(xué),可是我們鄰班的一個(gè)同學(xué)就在我們經(jīng)過的十分鐘后,被突然沖過來的馬車奪去了年僅十歲的生命。后來,我還常常憶起校門口一個(gè)蓬頭垢面的女人癡癡地等待她孩子回家的情形……
上高中的時(shí)候我們都有了自行車,我的自行車是除了鈴不響以外哪里都響的典型,而且是一個(gè)很大的“二八”車身,可這臺(tái)自行車為我家立下了“汗馬功勞”。由于當(dāng)時(shí)客運(yùn)站離家很遠(yuǎn),每次家里人出門都是父親騎著這臺(tái)自行車,前面掛著大包小包,后面馱著大人或是小孩,無論是驕陽炙烤之下還是在寒風(fēng)刺骨的冰雪中前行,它就像一個(gè)忠實(shí)的保鏢,縱使很慢,但終可以安全到達(dá)終點(diǎn)。
高中三年每一次我穿著厚厚的冬裝騎著那臺(tái)已經(jīng)是破舊得近乎散件的自行車走在上學(xué)路上的時(shí)候,頭腦中閃現(xiàn)出大都市的繁華和美好,那時(shí),我就想一定要考出去。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這里的貧窮和落后,臟亂和低俗,我小小的心靈裝滿了對(duì)異鄉(xiāng)的向往和渴望。然而,在我眼巴巴看著我的同學(xué)一個(gè)又一個(gè)陸續(xù)接到大學(xué)通知書興高采烈地離開家,而我還在黑色的八月中翹首期待屬于我的那份希望時(shí),我曾在雨中站了整整一夜,母親的呼喊和父親的責(zé)罵形成鮮明的對(duì)比,在我近乎是絕望的等待中,二十天后我才接到了那份輾轉(zhuǎn)之中被擱淺了近一個(gè)月的海拉爾學(xué)院的通知書。我的淚水如泉涌出,我在心里暗暗地念叨,別了,這個(gè)貧窮的小城,別了,這里灰色的年少時(shí)光。
當(dāng)我第一次坐上火車去海拉爾的時(shí)候,二十歲的我感覺就連扎蘭屯的天也是那么藍(lán),可是,當(dāng)我滿懷欣喜地交完入學(xué)學(xué)費(fèi)的時(shí)候,我的兜里只剩下六十元錢,我還記得我站在異鄉(xiāng)的電話亭里一遍遍給父親打電話,每一次父親都說馬上就來,最后我兜里只剩下打電話的錢的時(shí)候,我沒有再提錢的事情,我平生第一次用哭腔和父親說了一句很動(dòng)情很心碎的話:“爸,我想你……”
后來,父親告訴我回家上班吧,這個(gè)上班的機(jī)會(huì)實(shí)在太難得了,并且把我的學(xué)業(yè)改成函授學(xué)習(xí)。我一直是一個(gè)很聽話的孩子,何況我知道,上學(xué)的最終目的也是就業(yè),而且弟弟和妹妹更需要求學(xué)的機(jī)會(huì)。
我討厭這個(gè)地方,這里的人這里的環(huán)境,然而我終沒有走出去,我回來了,我萬念俱灰。上班的環(huán)境也是在鄉(xiāng)下,在臟兮兮的食堂里每天就著同樣的咸菜吃著粗面的饅頭,最多的菜就是菠菜燉豆腐,每天躺在冰冷的板床上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家。
而我生活的不幸就從那個(gè)時(shí)候埋下了必然的伏筆,三年后在急功近利中我絲毫沒有考慮到自己對(duì)待愛情的感受,匆忙嫁人,而讓我成就婚姻最佳的理由是,我調(diào)回來了。陽光是這樣的燦爛,工作環(huán)境也很優(yōu)越,我努力工作,發(fā)揮自己的特長,一種屬于年輕人的豪情壯志滌蕩我的身心。幾年后,當(dāng)我們住上了單位統(tǒng)建的全旗一流的住宅樓的時(shí)候,我的身邊經(jīng)常是榮譽(yù)鮮花和掌聲的時(shí)候,我才知道安居并不意味樂業(yè),環(huán)境的優(yōu)越未必代表心靈的幸福,衣食無憂的背后,我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jià)。如果說年少的貧窮是一種無奈的狀態(tài),那么而今精神境界的貧窮是一個(gè)女人生不如死的悲涼。
長久地氤氳這種無言的悲涼,腳下的這片土地卻已經(jīng)發(fā)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垃圾屯”的故事已經(jīng)遙遠(yuǎn)而陌生,阿榮旗已經(jīng)成為呼倫貝爾一顆璀璨的明珠。
當(dāng)我孑然一身走出婚姻圍城的時(shí)候,站在魅力阿榮華燈初上的夜晚,我徹底放棄了多年以來想要出去創(chuàng)業(yè)的想法,不是年齡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作為一個(gè)母親對(duì)自己孩子的掛牽,因?yàn)椋谖医?jīng)歷的風(fēng)雨歲月中,我難以割舍的居然是對(duì)這片土地上郁結(jié)的鄉(xiāng)情。
我還記得在電視臺(tái)做節(jié)目的時(shí)候,我采訪的那些淳樸的鄉(xiāng)親;那些為阿榮小城建設(shè)付出辛勤汗水的人們;那些披星戴月早出晚歸的清潔工人;那些至今仍在為阿榮旗的各項(xiàng)事業(yè)運(yùn)籌帷幄、勵(lì)精圖治的人民公仆。記得一位七旬老人拉著我的手說:“阿榮旗是個(gè)風(fēng)水寶地,可不能離開啊。”當(dāng)時(shí),我還想笑。
如今在同學(xué)十五年畢業(yè)回家團(tuán)聚的笑聲中,我的兩位在外地發(fā)展很好的同學(xué)有感于家鄉(xiāng)的變化,說要回家投資,阿扎鐵路的投建是他們最感興趣的話題,而且他們居然開始羨慕我由“麥田里的守望者”成功蛻變成“城市達(dá)人”。他們向我訴說外面世界的艱辛與無奈,即使是事業(yè)最精彩的時(shí)刻依然是走不出對(duì)親人和父母的思念,回家,回家一直是支撐著他們?cè)谕饷娲蚱吹膭?dòng)力。
這個(gè)秋天,我和我的同學(xué)們,胸中涌動(dòng)著一股暖流,回家真好!
樓群,街道,綠草,轎車,人流,一切和二十年前截然不同。
我和阿榮小城一起成長一起成熟,而且還將相伴走過以后的日子,魅力阿榮在我的心中就是海市蜃樓,就是夢(mèng)中天堂。我恍然大悟的是,其實(shí)只有心中有了大愛,只有真正愛你腳下的這片土地,你才會(huì)甘愿平凡或是偉岸,貧窮或富有,才會(huì)找到你最溫情的小家。大愛正如這秋日里無比溫暖的陽光,穿過我的思緒停留在枝頭上的那些豐碩的果實(shí)上。
明年這里的別墅會(huì)是什么樣的呢?
想象開始生出多情的翅膀……
(責(zé)任編輯 晉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