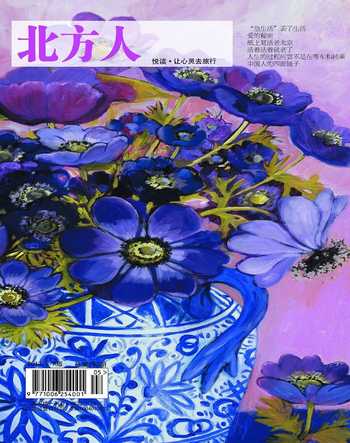徐雪寒用生命敲擊改革開放大門的人
從玉華
他被稱為“用生命敲擊改革開放的大門”的人。
他被拿來與顧準相提并論。經濟學家吳敬璉評價道:“如果顧準在學術思想上是一個泰斗級的人物,那么他的才能是表現在多個方面的。”實際上,他與顧準本就是摯友。
他叫徐雪寒。
一個自稱“跑龍套”的大家
徐雪寒生于1911年,卒于2005年,原名漢臣,浙江慈溪人。他是1926年參加中共的老黨員,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貿部副部長,后來因為潘漢年案牽連入獄,蒙冤26年,平反恢復工作時已經70歲。在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后改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他當常務干事,以經濟政策研究推動改革。
在北京的西長安街,人們看到風格獨特的中國人民銀行大樓,便知那是中央銀行。但是沒多少人知道人行是怎么成為名副其實的“央行”的,其中,徐雪寒功不可沒。
在上海的交通銀行總部,每天出入成千上萬人,但鮮有人知,當年建立這第一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建議,主要是徐雪寒提出來的。直到紀念改革開放30年,在一篇“交通銀行遷滬記”中,才終于有人提到他的名字。
在上海浦東繁華的街頭,沒有人會把今天的上海跟這個故人聯系起來,可徐雪寒正是最早向中央提出要給上海“松綁”的人之一。
在北京美術館東街22號三聯書店辦公樓一樓大廳內,懸掛有9位創始人的大幅照片。作為三聯前身之一新知書店的主要創始人,徐雪寒的照片就在其中。所有照片中,他顯得最為年輕,著西裝,系領帶,頭發向后梳著,很有風度。每天上下班,很多員工出入電梯,都要面對徐先生的照片,可幾乎沒人停下來多看他一眼。
他還是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的創辦人之一。基金會的一間老屋子里至今保存著一份發黃的賬目單,上面記載著:徐雪寒2008.32元。1983年,剛平反兩年的他把補發的“文革”10年工資全部捐出,成為基金會的第一筆捐款。
徐雪寒生前給自己定位,不過是“一個在漫長的革命運動中跑龍套的人”。
捉迷藏的人
徐雪寒的兒子小時候寫過一篇作文叫《我的父親》,寫自家從一處遷到一處,又遷到另一處,卻總見不到父親。老師的批語是:“像捉迷藏。”而徐雪寒的一生就真的在“捉迷藏”,直到晚年,才被宣布“游戲”結束,回到家來。
他一生有26年失去人身自由。1928年初,17歲的他因從事革命活動被捕,在國民黨的監獄中待了6年。1955年后又因潘漢年案蒙冤,在北京秦城監獄等處關了10年。“文革”中,他又在“牛棚”和“干校”中度過了大約10年。等到平反時,他已是七旬老人了。
青年時期的徐雪寒“像救火隊員一樣”干過很多種職業。他干過地下黨,為黨組建過書店、對外貿易公司、錢莊、銀行、紗布公司等。當年他組建的香港寶生銀號,在后來美國凍結新中國外匯時,曾為國家保存大量外匯發揮過很大作用。1949年后,他又被任命為上海鐵路局局長、華東貿易部部長、外貿部副部長。
一度,這個高級干部成了國家重用的“棋子”,被挪來挪去。干鐵路時,他為抗美援朝運煤、調物資;干外經貿時,他西裝革履,代表國家出訪波蘭、民主德國。周恩來曾稱贊他,干一行,鉆研一行,成績優異。
他只有初中學歷,卻發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稱自己讀的是“牢監大學”。當年在國民黨的牢房,他跟薛暮橋、駱耕漠等關在一個“籠子”里,他們就組成世界語學習小組,學習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盧森堡的《新經濟學》等。他還通過家里搞來了一本石印的《史記》,由于沒有辦法圈點,“就用洗馬桶的掃帚條在印泥上一印,然后在書上一點”。
魯志強說,自己很難想像,徐老這樣的共產黨員“坐了6年國民黨的監獄、10年共產黨的監獄、10年革命群眾的民辦‘牛棚”,“一個革命者被‘革命,一個理想主義者被理想拋棄,那是怎樣的痛苦。”
有人勸徐雪寒寫回憶錄,他不肯。有人猜測,他是不想讓那些當年整他的人難堪。他總是說:年輕人犯錯誤,不算什么。
“徐雪寒的氣質是學不來的”
關于自己的研討會,徐雪寒一生也沒經歷過,盡管他可謂成就斐然。
為了成立央行,他分別和四大銀行以及保險公司的負責人談,經過12次座談會,才大體達成協調。最后,他和他的同事們向國務院建議:由中國人民銀行承擔中央銀行職責。
晚年,他有過3次調任、高升去做“正職”的機會,他都放棄了,他甘于“跑龍套”。
“徐老不喜歡在聚光燈下,他非常‘享受,甚至自得被人們遺忘的感覺。”魯志強學著老人“得意”的樣子,最后擺擺手說,“徐雪寒的氣質是學不來的。”
1978年,他被安排到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經濟研究》雜志擔任編輯。他很珍惜這份工作,天天擠公共汽車上下班,戴著副套袖,有時還把稿件帶回家加班。他總是最早到單位,打掃衛生,拿鐵皮水瓶打水。有年輕人過意不去,也早來搶著打水,可總搶不過徐老。
1979年,《經濟研究》發表了一篇論述目前中國社會主義還處于不發達階段的文章,有領導認為這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抹黑,強令編輯部組織文章批判。徐雪寒很生氣,據理力爭,堅持文章觀點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態度極為堅決。而當時,他還沒平反。
他也不太懂官場的“規矩”。有一年,有個領導給當時很窮的研究中心拉來了一筆贊助,要給每個人發200元的獎金。徐雪寒知道后,一下子從沙發上跳起來,當著所有人的面,毫不留情面地說:“這些不正當的錢、骯臟的錢,我一分不要。”
他是“改革派”。對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波折,他常常是心急如焚。1987年,國家經濟遇險,他發文預警:制止通貨膨脹是當務之急。
他曾和一些經濟學家研究“深圳特區貨幣”發行問題,后來深圳特區改革遇到一些人的質疑時,他“力挺改革”。
他竭力主張及早開放和開發上海,要對上海“松綁”。他說:“上海人靈得很”,“要解脫發展商品經濟的束縛,使上海人的長袖能夠舞起來”,“著眼于祖國的統一,有必要和香港、臺灣比”。這一建議引起了當時中央領導的重視,很快就被采納。那些年里,陳國棟、胡立教、汪道涵等上海市領導來京開會,必來看他。
徐雪寒的文章語言樸實,沒什么數學模型,卻篇篇都直指當時的經濟熱點。他的司機施國通不懂什么“實證研究”,他只是記得,在徐老的最后10年里,這個對自己的存款從沒概念的老人,總是讓他推著輪椅,一趟趟地在菜市場轉,看老百姓的經濟狀況。
回歸到百姓之中
這個習慣了各種監牢的老人,在最后的時光里,終于被自己的身體囚禁了。
他整日睡不著、頭昏,只能圍著圍嘴喝粥,抑郁癥摧毀著他的每寸神經。醫生勸他聽音樂、相聲,這個“無趣”的老頭兒說,“那不是自己的行當,不懂”。他最擔心的是,“報紙新聞都看不了,怎么活啊!”
為了看《新聞聯播》,這個簡樸的老人擁有了他并不喜歡的“奢侈品”——一副助聽器。
他讓司機施國通給他念報紙,遇上《人民日報》的社論便要求多讀一遍。他聽新聞很認真,有時會打斷施國通,問上面一個數字是多少,施國通說“好像是……”他立馬說:“不能好像,要一定是!”
身體的門一扇扇向這個早些年還堅持每天冷水擦身、意志堅定的老人關閉了。他對魯志強說過好幾次,希望安樂死,不愿再浪費國家的醫療資源。每一次去探望,魯志強都覺得“徐老今年夠嗆了”,可徐雪寒還是熬過了一年又一年。魯志強說:“那一定有一種神奇的力量支撐他。”
徐雪寒其實是熱愛生活的。相比老朋友薛暮橋“像被剪刀隨便啃過幾口”的頭發,徐雪寒偶爾也會去北京最好的理發店“四聯”。
有時,他像個可愛的老小孩兒。他是南方人,好甜口,遇到高興的事兒,他總是讓保姆給他一顆糖吃。
女兒徐淮回憶,記得爸爸曾說,“如果說我一生還干了一些事,有三點:肯下力,不自私,寬待人”。這實在不是什么豪言壯語,要做到卻實在不容易,但徐雪寒做到了。
吳敬璉是最后一個見到徐雪寒的人。2005年4月27日,他去北京醫院探望徐雪寒。他像是睡著了,吳敬璉俯身在他身邊說:“雪寒同志,我是吳敬璉,我來看你……”一滴清淚從徐老的眼角滑落,同時,監護儀上的血壓數字也開始往上跳動。
吳敬璉走后幾分鐘,徐雪寒去世了。
遵照徐雪寒的遺愿,他捐獻了遺體,并捐獻角膜,但最終因為角膜老化,沒有派上用場。按照級別,他本來“有資格”進八寶山革命公墓。但最終,兒女們把徐雪寒夫婦合葬在了八寶山人民公墓。女兒徐淮說,他們來自普通百姓,就讓他們最后回歸到百姓之中吧。